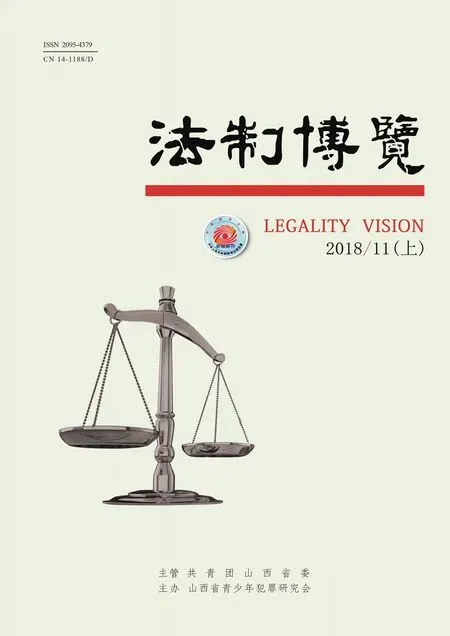論未成年人不良行為預防矯正體系檢視機制之建構
曹若晨
宜興市人民法院,江蘇 宜興 214200
對于未成年不良行為的預防與矯正問題上,學者們達成了共識,家庭、學校、社會應形成合力,共同預防與矯正。《預防青少年犯罪法》規定對于不良行為,未成人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與學校應當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對于嚴重不良行為,則為二者共同嚴加管教。此外,在工讀教育由強制性轉變為自愿性后,監護人實質上成為了不良行為(嚴重)預防與矯正的主力軍。法律規定與學者獻策的背后皆潛藏著這樣一個邏輯前提,若監護人或者學校想教育,則一定可以教育的好,問題在于,這樣的假設難免流于武斷和經不起推敲。監護人與學校是否有能力去預防與矯正缺乏科學的評價機制,進而社會何時應介入也成為“未解之謎”。基于此,有必要建立不良行為預防矯正評估機制,在跟蹤檢驗的同時,也為社會的介入時點提供科學的論據。
一、問題的提出
《預防青少年犯罪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由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法律規定看似詳實,并對接于未成年保護法的監護權轉移制度,但細細咀嚼,若未成年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但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愈演愈烈的情形,又該當如何呢?縱觀兩部未成年的“憲法性”保護法未有只言片語,從規范角度,這種情形自然而然,因為法律不強人所難。但從事實角度,這是預防與矯正的缺漏地帶。
二、現行不良行為預防與矯正運行機制之檢視
未成年犯罪呈現從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至違法犯罪的漸變轉化趨勢。多數未成年人在犯罪前就己經具有夜不歸宿、不良交友、逃學、打架斗毆、吸煙等不良行為,并處于家庭、學校無力監管的狀態[1]。現行法律制度對于嚴重不良行為依據情節的輕重規定3種矯正措施,但對于不良行為的矯正則呈現空缺狀態,也即在嚴重不良行為向違法犯罪轉化這一階段,社會力量才開始介入,而在不良行為向嚴重不良行為轉化階段則完全依靠學校和監護人的自主努力。
(一)法律規定存在邏輯空缺
《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將未成年失范行為分為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并展現預防不良行為,矯正嚴重不良行為的理念。從形式邏輯上分析而言,預防意味著防止不良行為之出現,而矯正意味著嚴重不良行為之去除,那么在不良行為出現后,并進而向嚴重不良行為逐步遷移的過程中,是應該預防還是應該矯正呢?法律對此全然無規定。《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在不良行為處使用“不得有”,在嚴重不良行為處使用“制止”,若我們把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視為同一或者將其轉化視為一蹴而就,則防止出現與制止再生邏輯上具有完全性,但不良行為與嚴重不良行為顯然不是同一事物,法律對此有明確的界定,此外,從“屢教不改”,“多次”這樣的界定用語也可以發現不良行為到嚴重不良行為的轉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于是,預防不良行為出現與嚴重不良行為消除規定之間,不良行為加深、重復并進而被認定為嚴重不良行為這一過程被忽視,呈現規范意義上的形式邏輯空缺。
(二)矯正體系缺乏檢視機制
在預防未成年犯罪領域,矯正可以分為刑事矯正與非刑事矯正兩大類,針對于不良行為未成年的矯正顯然是非刑事矯正。非刑事性質的矯治不是對未成年人進行懲罰,主要是出于保護和教育的目的,使未成年人改過自新,改掉身上的不當行為和不良習慣,重新返回普通學校學習[2]。未成年人非刑事矯正本質也是一種治療,其對象是未成年的不良行為,與醫師醫學治療所相似的是,二者皆以治愈也即矯正對象的去除為最終目標,故矯正的有效性是矯正體系建構的核心。
不良行為至違法犯罪演進轉化的過程性,決定了預防與矯正過程的過程性。于是,吳宗憲教授提出了針對青少年犯罪預防的三級預防機制:防患于與未然的一級預防;針對輕微違法行為的二級預防;針對輕微犯罪行為的三級預防[3]。三級預防的階層性建構意味著不良行為至違法犯罪漸進的過程伴隨著層級預防的失效。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趨勢表明三級預防的相對無效性,需要追問的是,哪一級預防出現了問題,哪一級預防的哪個方面出現了問題?在我國現行的矯正體系下,這樣問題無從回答。在實證證成,不良行為與青少年犯罪的強相關后,不良行為的成因成為研究的熱點,也即一級預防的失效問題。雖然從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理論和實踐來看,最有效、最經濟的犯罪預防,是一級預防[4],但二級預防與三級預防顯然也是青少年犯罪預防體系的重要內容,且矯正體系對應的正是二級預防與三級預防。當青少年從不良行為向嚴重不良行為轉化并進而實施犯罪行為的時候,二級預防、三級預防如何失效,這樣的成因分析或者事后檢視在現行的矯正機制中難覓。三級體系的構建意味著為青少年犯罪構筑三道安全門,同時也為安全門有效性的檢視提供了三次機會,沒有門是打不開的,故檢視與修正在某種程度上相較于構建更為重要,令人惋惜的是,在明晰矯正主體的同時,并未構建相應的檢視機制,也即關注“有”,而非“有效”,這不能說不是矯正體系的一大缺陷。
三、不良行為預防矯正長效評估機制具體設想
最大效益原則下,對于不良行為預防矯正長效評估機制的構建必然要依托于現行的預防體系運行機制,也即在原有機構能夠有效承擔的情況下,無需建構相應的全新或者獨立的機構而負責評估機制的運行。未成年的環境敏感性與自身的非穩定性決定了評估機制的視野不應僅限于不良未成年人自身,也應包括相應的環境。相較于成年犯的犯罪場[5],未成年人對于環境的易受性決定了其不良行為場更為值得關注。
(一)評估機制主體
不良行為至違法犯罪的行為多元性以及處遇的多樣性以及環境因素的復雜性決定評估機制的主體應該能夠涵攝整個預防矯正循環過程,同時能夠兼顧或者調動家庭,學校與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溝通或者協調于行政與司法機關。在此,似乎我們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全面管控未成年的不良行為及違法犯罪的機關,這也為諸多學者所極力提倡。我們認為獨立建構獨立機關有違最大效益原則,在所涉黨政機關中,具有這樣的職能機關并非不存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也即“關工委”正是這樣的機關。從其機構設置的目標以及人員配置來看,其完全有能力組織相關力量,承擔對不良行為預防矯正體系的評估職責。其完整的機構布局體系與長期的工作基礎決定了只需單純賦予此其項職責即可,同時其群眾性工作組織的屬性也滿足于檢驗獨立性的要求,并進而形成家庭與政府主導,社會力量檢驗雙層體系。
(二)評估機制客體
評估機制的客體也即評估機制的對象至少應包括不良行為人自身以及其所處的環境兩部分。刑事事件中隱含著一種三元性的結構模式,即由犯罪者、被害者和刑事環境在具體和抽象、情境和人格形成等不同維度上組合而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模式及規律[6]。在未成年人不良行為事件中,犯罪者與被害者為同一體,不良行為未成年人既為施行人也為受害者,故三元結構轉化為二元結構也即不良行為人與環境。正如前文所述,未成年人具有環境易受性,在意志自由非決定論下,這樣的影響因素顯然值得關注,這既關乎成因的發現,更關乎矯正的一般過程的有效性與最終有效目標的實現。以往,規范學上的一般預防與報應思維使得我們將視野專注于不良行為人自身,但矯正與預防成敗顯然也與環境對行為人的影響息息相關,故將環境因素納入評估機制也自然而然,此外,基于評估機制的設定初衷與最終目的,在評估機制中納入環境因素也是必須。
(三)評估機制內容
評估機制內容也就是評估機制的具體運作方式。預防矯正的長期性與過程性決定了這種評估是一種跟蹤性的評估。在維度上,可以分為整體與具體兩個層次。整體層次包括整體預防與矯正效果的評估,其類似于某地區的治安狀況的評估,這種層次上的評估一般以月、季、年為周期進行周期性的比較評估。而在具體層面,評估針對的是個體的行為人,與整體評估進行的統計相區別的是,個體評估應具有持續追蹤性,也即評估工作要非周期性的多次重復進行。類似于醫療機構對患者的診療,具體層面的評估應針對每一個體建立相應的評估檔案,在科學性與專業性的基礎上,貫穿于整個不良行為矯正過程,并延伸至不良行為的成因發現與不良行為的再次預防,進而使針對個體的整個不良行為預防矯正過程納入評估與監控。評估結果應作為調整矯正方式,改變環境因素的科學依據,并進而使預防與矯正體系不是一種經驗而是一種科學。同時評估所具備的記錄性與檔案性,使得接續運行的機構能夠在獨立運行的情形下形成一個整體,當然不可或缺的是接續運行機構的自我評估與記錄,當然這不是刑事訴訟法所抨擊的卷宗主義,因為自我評估與記錄運行的同時,存在另一主體相對獨立的評估機制存在,卷宗主義缺陷的核心點在于缺乏檢驗機制,顯然,在此這一缺陷顯然是不存在的。于是,在自評與他評,自我記錄與他方檢驗,獨立運行與接續合力,重復運轉與長效檢驗中實現對于未成年人不良行為有效的預防與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