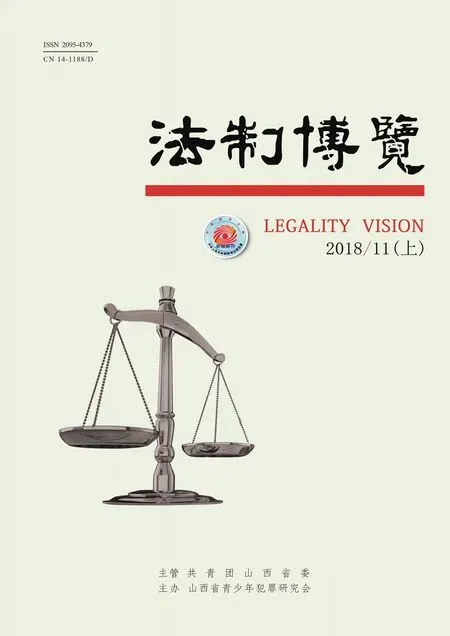商鞅“刑無等級”思想探析
潘衛東
青海師范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8
《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中認為:“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1]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一斷于法,重視法律的平等的思想,最早來自于商鞅的“刑無等級”。“刑無等級”作為商鞅的重要法家思想之一,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從“刑無等級”的局限性,其對象不包括君主、其目的在于維護封建統治及貴族的司法特權等角度看,從而更加全面了解“刑無等級”思想,同時也正確把握商鞅的法家思想。
一、“刑無等級”的概念提出
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并沒有出現真正的成文法,因而法律具有神秘性;此外,司法審判掌握在貴族手中,從而造成司法審判的隨意性。春秋時期的法家都極其反對貴族的司法特權,商鞅尤為突出。商鞅在秦國變法最大阻力來自于舊制度的受益者,如果繼續實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舊司法審判制度,就不能有效懲處對舊制度的維護者,沒辦法清除秦國變法的阻力。為了推行變法,突破了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商鞅從而提出“刑無等級”,無論哪一級貴族,只要犯法,和庶民一樣受到法律的懲處。商鞅的“刑無等級”思想的提出,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促進了秦國的變法的成功,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影響中國后世的法律相對平等的時代。
“刑無等級”就是“壹刑”,具體指刑法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刑罰不因個人的地位高低,財富的多寡,而因人而異。“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2]“刑無等級”對三代時期隱秘司法產生了重大影響。“法家把西周時期來源于隱秘司法且具有隨意性的法律特權變為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的法律特權,使法律特權具有法定性和確定性,貴族與平民一樣,都要依法定罪量刑,開啟了一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新時代。”[3]但“刑無等級”看似刑法的處罰對任何人都平等,而從司法實踐的局限性看其仍然是“刑有等級”。
二、“刑無等級”思想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觀”
首先,“刑無等級”的對象中并不包括國君。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無一例外都重視法律的平等性,但是卻很少有人將這種平等性用來限制國君的。一方面都承認平等性對于樹立法律權威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通過法律的制定,為國君的絕對專制所服務。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為了爭霸,都招攬人才為實現富國強兵。而法家為了宣傳自己思想,在權衡了利弊后,他們將國君排除在法律平等之外。乃至未來的國君也排除在外,如商鞅變法期間,面對太子犯法,本應該按照刑法處罰太子的,商鞅卻以“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為理由,最后處罰竟然是對太子的傅公子虔施刑,對其師公孫賈處以黥刑,太子什么處罰都沒有。由此可以看到在面對君主特權時,刑無等級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一視同仁。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說:“法家最大缺點,在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彼宗固言君主當‘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力言人君‘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然問法何自出?誰實制之?則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與廢,不過一事實之兩面,立法權在何人,則廢法權即在其人,此理論上當然之結果。”[4]所以,“刑無等級”在司法實踐上很難得到完全的貫徹實施。
其次,“刑無等級”的目的在于維護封建統治,加強君主專制,而不是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換言之,君權具有凌駕于各級臣民之上的特權,除了從實際的成敗和效用等方面考慮,它幾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而現代社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要求的“法治”,其重心在于以法律來限制權力,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合作基礎之上,而不是由一個垂直的權力所驅使,后者由于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者指令才得以實現。“封建社會里,法律是對君主負責的。法制的作用無非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維護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二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從法律上保證封建制度的長久治安。因此,在封建社會里,是君主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主,法律絕不可能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普遍的約束力。”[5]
最后,“刑無等級”并不是徹底的平等觀,在司法實踐中貴族有司法特權,即用爵位可以贖罪,從而減輕處罰。商鞅在《境內篇》中:“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6]商鞅在秦國變法時,確立的爵位的種種特權,其中就包括在法律的特權,可以用爵贖罪。在秦漢出土的竹簡文獻中,根據爵位等級來減輕刑罰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法律答問》中記載:“爵當上造以上,有罪當贖者,其為群盜,令贖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贖]宮。其它罪比群盜者亦如此。”[7]無爵位的王公貴胄子孫也享有贖罪的特權:“內公孫毋(無)爵者當贖刑,得比公士贖耐不得?得比焉。”[7]官吏也享有贖罪的特權:“吏從事于官府,當坐伍人不當?不當;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不當。”[7]另外因身份的不同,如父與子,士伍與商賈等,出現同罪而不同刑、同罪異罰的情況。“爵位的等級性超越和破壞了法律的平等性,使法又回到禮的等級框架中。”[8]更確切的說,這使法回到爵制的等級框架中。西嶋定生先生認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除奴婢、賤民之外,全體人民都被組織到爵制秩序中了。該秩序就是國家秩序,與皇帝支配的結構是一致的。”[9]無論法回到禮還是爵制的框架中,都是具有等級性的,并不是真正的“刑無等級”。
三、結語
法家商鞅看到其時代的社會動亂,皆有人們的私心而起,所以,主張通過重刑主義手段,實現“以刑去刑”的理想。趙敦華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價值律的重構及其現代意義》文章中認為:“中國古代價值律有四種,分別是金律、銀律、銅律、鐵律。而法家屬于鐵律,鐵律就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10]而“己所不欲,先施于人”思想正是迎合了封建君主加強其獨裁的需要。商鞅推行重刑主義政策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的思想恰恰相反,但法家所追求的“以刑去刑”和儒家的“無訟”社會,卻是殊途同歸,實現沒有刑法的社會。商鞅通過“刑無等級”政策的實施,希望廣大人民重視并擁護法律,從而實現“以刑去刑”。“刑無等級”本身就帶有不平等,卻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去遵守法律,而商鞅所追求“以刑去刑”的理想怎能實現。同時,在事實上,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讓君主放棄特權,遵守法律,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封建法本身就是特權法,“刑無等級”在封建時代只能是一種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