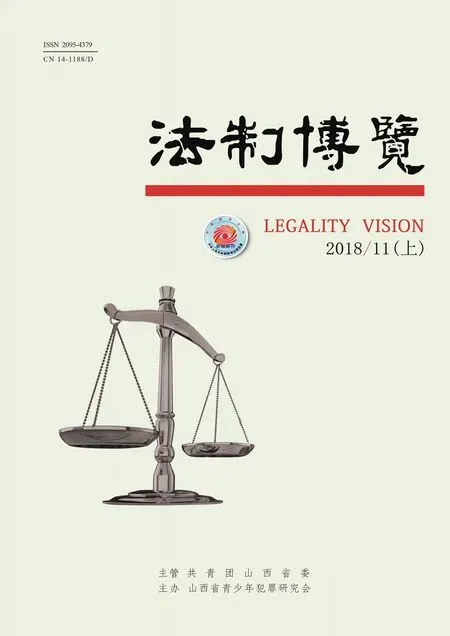淺析現有資本制度下的股東出資義務
張儀 如方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29
在資本制度設計之初,1993年《公司法》確立了嚴格的法定資本制來保證債權人的利益。但隨著世界眾多發達國家對注冊資本在債權人保護上的認識更新,我國公司資本制度也遵循了順應市場、逐步放寬管制、加強公司自主權的發展規律,因而在2013《公司法》改革確立了新的資本制度,采取廢除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等多個措施。對此,與股東出資義務密切相關的一系列改革而帶來的變化,也引起了不同聲音的質疑。而下文將在新的資本制度下,分別解讀在現有資本制度下股東的出資義務。
一、取消最低注冊資本與股東出資義務
2014年《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冊資額限制的規定,其規定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或全體發起人認購的股本總額,這個制度既包括一人公司在內的有限責任公司,又包括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說,在沒有最低注冊資本的限制下,公司的注冊資本完全由股東決定。在最低資本額度下,雖有法定最低資本額的門檻以及股東出資的最低底線,但如今取消限制,股東的出資義務沒有了最低底線,并不意味著股東出資義務的完全免除。再者,決定每一公司股東出資義務或出資范圍的并非法定最低資本額,而是公司自我設定的注冊資本。雖然有人質疑在此制度下,“一元公司”與“天價公司”的出現會對市場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但這對于股東來說,仍然附隨著哪怕一元的股東出資義務。
二、認繳資本制度與股東出資義務
新公司法改革下,股東的出資方式也由實繳制變為認繳制。一方面是公司成立時從實繳出資到認繳出資并可以再一定時期內“認而不繳”。另一方面,則是股東自行在章程中約定在一定期限內繳納出資。但兩方面的新變化,都不影響股東的出資義務。
首先,在公司設立時認繳出資仍然顯示了股東的出資義務。相較于實繳制度,認繳不要求股東即使履行出資義務,但只是給予了股東一個更長的寬限期,使得在某些情況下資本能夠更好地在市場中有效利用。并且,認繳行為的完成是以公司設立時股東之間所簽訂的出資協議為表現,其認繳的行為即承諾出具資產獲得公司股權的行為依舊表達了其承擔出資義務的承諾。
其次,依公司章程所確定的出資期限同樣不影響股東的出資義務。不僅在股東之間的契約關系中體現約定到期后繳納出資的出資義務,更是法律中規定在公司存續、清算、破產時股東不實際履行出資義務有著相應的制裁。所以,即便在認繳制度下,股東依然負有按照約定的出資義務進行實際出資的法定義務。甚至在實踐中出現的約定的無限期出資義務,也如同無期限債務一般,時間長短并不影響債務或是出資義務的存在與否。
雖然期限的不確定性不影響股東應負擔出資義務的存在,但是在出資期限的不確定性,卻也嚴重影響了債權人的利益。實踐中,不僅出現為了逃避出資而設定崎長的出資期限,可能直到公司解散終止,部分資產仍然未成為公司獨立財產;或是在公司經營存續期間沒有能力支付到期債務,而公司股東因期限未到期而未履行出資額或未足額繳納。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能否要求股東履行出資義務,或者說在無論是設定崎長的出資期限、臨時修改公司章程延長出資期限的情況下股東是否負有出資義務的問題都值得我們討論。
三、取消強制驗資與股東的出資義務
在未改革前,強制的驗資制度為資本真實原則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因為在市場中各商事主體提供真實資本信息的情況下,投資者才有直接判斷對方主體財產狀況決定是否投資的根據。雖然公司注冊資本不能代表公司的經營能力,但信息披露下資本真實是維持市場交易秩序的必要條件。加之,部分股東虛假出資或抽逃出資,卻能享有與正常履行義務的股東同等權利,也是為法律所不允許的。由此,對于股東而言,除了在公司章程約定下按期實繳的義務,也要承擔出資真實的義務。而取消強制驗資,也自然并不意味著允許股東們出資不實,而是將驗資檢查的關口后置,轉換管理方式,突出事中事后的資本監管,為公司事前成立提供便利條件。
同時,對于投資者來說,取消強制驗資制度也更加提醒了他們注意注冊資本所能反映出信息的重要性。對于股東來說,也意味著更加審慎的出資義務。因為沒有了強制的驗資程序,一方面是出資行為的監督從政府轉向股東自律。另一方面,則會導致缺乏程序下一份驗資報告,能夠證明出資義務履行完滿的證據。一旦發生糾紛,對于公司股東自行證明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之也可說明,若希望在公司取得相應的股東權利并獲得收益,股東也應當自覺履行出資義務,保證出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