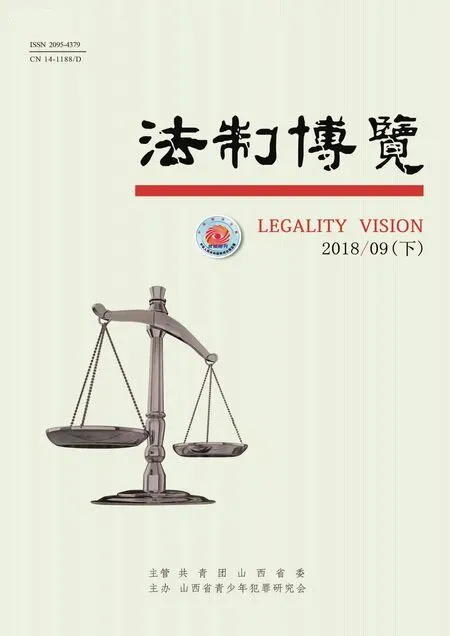電信詐騙犯罪證據(jù)體系構(gòu)建和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
許政強(qiáng) 茆仲義
平湖市人民檢察院,浙江 平湖 314200
近年來,我國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長(zhǎng),已成為社會(huì)公害,給人民群眾造成巨大的經(jīng)濟(jì)損失。[1]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犯罪具有非接觸性、空間跨度大、詐騙手段繁多,群眾防不勝防,預(yù)防和打擊難度異常巨大,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顆毒瘤,并呈現(xiàn)愈演愈烈之勢(shì)。特別是2016年8月以來,山東、廣東連續(xù)發(fā)生學(xué)生被詐騙后死亡案件,影響惡劣。防范和打擊電信網(wǎng)絡(luò)新型違法犯罪,事關(guān)人民群眾合法權(quán)益,事關(guān)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大局。
作為檢察機(jī)關(guān)公訴人,于2015年參與辦理李某某等十七人電信詐騙案。2016年6月,本院又受理陳某某等150人特大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案,該團(tuán)伙實(shí)行公司化管理模式,內(nèi)設(shè)回訪部、話務(wù)部、財(cái)務(wù)、人事行政、倉庫等多個(gè)部門,通過網(wǎng)絡(luò)、電視等平臺(tái)推廣相關(guān)減肥瘦身、美容豐胸產(chǎn)品,由接線員或者話務(wù)員負(fù)責(zé)一次性銷售及收集客戶資料,并將獲取的客戶資料輸入電腦系統(tǒng)進(jìn)行流轉(zhuǎn)。回訪部人員根據(jù)公司相應(yīng)的抬單劇本,互相扮演不同角色,互相配合進(jìn)行詐騙。案件被害人涉及全國各地一萬余人,涉案價(jià)值高達(dá)1.5億余元。該案范圍廣,金額大,取證難,本人提前介入指導(dǎo)公安機(jī)關(guān)取證,固定證據(jù),并審查起訴和出庭公訴上述電信詐騙案件,對(duì)于該類詐騙案件偵破、批捕、審查起訴、裁判中的難點(diǎn)以及注意事項(xiàng)進(jìn)行研究,以期對(duì)以后辦理該類電信詐騙案件有所指引。
一、電信詐騙案件的主要特點(diǎn)
電信詐騙在作案方式上傳統(tǒng)詐騙不同,是利用通訊工具(固定電話、移動(dòng)電話)、互聯(lián)網(wǎng)等技術(shù)手段,虛構(gòu)事實(shí)模板化,作案人員團(tuán)伙化,遠(yuǎn)距離、跨區(qū)域(甚至跨國、跨境)實(shí)施的非接觸式詐騙犯罪。
(一)詐騙手段多種多樣,且翻新速度快
詐騙方式系詐騙團(tuán)伙根據(jù)各地詐騙版本精心設(shè)計(jì),詐騙行為人人手一份,定期和不定期培訓(xùn)學(xué)習(xí),且根據(jù)經(jīng)濟(jì)、時(shí)事等情況,不斷更新,電信詐騙方式從以前中獎(jiǎng)信息、電話欠費(fèi)、冒名頂替、辦理證照,已更新到緊貼時(shí)事的補(bǔ)貼退稅、投資理財(cái),甚至銀行卡涉案(洗錢、販毒、涉黑)等,到冒充主任、教授等以推銷減肥產(chǎn)品為幌子,后虛構(gòu)被害人身體有毒素,不排毒可能得癌癥死亡等事實(shí),詐騙被害人錢財(cái)?shù)挠坞x于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新型電信詐騙模式。
(二)詐騙流程的標(biāo)準(zhǔn)化、模板化,職業(yè)化水平較高
前期通過電視、網(wǎng)絡(luò)、微信等媒體廣泛撒網(wǎng),到被害人主動(dòng)聯(lián)系,登記個(gè)人信息,行為人冒充各類身份聯(lián)系被害人并相互配合,后通過倉庫發(fā)貨,使用套卡取款轉(zhuǎn)移贓款等進(jìn)行詐騙。團(tuán)伙成員之間系按照公司化運(yùn)作,各部門之間分工明確,相互之間一對(duì)一聯(lián)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謀面,且相互之間稱呼化名。
(三)詐騙對(duì)象的廣泛性
電信詐騙行為針對(duì)的是不特定對(duì)象,通過短信群發(fā)、電話隨機(jī)撥打等方式來散布詐騙信息,但部分犯罪團(tuán)伙設(shè)計(jì)虛假商品宣傳網(wǎng)站,有的甚至通過媒體播放虛假廣告,在廣泛的群體中等待不特定的人上當(dāng)受騙。這種犯罪行為使得被害人的范圍更加廣泛,社會(huì)危害性更加嚴(yán)重。
(四)詐騙行為隱蔽性強(qiáng)
電信詐騙犯罪主要利用電話、手機(jī)、網(wǎng)絡(luò)等通信工具進(jìn)行遠(yuǎn)程詐騙活動(dòng),同時(shí),行為人從發(fā)布虛假信息到誘使被害人處分財(cái)物的整個(gè)詐騙過程均發(fā)生在虛擬信息空間中,行為人與被害人并沒有面對(duì)面接觸,是一種遠(yuǎn)程的、非接觸性詐騙,且一般不詐騙本地被害人,這使得案發(fā)后對(duì)行為人的指認(rèn)造成困難。行為人得手后一般使用銀行卡套卡及時(shí)將詐騙資金取出、轉(zhuǎn)移,并在被害人報(bào)案后,就不再使用用于詐騙的銀行卡套卡、手機(jī)卡等,使得警方查控、追蹤此類犯罪難度很大。
二、電信詐騙犯罪證據(jù)體系的構(gòu)建
(一)高度重視電子數(shù)據(jù)取證工作
鑒于電信詐騙的特殊性,要根據(jù)兩高一部《關(guān)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shù)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一時(shí)間和依法做好電子數(shù)據(jù)提取工作,包括詐騙的文字、語音聊天記錄、資金流向和被害人的信息等。
(二)及時(shí)做好現(xiàn)場(chǎng)勘查和扣押工作
通過現(xiàn)場(chǎng)勘查,詐騙團(tuán)伙一般均集中辦公,沒有相對(duì)獨(dú)立詐騙場(chǎng)所,就是聚集在一大間隔成的數(shù)個(gè)工作區(qū)域內(nèi)實(shí)施詐騙行為,相互之間對(duì)對(duì)方行為均知曉,沒有隱私和秘密,對(duì)證實(shí)行為人主觀上存有詐騙故意具有較強(qiáng)證明力。扣押的作案電腦、詐騙劇本、低價(jià)劣質(zhì)保健品等物證,通過后續(xù)偵查提取詐騙記錄,鑒定產(chǎn)品是否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等,以印證整個(gè)犯罪團(tuán)伙主觀上存在詐騙故意。
(三)全方位固定工商登記、銀行卡、物流、產(chǎn)品等證據(jù)
為逃避打擊,犯罪團(tuán)伙一般冒用他人身份注冊(cè)公司,公司實(shí)際注冊(cè)地和經(jīng)營地也不一致;使用購買的套卡收款,并及時(shí)轉(zhuǎn)移資金;使用虛假發(fā)貨地址和發(fā)件人;產(chǎn)品幾乎全部系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
(四)注重言詞證據(jù)和詐騙記錄細(xì)節(jié)審查
電信詐騙系非接觸性犯罪,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未見過面,電信詐騙次數(shù)和人數(shù)也眾多,務(wù)必對(duì)作案細(xì)節(jié)仔細(xì)審查,犯罪細(xì)節(jié)描述的一致性對(duì)證據(jù)認(rèn)定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實(shí)際身份和冒用身份情況不一致,被害人被騙時(shí)自報(bào)身份和實(shí)際身份也可能不一致,應(yīng)就銀行轉(zhuǎn)賬記錄、電話記錄等相關(guān)證據(jù)進(jìn)行收集和審查。
通過固定上述證據(jù),以證實(shí)詐騙團(tuán)伙主體的身份,在詐騙團(tuán)伙中作用地位(主犯、從犯)、詐騙的主觀故意、詐騙的客觀行為。
三、電信詐騙犯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
(一)管轄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fā)生地和犯罪結(jié)果發(fā)生地”。《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十六條規(guī)定“針對(duì)或者利用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實(shí)施的犯罪,用于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網(wǎng)站服務(wù)器所在地、網(wǎng)絡(luò)接入地以及網(wǎng)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及其管理者所在地,以及犯罪過程中犯罪分子、被害人使用的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所在地公安機(jī)關(guān)可以管轄。”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刑事訴訟法上的地域管轄以犯罪地為主,而電信詐騙屬于通過電信、網(wǎng)絡(luò)等媒介的財(cái)產(chǎn)犯罪,所以在電信詐騙案件中,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fā)生地和被害人被騙地。但因被害人遍及全國各地,一個(gè)地區(qū)的被害人可能僅有一名或幾名,且犯罪團(tuán)伙為逃避打擊,一般不詐騙本地被害人,本地公安機(jī)關(guān)受理詐騙團(tuán)伙案件幾乎為零,如何合理利用司法資源,打擊涉及全國范圍電信詐騙犯罪。本人認(rèn)為為節(jié)約司法資源,提高打擊效率,應(yīng)堅(jiān)持主要犯罪地管轄為原則,被害人所在地管轄為補(bǔ)充。
(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區(qū)別問題
電信詐騙案件也有產(chǎn)品,表象上也有交易行為,詐騙罪與民事欺詐在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也有質(zhì)的區(qū)別,如何甄別兩者區(qū)別,揭開詐騙的丑惡面紗非常重要。
在詐騙罪中,行為人意圖通過被害人履行獲取被害人財(cái)物,而自己根本不履行義務(wù),或者僅是象征性履行義務(wù),交付部分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僅是用來掩人耳目或迷惑對(duì)方的手段,這種表面履約行為并不能改變行為人整個(gè)行為的詐騙性。
在民事欺詐行為中,行為的主觀目的雖然也是為了謀取不當(dāng)或不法利益,但這種利益的取得,行為人是通過民事履約行為實(shí)現(xiàn)的,只不過這種履約行為是有一定瑕疵的,但總體上,行為人還是支付了一定對(duì)價(jià)的。
具體到個(gè)案,應(yīng)從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客觀行為,以及該犯罪團(tuán)伙的運(yùn)作模式、行為人假冒的身份、銷售產(chǎn)品是否為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資金流向等諸多方面來認(rèn)定。
(三)詐騙罪和銷售偽劣產(chǎn)品罪區(qū)別問題
銷售偽劣產(chǎn)品罪系通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為實(shí)施犯罪,電信詐騙罪中往往也有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的銷售,兩罪的行為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在司法實(shí)踐領(lǐng)域很容易將二者混淆,導(dǎo)致出現(xiàn)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對(duì)二者進(jìn)行區(qū)分,需要我們結(jié)合交易意圖、交易價(jià)格和被害人受騙原因及犯罪客體等方面進(jìn)行綜合評(píng)價(jià)。
(四)單位犯罪和個(gè)人犯罪問題
辯護(hù)人和被告人辯稱,詐騙團(tuán)伙公司規(guī)模巨大、管理規(guī)范,自己僅是普通員工,并有底薪,認(rèn)為詐騙行為系公司實(shí)施,和自己無關(guān)。本人認(rèn)為,單位犯罪,是指單位在正常經(jīng)營業(yè)務(wù)外存在犯罪行為,而非以為實(shí)施犯罪或主要為實(shí)施犯罪而成立。具體在詐騙團(tuán)伙成立的公司,往往一開始就是假冒他人身份成立公司,成立公司目的也主要為實(shí)施詐騙,在詐騙行為以外無其他實(shí)質(zhì)性經(jīng)營業(yè)務(wù),公司僅是詐騙團(tuán)伙華麗的偽裝。故認(rèn)定是否系單位犯罪,應(yīng)從詐騙團(tuán)伙公司成立目的、運(yùn)行情況等多方面分析。
(五)共同犯罪問題
電信詐騙往往由多人共同實(shí)施,其中以犯罪團(tuán)伙作案為主,電信詐騙團(tuán)伙的組織者、領(lǐng)導(dǎo)者等首要分子應(yīng)對(duì)所實(shí)施的全部詐騙犯罪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實(shí)踐中爭(zhēng)議較大、比較疑難復(fù)雜的問題是電信詐騙案件中具體詐騙行為人如何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電信詐騙的實(shí)行犯最常見的兩種行為模式是平行式和漸進(jìn)式,[2]漸進(jìn)式與平行式區(qū)別在于平行式多個(gè)行為人針對(duì)的是不同的詐騙對(duì)象,而漸進(jìn)式一般是多個(gè)行為人針對(duì)同一詐騙對(duì)象。
1、平行式詐騙中實(shí)行犯的刑事責(zé)任。平行式詐騙指多個(gè)犯罪人受同一人指使或多個(gè)行為人共同預(yù)謀實(shí)施詐騙行為,但多個(gè)行為人不是針對(duì)同一對(duì)象實(shí)施詐騙行為,而是各自針對(duì)不同的被害人,互相之間沒有交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對(duì)自己實(shí)施的詐騙行為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但對(duì)其他人實(shí)施的詐騙行為是否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則爭(zhēng)議較大。需要從是否存在共謀以及共謀內(nèi)容的明確程度、行為人事前或者事中的表現(xiàn)、是否具有共同分贓情況等方面進(jìn)行綜合判定。如事前無共謀,事中無幫助行為,事后未分享詐騙收益,不認(rèn)定為共犯。對(duì)于無共謀,也無幫助行為,僅為業(yè)績(jī)考核而分享部分詐騙收益,因無具體詐騙行為,也不認(rèn)定為共犯。
2、漸進(jìn)式詐騙中實(shí)行犯的刑事責(zé)任。漸進(jìn)式詐騙指針對(duì)同一對(duì)象,先由部分行為人實(shí)施詐騙行為,之后為了非法占有更多的錢財(cái),其他行為人加入繼續(xù)實(shí)施詐騙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應(yīng)從后行為人是否利用了先行為人造成的狀態(tài)、分贓情況、先行為人是否完全退出等多方面研究。如先行為人因?qū)嵤┣靶袨闉楹笮袨槿说脑p騙作了鋪墊,并分享全部業(yè)績(jī),對(duì)整個(gè)詐騙行為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如先行為人在后行為人加入后完全退出,并不分享后行為人實(shí)施詐騙產(chǎn)生的收益,對(duì)后行為人實(shí)施的行為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如后行為人和先行為人事前無共謀,也僅分享自己實(shí)施詐騙行為的收益,僅對(duì)自己實(shí)施行為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反之則承辦全部刑事責(zé)任。
(六)幫助取款行為人行為定性問題
在幫助取款行為的定性問題上,爭(zhēng)議主要集中在是詐騙罪,還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目前關(guān)于電信詐騙犯罪的多數(shù)裁判文書對(duì)此沒有進(jìn)行說理性的論證,而直接將幫助取款人的行為認(rèn)定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和實(shí)施共同詐騙的行為。[3]辯護(hù)人或被告人提出的意見主要有兩種:一是被告人僅知道幫助取款的錢來源不合法,但不知道所取的錢是何種性質(zhì),其主觀上不清楚所取款項(xiàng)是詐騙得來,其事先亦未與電信詐騙行為人進(jìn)行共謀,只為賺取少量傭金,幫助取款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共犯主觀要件,客觀上也未參與實(shí)施任何電信詐騙的行為。二是被告人幫助取款時(shí)詐騙犯罪已經(jīng)結(jié)束,成立既遂,被告人僅是在他人詐騙行為完成后,實(shí)施幫助轉(zhuǎn)移贓款的行為,被告人事后幫助取款行為不構(gòu)成詐騙共犯。
電信詐騙中,對(duì)于幫助犯證據(jù)審查與實(shí)行犯不同,其審查證據(jù)重點(diǎn)在于主觀方面,即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審查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重點(diǎn)審查的基礎(chǔ)事實(shí)主要包括:(1)通過幫助犯供述、同案犯供述及其他證據(jù),審查雙方之間有無共謀或者在實(shí)行犯共謀時(shí)幫助犯是否在場(chǎng);(2)是否曾參與過其他類似的詐騙犯罪;(3)辦理銀行賬戶(是否套卡、銀行卡數(shù)量等)、匯取錢款(是否在凌晨、有無偽裝等)的具體情況;(4)幫助者與實(shí)行犯是否系親屬、朋友或者是單純的雇傭等等。通過基礎(chǔ)事實(shí),特別是細(xì)節(jié)方面的審查來推定幫助者與實(shí)行犯是否具有共同故意,從而確定是否構(gòu)成詐騙犯罪共犯。如果確實(shí)無法證實(shí)有共同故意的,但其行為構(gòu)成其他犯罪,可以按照相應(yīng)的罪名定罪處罰。
(七)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和物流成本是否應(yīng)從詐騙金額中扣除問題
在審查起訴和庭審中,部分人辨護(hù)人辯稱部分保健品是真的,部分被害人陳述使用后有效,這些產(chǎn)品成本和物流成本應(yīng)從詐騙金額中扣除。本人認(rèn)為,各行為人主觀上均有詐騙的犯罪故意,所涉相關(guān)產(chǎn)品均系為實(shí)施詐騙而采購的低價(jià)劣質(zhì)或假冒產(chǎn)品,是為實(shí)施下一步詐騙犯罪所作的鋪墊,且各行為人通過虛構(gòu)事實(shí),讓被害人限于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購買產(chǎn)品而受騙,故假冒低價(jià)劣質(zhì)產(chǎn)品和物流成本僅是行為人詐騙的工具,金額不應(yīng)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