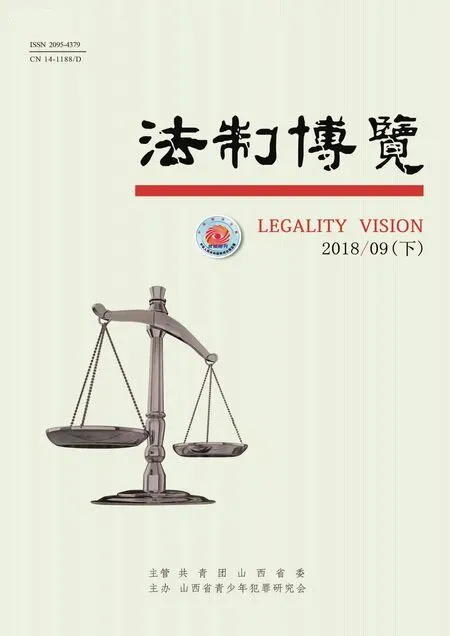我國死刑制度改革的憲法考量
徐 楠
鄭州大學法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一、世界范圍內死刑廢除的地區差異
人道主義在死刑改革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堅持人性和寬容的思想始終貫穿在我國傳統文化的演進中,但這與現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大相徑庭。縱觀世界范圍,保留死刑的國家主要多數東亞國家,其在歷史上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還有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和受佛教影響的國家。作為主要治國理念的儒家出于報應的觀念從未提出過廢除死刑。雖然東亞國家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開始本土化的實踐西式民主政治模式,但即便是傳統普通法系的新加坡至今也保留著死刑①。反觀廢除死刑的國家,其主流宗教是擁有共同的淵源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分析這些國家的分布區域上可以得出在西方文明發源和受其影響較深的地區,基于宗教文化傳統更易形成廢除死刑的制度的結論。研究死刑存廢問題應當本著相互尊重不同文明的差異,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的態度。
二、現代人道主義對傳統人本主義的繼承
我國傳統文化思潮中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為了保證統治者利益和維護皇權,并不鼓勵人們對自由、平等的追求。現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是死刑改革所需的思想基礎,而傳統的民本觀念雖然為死刑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卻也會演化為死刑改革的藩籬②。透過對死刑制度改革的研究不難看出刑法工具主義實際上與人權運動主導的廢止死刑理念存在不小的矛盾,與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矛盾格格不入。所以,對少殺慎殺理念的積極推行與強化有助于刑法擺脫工具主義的制約,培養對刑法謙抑性的理性認識,使司法在適用死刑時兼顧人道主義精神充分考慮其社會影響,通過對人的價值的強調和社會發展目的性的考量在實踐中推動少殺慎殺政策的貫徹落實。另一方面,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反映的人本主義精神由于其時代局限性與現代法治社會下推崇的人道主義價值觀不同。因此,立法和司法需要采取積極的態度來引導其發展。不僅要在實際改革進程中善加引導,而且要將少殺慎殺的核心理念與思潮轉化為人們可以接受的法治文化。
三、我國的刑事政策的變化
由于我國對逐漸普世的人權概念和相關法律標準進行了主動借鑒和有選擇性的吸收,使得我國的人權法律實踐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方面,中國對于吸納國際法標準采取了非激進的方式,沒有直接拿來主義的照搬別國的經驗,直接廢除死刑,而是采取了漸進的方式分別從立法、司法方面向國際接軌。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司法探索中,我國學界和司法界逐漸達成了“逐漸限制死刑,并最終廢除死刑”的共識③。另一方面,中國的立法和司法機關采取了結合我國國情,部分吸納國際人權相關規則。
我國的死刑政策經歷了顯著的變遷。曾經嚴打時采取的“從重從快”刑事政策逐步被“少殺慎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所取代,進而成為當前對于死刑的主導刑事政策④。從2006年開始實施的死刑案件二審一律開庭審理起,原先下放到省級高級人民法院的死刑復核權限自次年一律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死刑案件證據規則于2010年通過實施,隨后的《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都刪除了相當數量的經濟型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刑罰。另一方面,2012年的新刑事訴訟法又對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正當權益的保護進行了進一步強化⑤。死刑復核權重新收歸最高法院,基于最高法院死刑復核程序“少殺慎殺”政策原則的指導,通過改判、不核準等手段將“事實認定不清,程序適用有瑕疵”的案件判決及時糾正,同時也為各地地方司法部門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死刑復核權的收歸作為死刑改革的第一步,死刑案件的二審審理一律開庭等,保證了地方法院的刑罰權能夠受到來自最高法的有效監督。同時,為了進一步規范地方法院的采證過程,死刑證據規則應運而生。立足我國國情,目前保留死刑制度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基礎,但并不代表現行死刑制度完全合理,當代死刑制度也在不斷發展與改革當中逐漸形成了對于未侵害人身生命權利的普通犯罪行為應逐步廢除死刑,對構成死刑要件的犯罪行為在審判過程中保持嚴謹審慎的態度,保障并監督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等共識。在立法和修正過程中應正視制度中的問題并進行合理優化使死刑制度在發揮懲戒作用的前提下,盡可能達到教育目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作為先導的死刑改革必將成為我國刑法體系和社會發展的標志性豐碑。
四、我國死刑的憲法角度分析
(一)死刑與人的尊嚴
人的尊嚴的概念早期多來源于西方傳統哲學和基督教教義,我國憲法也對人的尊嚴給予了高度關注。有學者稱《憲法》第33條第3款為我國的人權條款,體現了對人的尊嚴的保護⑥。也有學者認為《憲法》第38條所指人格尊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權語境下的人的尊嚴等同和互換⑦。尊嚴從人出生起就存在,屬于人權的核心與本質內涵。人的尊嚴必須受到憲法的保護。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我國公民在行駛自己的自由與權利過程中,不能損害社會、國家、集體以及其他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可見,在不損害人的尊嚴的前提下,個人權利應當受到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利的限制。假如死刑破壞了人的尊嚴,那么就無需再討論其與憲法的關系,必須予以否定。對人的尊嚴在憲法中以文本形式進行積極定義難度較大,因此技術上采用較多的手段是消極定義,即以侵權的角度來定義人的尊嚴。例如,康德認為某個具有價值的事物被其他事物所取代,彼此之間就是一種等價關系。反之,凌駕于所有價值之上,找不到同等事物來取代,那就是尊嚴⑧。然而,生命權與人的尊嚴屬于兩個獨立的憲法概念,二者在內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并不相互捆綁⑨。死刑直接剝奪生命權,但并不一定會破壞尊嚴。有學者認為無論方式如何死刑本身就是一種殘忍的酷刑的事實是不會變的,而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就必須抵制無人性、殘忍、歧視性的刑罰⑩。不過隨著社會認知和技術水平的進步,在具體執行死刑過程中在手段上要更多的考慮人性化的執行,在承認且尊重尊嚴階段性認知水平的前提下,憲法應當有前瞻性的為以后新技術帶來的政策變革留出適當的空間。所以,憲法最終會出于保護人的尊嚴的訴求,在社會和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對死刑進行廢止。
(二)死刑與生命權
盡管死刑不一定會觸及人的尊嚴,但是一定會涉及對生命權的剝奪。雖然我國《憲法》中并沒有對生命權進行明確的規定,但作為人行使其各項基本權利的基礎的生命權必然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入憲,成為一項關于基本權利的兜底性條款,凡是憲法沒有明確規定的基本權利都可以納入此條款的保護范疇?。可見,《憲法》第33條第3款通過對人權的確認對生命權進行了規定。需要明確的是,憲法中人的尊嚴和作為基本權利的生命權的地位并不是同位階的。盡管生命權屬于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其他權利的保障必須以此為前提,不過憲法并不是無限制的保護生命權,其中第51條對公民行使權利做出了限制。盡管在一定意義上憲法對生命權進行了維護,不過個人基本權利并不是無限擴張的,自有其憲法界限。不包括法律保留原則在內,凡涉及到對公民基礎權利的裁判時,必須充分考慮并嚴格遵守比例原則,否則憲法將失去其應有的效力。在進行比例原則審核前期,需要先確認死刑能否得到憲法的肯定,比例原則必須與限制目的和限制手段直接掛鉤,并且限制基礎權利一定要滿足《憲法》第51條給出的有關標準與制度?。
五、結語
我國的刑事法律無論在立法還是司法上都取得了與國際接軌的實質性進展。人權理論為廢除死刑提供了正當性的解釋手段,在國際化的趨勢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相關改革進程。死刑雖然沒有必然牽涉到人的尊嚴,但事實上卻給犯罪人生命權造成不等同的傷害。因此有必要推動死刑的廢除,這既能有效維護憲法權威,也能讓民眾更加理解現代法治下的生命權內涵。人道主義價值觀是保留與廢止死刑的最關鍵價值因素,只有將人道性視為死刑改革過程中的核心理念,方能從根本上推動國內死刑制度改革進程,逐步降低死刑數量,以期最終達到限制甚至廢止死刑的目的?。但死刑制度經歷諸多變革最終成為對公平正義追求和罪刑相適原則的最高體現,死刑制度既和社會發展現狀相適應,又可滿足民眾樸素的心理期許。所以,當前保留死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順承了法制傳統,也延續了法律架構。只要有死刑的存在,就必須有類似審核程序以保證死刑不被濫用、誤用。無論是基于充分保障人權的必然要求,還是完善法律體系的客觀需要,繼續堅持和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確立規范統一的死刑標準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必然要求和偉大實踐。
[ 注 釋 ]
①劉學海.新加坡為何堅決不廢除死刑[J].商,2014(9):162.
②王宏玉,李明琪.對“嚴打”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58-63.
③趙秉志,王鵬祥.中國死刑改革之路徑探索[J].中州學刊,2013(6):46-52.
④同前注3.
⑤陳永生,白冰.死刑復核程序中辯護權之保障[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140-150.
⑥李海平.憲法上人的尊嚴的規范分析[J].當代法學,2011(6).
⑦林來梵.人的尊嚴與人格尊嚴——兼論中國憲法第38條的解釋方案[J].浙江社會科學,2008(3).
⑧[德]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5.
⑨陳征.從憲法視角探討死刑制度的存廢[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1):79-86.
⑩林占發.死刑刑罰觀的歷史追問和現實觀照[J].人民檢察,2011.
?同前注9.
?吳勇.論對憲法第51條的合理解釋[D].華東政法大學,2016.
?趙秉志.當代中國死刑改革爭議問題論要[J].法律科學,2014(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