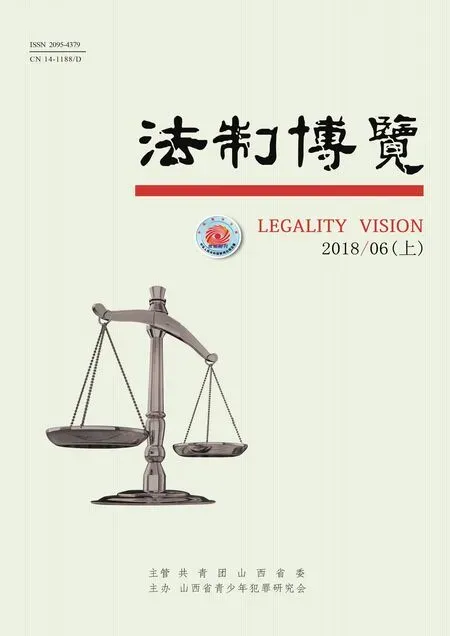夫妻一方所負合同之債的責任財產變遷考*
徐涵穎
蘇州大學,江蘇 蘇州 215000
一、婚姻法不能承受之重——《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思想內核之流變
《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自2004年4月1日施行以來,對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質疑就隨著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不斷被援引為法律依據而呈井噴之勢。相比于實務中對該條文的咎譽兩極,十三年后最高法出臺的《解釋二補充規定》和《通知》的補缺作用就似乎都唐捐了。因此本文首先運用時間順序法、綜合歸納法對《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體現中心思想的歷史沿革進行爬梳。
(一)階段:共同生活標準
1980年《婚姻法》首次就離婚后的債務償還問題專門作出了規定,其中第32條規定了夫妻共債共還的規則,另外該條文末句寫道:“男女一方單獨所負債務,由本人償還。”
為正確適用80年婚姻法的上述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7條中解釋了男女一方單獨所負債務的類型,分別規定有(1)夫妻雙方約定由個人負擔的債務,但以逃避債務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的親朋所負的債務。(3)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4)其他應由個人承擔的債務。
從以上條文不難看出當時對夫妻雙方意愿及夫妻內部關系和諧的重視。
2001年修訂《婚姻法》在第41條刪除了“男女一方單獨所負債務,由本人償還”的規定,另外在第19條第3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
可見,2001年婚姻法只專門規定了分別財產制下,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負債方所有的財產清償。至于第三人不知道該約定情形以及夫妻共同財產制下,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債務,是否由夫妻雙方負擔,則沒有明確規定。①
(二)傾斜保護債權人利益階段:身份標準
2003年《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自此,對夫妻一方所負合同之債的認定標準轉變為“身份標準”,只有在第三人知道夫妻雙方約定分別財產制的情況下,才認定為夫或妻一方的個人債務,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
不可否認,24條表述的確定是在結合當時的經濟社會生活和司法實際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債權人利益和夫妻另一方利益反復衡量和價值判斷后,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在邏輯性、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完成的,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夫妻雙方“假離婚,真逃債”串通欺騙債權人的行為。但同時也引發了次生的另一問題:從前是“坑友”,現在是“坑配偶”。盡管2017年《婚姻法解釋(二)補充規定》增加第24條第2、3款,強調虛假債務、非法債務不受法律保護,但因僅憑夫妻的身份就要向對方的債權人承擔債務,無端加重了夫妻未舉、債方的舉證責任。
二、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現世的“陰影”
本文在跟進查閱大量文獻資料的同時,也依托項目資源,進行了“夫妻一方所負合同之債的責任財產研究”的問卷調查,走訪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領域研究人員,同時整理和歸集了婦聯和相關團體個人的來信,其中求助與申訴書(格式信件)8封,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合憲性審查建議1封,具體案件的答辯狀2封,24條受害者心聲2封等17封飽受24條司法實踐困擾的來信。個中困擾夾帶著復雜情感實在難以一概而論,我們不知道的那些受困擾者仍掙扎在訴求無門的陰影中,有鑒于此,本文通過剖析來信中具有代表性的聲音加以考察和分析。
來信中不乏偏激的聲音:“從我們接觸基層反饋的角度而言,當下24條議題及其受害人群體的現狀,有一些帶有潛在傾向性的苗頭,不利于各方共贏皆大歡喜盡快建設性解決24條問題,尤其不利于營造喜迎十九大換屆之年的社會和諧穩定大局……”,也有些話語在大量情緒化的聲音中為我們樹立了理性思考的旗幟:“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最高院無須繼續背書24條,因為13年前出臺24條可以說并不存在錯誤。13年來的社會與經濟變遷劇烈,導致實踐中出現太多新情況、新問題,從婚姻破裂的方式,到民間借貸方式日益無門檻化的惡性泛濫,再到網絡賭博、色情泛濫等帶來的取證困難,甚至再到財產轉移方式日益多元化、境外化等等與轉型時代伴生的種種失序現象,才是問題激化的根源”其實,一般訴求也好,論文的批判也罷,都很少有結合法條出臺時背景的深入思索。事實上,在若干年前出臺第24條時,司法適用案例非常少,但是就從2013年開始,圍繞夫妻間的債權債務問題,產生了非常多的訴訟,甚至導致很多家庭家破人亡。
“最高院(兩通一補)有沒有解決24條存在的問題?沒有……實踐證明,這是強人所難了。壞人總不會承認自己壞,怎么證明人家是虛構債務,又怎么證明人家是違法債務?而且他們都自認債務存在,法官總不能憑自由心證就認為它是虛構的或者認為它就是惡意債務吧?證明不了,那么法官只能根據24條規則認定夫妻共同債務”。②“兩通一補”隔靴搔癢,沒有解決第24條的核心問題,即“舉證責任”問題。我們收集到這一類在司法實踐中的極端情況:即使被負債的配偶提供了銀行賬號流水、家庭支出等單據證明家庭生活支出全部都由其個人承擔,也被認為“不足以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被判決為共同債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如何認定的答復》中的共同生活標準,由于法律效力位階的問題,并不能終結《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負面影響。
三、未具名舉債夫妻一方與債權人利益的平衡木
爬梳夫妻一方對外負債不利后果的責任承擔分配所涵攝的立法理念,我們不難發現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背景下不同利益主體呈現出訴求多元化的趨勢和家庭財產模式的深刻變化,婚姻法體現出從維護夫妻和諧安定向維護市場秩序、社會經濟秩序、偏袒第三方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傾向轉變。這其中有“假離婚、真逃債”、破壞交易安全的社會現象受到遏制,市場秩序得到有效保護之“喜”,亦有剝奪不知情配偶一方合法權益,未具名舉債一方的訴訟權利難以窮盡之“憂”。
在平衡未具名舉債夫妻一方與債權人利益的探索中不求等量齊觀,但在理念上,區分夫妻共同債務與夫妻連帶債務不失為一種可落腳的模式。夫妻共同債務的本來面目即是基于夫妻共同共有關系產生的“共同共有之債”,它不等于夫妻連帶債務。就外部關系而言,共同共有之債是不可分之債,債權人只能要求全部共同共有人作為整體或其代理人對自己履行,共同共有人以其共同共有財產負責。每個債務人非對全部債務負責,而是所有債務人對全部債務不分份額地共同負責。就內部關系而言,共同共有之債的內部關系無須與外部的債務、責任關系保持一致,而是由共同共有關系的內部規則規定。③由此,一方面,這一思路能克服債權人在夫妻共同財產制下受到的額外優待——在夫妻共同財產制背景下,將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負擔的合同之債一概認定為夫妻連帶債務,夫妻雙方就應當以夫妻共同財產和全部個人財產對債權人負責。另一方面,也契合于在我國現行法中的其他三類法定共有關系中——合伙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遺產分割前繼承人對遺產的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以個人名義負擔的合同之債,其他共同共有人并不當然對該債務負擔連帶責任的理念。
在實踐中,2018年1月17日最高院發布《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已被修正,標志著其確立的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壽終正寢。
四、結語
家事案件審判應全面關注當事人權益,堅持以人為本,將案件審判由側重財產權益保護轉變為全面關注當事人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情感利益和財產權益。同時維護公序良俗,倡導文明進步的婚姻家庭倫理道德觀念,樹立家庭本位的裁判理念,不斷地從社會生活的客觀現實中去“發現”司法規范的意義代替對條文不加分析的流用。
[ 注 釋 ]
①“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案件維護健康誠信經濟社會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就‘婚姻法司法解釋(二)’有關問題答記者問”[EB/OL].(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2/id/2558120.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4月2日.
②<在中國,婚姻中的每個人都可能被背負巨額債務”>,2017年7月16日,游植龍律師,“南粵家事”微信公眾號.
③繆宇.走出夫妻共同債務的誤區——以<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為分析對象[J].中外法學,2018(1).
[1]曲超彥.夫妻共同債務清償規則探析[J].法律適用,2016(11).
[2]賀劍.論婚姻法回歸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財產制為重點.中外法學,2014(06).
[3]陳法.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之檢討與重構.法商研究,2017(01).
[4]繆宇.走出夫妻共同債務的誤區——以<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為分析對象[J].中外法學,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