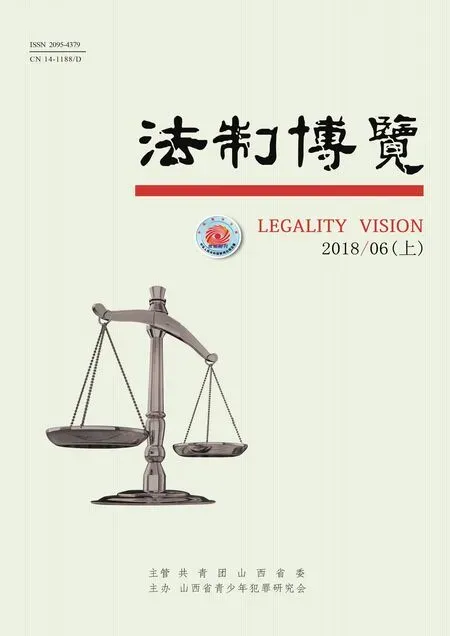淺析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在公司治理中的沖突與協調
曹 帥
四川坤弘律師事務所管理委員會,四川 成都 610000
從廣義角度分析,公司治理不但包含對公司內部事務的管理,而且也涵蓋對外部市場的各方面管理。從狹義角度分析,它只包含公司的內部治理機構與運作模式。在公司治理中,公司法是公司章程制訂的基本準則,而章程在一定意義上則屬于它的“實踐媒介”。然而在現實操作中,公司法中的強行性規范與奉行“高度自治”的章程之間總會出現摩擦,因此在當前的公司治理中,如何運用好“矛與盾”,協調好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之間的沖突,便成為當前立法者、審判者、律師以及公司管理層不得不重點考慮的問題。對此,筆者將從立法及司法實踐角度出發,主要探討一下“矛與盾”在公司治理中的沖突與協調。
一、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在公司治理中的相關理論概述
(一)公司章程的概念、特征及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公司章程,主要是指公司依法制定的含有公司名稱、住所、經營范圍、組織架構、經營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項的書面文件。公司章程主要具有以下幾方面特征:其一,公司章程主要囊括公司的組織、行為、權利等要素,對所有職員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定的束縛;其二,公司章程中也涵蓋公法的部分內容,它在發揮自治功能的同時,也有公法的元素填充在里面,例如,公司名稱、地址等都屬于強制性的章程內容。其三,公司章程只有在與強制性規范不沖突的情況下,才有優先適用的余地。
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占據著十分關鍵的主導地位。具體而言,每個公司都能夠在法律準許的邊界內融入更多的自治元素,從而制訂出符合自身實際發展情況的、具有個性化的具體實施細則。再者,它具有公示的效力。它記載的注冊資本、經營范圍等內容對于外界人們了解該公司起著“橋梁媒介”的作用。除此之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有關政府部門所監管的范疇。由此可見,公司依據實事求是的態度將經營運作狀況記載在公司章程上,非常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口碑與誠信。
(二)公司法規范的概念與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公司法規范,主要是指規定公司設立、變更與解散等方面內容的法律規范,它主要包括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其中,前者凸顯了公法的基本特色,有利于約束公司的具體經營行為,維護好公共利益與秩序。公司成立的根本目的,便在于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市場支配地位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深受利潤至上的觀念影響,各個公司之間或多或少都會發生利益的碰撞,進而引發沖突或分歧,因此這就需要公司法這把“法治的手”來加以約束,從而保障社會利益的相對穩定。
(三)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的聯系
在公司治理過程中,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都屬于促進公司事務管理的有效手段,也都屬于促進公司更加合法、合理的重要渠道。換言之,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就相當于“矛”與“盾”的關系,前者有利于實現公司的自治,后者有利于促進公司的合法、合理。具體而言,首先,公司章程具有一個填補公司法空白的優勢,可以在后者還未加以規定的情況下自由做出具體的制度安排;其次,公司章程在一定意義上有利于排除后者的適用,比如“……,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句話深刻表明公司章程具有意思自治的功能效果;最后,公司章程在現實操作中可以對后者進行具體、深入的細化解讀,由于一些法條較為抽象,因此公司章程可以將其具體化,轉變成更加簡單易懂、更加明確細化的內容,有利于促進公司內外部人員都可以理解其中的具體內容以及含義。總之,在章程與公司法的通力合作下,更有利于規范公司的行為。
二、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在公司治理中的沖突及具體成因
(一)積極沖突與消極沖突
積極沖突,顧名思義,屬于一種必須作為的沖突。而在具體的公司治理中則表現為章程中的部分內容與強制性規范存在明顯分歧。具體而言,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須嚴格遵循公司法中的強制性規范,這是法定作為義務,若違背的話,則極易導致法律沖突的出現。
消極沖突,主要是由公司章程制訂者的不作為引起的。具體而言,公司章程中的自治空間屬于公司法任意性規范特意留出來的自由空白,然而在現實操作中,諸多公司實際上并沒有充分利用這一權利,導致出現了公司章程大同小異、基本一致的情況。
(二)具體成因
首先,從設立公司的目標分析,公司章程所體現的是發起人的共同意志,它主要詮釋一個公司的具體目標,其中利益目標占據絕大部分比例。但是,公司法是基于國家整體意志而產生,它所代表的是國家對公司的預期發展目標的適當干預和引導,既包括利益目標,也包括公益目標,所以當這兩者極易造成矛盾或沖突。
其次,從調節方式分析,公司的經營運作實際上受市場與政府的共同作用力影響。但是公司章程屬于自由法則,而公司法屬于“強制干預法則”,兩者之間是相互對立的,所以當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在調節方式上有不同意見時也會導致分歧的出現。
再者,從公司發起人來分析,他們普遍認為公司章程只是設立公司的程序性步驟,即“走形式而已”,因此他們根本沒有重視過公司章程“這把利刃”,造成公司章程的內容出現諸多漏洞,比如,與實際情況相脫節,甚至與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相背離。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公司發起人缺乏法治意識,在章程制訂上“重形式、輕內涵”,極易造成公司治理法律沖突的頻頻出現。
最后,從公司法規定來說,“命令句”中的應為模式與勿為模式(如應當、必須、禁止等)常常屬于強制性規范,而“允許句”(如可以、選擇適用等)往往屬于任意性規范,公司發起人可以按照這些重要字眼制訂合法、合理的公司章程,但是實際上有些法律條文并沒有如此明顯的區別,如“陳述句”大都沒有“應當、禁止”這樣的字眼,這就需要他們在制定中認真思索這是“可為”還是“應為”。除此之外,法律有時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導致實際出現的問題無法可依,由此也會引發一系列的沖突與矛盾。
三、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在公司治理中的協調措施
(一)加強公司發起人的法治意識,做好章程制訂的具體工作
現階段,大多數公司發起人在制訂相關公司章程時,仍然是照搬其他公司的“章程模板”或者采取“填鴨式”制訂法,導致公司章程或多或少都與公司的實際情況存在脫節的狀況。對此,務必要從公司發起人這個“源頭”管起,提升他們的法治意識,引導他們做好章程制訂的相關工作。具體而言,首先應當明確公司章程的角色定位,它不單是設立公司所必經的環節,更是賦予股東或發起人更多“自由”的“權利載體”,所以發起人在章程制訂過程中應當要考慮的是如何賦予公司人員更多的自由,如何最大化地獲取市場利益。換言之,從律師角度出發,應當幫助章程制訂者提升法治意識,引導他們學會正確利用自身的權利,通過積極作為的方式去制訂章程,從而有效規避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沖突。
(二)從立法角度出發,嚴格把控好公司章程的“自由”邊界——自治規范
從立法角度來講,公司章程并非屬于一般的自治規范,更多的是一種“自治+強制”相結合的產物。具體而言,公司章程不能違背公司法的強制性規范,即在遵循它的前提下,可以變更或排除任意性條文,因此公司法在制訂過程中應當嚴格把控好“自由邊界”,否則會出現分歧。再者,當前階段,公司章程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便是由于它缺乏較為明朗的指導性規范,很多章程文本只是對公司法條文進行了簡單照搬的內容規定。對此,立法者應當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正,即應當在指導性規范中明確章程的自治界限,細化法律的最低防線。這不但有利于防止章程與公司法的沖突,而且也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健全私法自治的模式。
依據二分法,可以將公司法分成普通規則與基本規則。其中,普通規則是指公司內部具體規章制度的規則;而基本規則是指公司外部關系的規則。無論是封閉式公司還是開放式公司,都應當對前者“適當放手”,賦予更多的自由。而針對后者,應當依據強制性規則來加以規定。再者,從公司事務性質上講,在治理公司內部事務時應當適用大量的任意性條文,讓發起人可以自由斟酌是否適用,但對于外部事務特別是與利益掛鉤的事務務必要讓強制性條文“傍身”,這也有利于實現民法的公平原則。
(三)從司法實踐立場出發,做好兩者之間的協調工作
1.理論延伸
一般而言,法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依據具體的案例來進行斟酌與裁量,摒棄“教條主義”思想,即法官不能死板地只依據法律進行硬性裁判,同時也要摒棄“一刀切”的觀念,即不能單純認為和公司法不一致的都是錯誤的,同時也不能任意擴大公司章程的自治權,因此這就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把握好“尺寸”,做好公司章程與公司法之間的協調工作。具體而言,法官在遇到不同的案件時應當密切結合該公司的實際情況以及當時的市場背景與國家法律的變化,牢牢握好自己手中的審判權與裁決權,既要聯系實際,也要嚴格遵循法律相關規定,換言之,法官應從自身司法實踐的立場出發,努力“撮合”公司章程與法律在某些方面的“不和”,從而有效促使它們能夠真正“握手言和”。
2.案例分析
某有限公司由30個自然人投資設立,其中注冊資本為500萬。2015年6月,該公司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對章程內容進行了部分變動。但是,原告李某等12個股東對章程規定的兩條內容表示不服,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其中有爭議的章程內容如下:(一)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合法繼承人繼承部分股東權利與全部義務,同時也可出席會議,但必須同意由股東會做出的各項決議。(二)公司新增資本時,可以根據股東會決議優先認購出資。
該案件爭議的焦點主要有兩點:其一,股東權利能否被股東會決議與公司章程剝奪;其二,公司的股東會決議能否代替《公司法》第三十四條中所述的“全體股東約定”。首先,從第一個爭議焦點展開具體分析:根據《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可知,繼承人可以享有股東資格,但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律準允的前提下做出其他自治規定。然而,涉案章程只符合了“自治”,但卻不符合“法律允許”這個硬性條件。換言之,它表面上規定了繼承人出席股東會的權利,但卻限制了他在股東會的表決權,即要求他必須全部同意股東會所作決議,這導致他不能親自參與公司的實際經營管理,其股東權利實際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這與民法的公平原則嚴重相悖,因此該公司章程條款是無效的。
再者,從第二個爭議焦點進行深度挖掘與探析:涉案章程發起人根據《公司法》第三十四條:“……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的除外”之規定認為,該法條雖然表明所有股東可以對是否依據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做出決定,但卻沒有明令禁止公司以股東會決議的方式認繳出資,同時股東會決議也是屬于所有股東的整體意志,因此章程可以做出該規定。但是他卻忽略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原因如下:有限公司具有人合性與封閉性,為了保持股東的人合性與信任關系,公司增加資本時股東享有的優先認購權屬于他們天然的權利。但是股東會決議通過的條件是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法條規定是全體股東一致同意,由此可以看出前者更加寬松,因此也就無法確保所有股東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這也就容易導致大股東損害小股東利益的情況發生。而《公司法》正是出于保護小股東利益出發而對股東意思自治做出的限制。由此可見,該案件章程內容“(二)”與公司法相抵觸,因此
無效。基于上述意見,法院最終判決原告勝訴,被告承擔相應的訴訟費用。
四、結語
總而言之,雖然現階段公司章程與公司法規范作為“矛與盾”總是避免不了沖突與分歧的發生,但是只要嚴格把控好法律的真正價值取向,明確公司法的角色定位,找尋章程自治的具體界限,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兩者之間的沖突,促進它們的友好協調。
[1]胡培雨.公司法強制性規范的司法識別[J].企業經濟,2011(07).
[2]宋尚華.公司強制性規范的立法考量[J].石家莊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3).
[3]陳朋輝,鐘麗紅,周吟春.商法的強制性規范和經濟法的強制性規范比較分析[J].商場現代化,2013(11).
[4]王舒蒙.商法的強制性規范與經濟法的強制性規范比較分析[J].商場現代化,2014(29).
[5]馬天柱.相對強制性規范——保險格式條款規制的特殊技術[J].保險研究,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