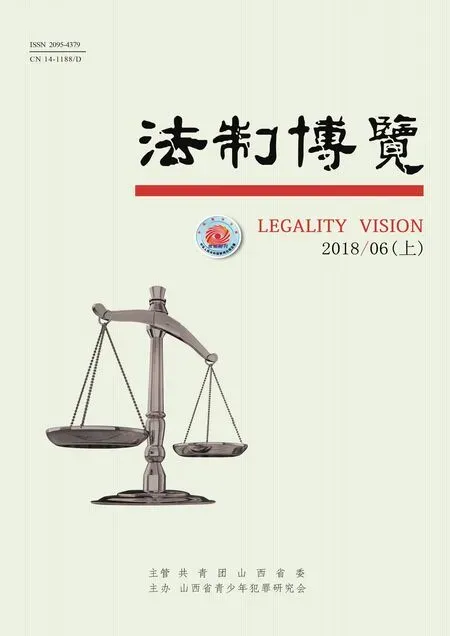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問題的探討
杜媛媛
西南科技大學,四川 綿陽 621010
一、人工智能產生的背景及現狀
人工智能在學界尚無一個準確統(tǒng)一的定義。但本文認為,可以將人工智能理解為通過對人類活動規(guī)律的研究和總結,讓計算機來完成需要人的智力才能勝任的工作。“人工智能”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美國1956年召開的達特茅斯會議上,會議討論了用機器模仿人類智能的主題,雖然沒有達成共識,但是為會議討論的內容起名為“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雖然我國人工智能起步相對較晚,但是發(fā)展迅速,2015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積極推進”互聯(lián)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中把”互聯(lián)網+“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列為重點行動,2017年人工智能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8年人工智能再入兩會,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再次強調人工智能給中國帶來的歷史機遇,這足以體現國家對人工智能的重視,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之下,未來我國或成為人工智能的領跑者。現如今的人工智能不止涉及計算機領域,在其他領域也廣泛涉及,比如部分媒體開始使用機器人寫作,繪畫機器人、作家機器人等也逐漸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物也正在被廣泛接受,其也在根據自己形成的價值判斷和邏輯思維實施創(chuàng)作,逐漸脫離人類的操縱。按照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趨勢,如何處理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已經成為不可逃避的社會問題了。(本文所討論的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指在忽略主體是否適格的前提下,即人類所創(chuàng)作的同類創(chuàng)作物屬于著作權保護的作品范疇)。
二、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權利的歸屬現狀
如今,對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的歸屬學界兩大爭議焦點分別是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物是否滿足成為著作權意義上的作品的條件以及人工智能是否能夠成為著作權權利的主體。
(一)人工智能是否符合著作權意義上的作品
我國著作權實施條例規(guī)定作品必須是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屬于文學、藝術、科學領域內的智力成果。根據傳統(tǒng)著作權觀念對“作品”的理解,“作品”必須是人類的智力成果。雖然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可以表達其自身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能夠達到對作品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但是人工智能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不能滿足現如今著作權法意義上對于作者人格屬性的要求,所以其創(chuàng)作物不屬于智力成果,不符合著作權意義上的“作品”。
(二)人工智能能否成為著作權權利的主體
根據著作權法的相關規(guī)定,我國著作權的主體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國家。如前文所述,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者必須是法律意義上的“人”,具有獨立的人格,能夠滿足著作權法對于作者人格屬性的要求,承擔法律后果。但是,現如今人工智能在我國無法獲得法律意義上的“人格”,所以其無法成為著作權權利主體。因此其創(chuàng)作物的保護也成為了一大難題。
三、探討現有人工智能著作權歸屬解決辦法的適用
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愈發(fā)普及,人工智能的法律保護制度也應該跟上其發(fā)展的腳步。英國最早意識到了計算機技術會對版權制度帶來威脅,其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人格和權利歸屬等進行了明確的規(guī)定。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進行保護的不止英國。美國版權局在1993年至少登記了兩份由計算機軟件創(chuàng)作的文字作品。而在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也對人工智能的法律保護問題十分重視,日本在《知識財產推進計劃2016》中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保護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未來是人工智能的時代,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物也會越來越智能化,那么其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問題也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今對于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學界有以下三點思路:
(一)著作權歸編程者或者單位所有
著作權設立的目的是鼓勵社會精神文明的發(fā)展,保護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作品,激勵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創(chuàng)作作品,發(fā)展與繁榮社會文化和科學事業(yè),對于人工智能來說,真正需要激勵的是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造者而非人工智能,正是有了這些創(chuàng)造者,才有了后來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產生,所以法律更加需要對編程者加以激勵,將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于編程者。若編程者是為了完成單位的工作任務,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才創(chuàng)造的人工智能,沒有單位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編程者無法做出人工智能;或者合同約定其為職務作品,該創(chuàng)作物就視為職務作品,其權利歸屬于該單位,但是編程者和人工智能可以享有署名權,前提是人工智能必須被賦予以人格。
(二)著作權歸使用者所有
人工智能雖由編程者完成創(chuàng)作,但是后期編程者或者其單位將人工智能售出,這時,權利就發(fā)生了轉讓,使用者此時擁有人工智能的所有權,且人工智能是在使用者的主觀意識下才創(chuàng)作作品的,所以權利應該歸使用者所有。
(三)編程者與人工智能共有
雖說人工智能是由編程者的創(chuàng)造才產生的,但是其創(chuàng)作物是結合了自身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所以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應該享有該作品的著作權,所以該創(chuàng)作物的權利歸屬就可以共同屬于編程者和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必須被授予法律人格,這種情況才能成立。即可以進一步探討是否屬于現行著作權意義上的合作作品。
以上三種情況對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權利歸屬的適用還需要再深入研究,本文認為,有學者建議為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單獨增設法律的行為是行不通的,我們只能在現行著作權體制下討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歸屬問題,至于人工智能能否被賦予法律人格而成為著作權意義上的主體,本文認為,是不可以的,著作權主體既要能夠享有著作權,也要在發(fā)生侵權行為時承擔法律后果,而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它可以創(chuàng)造出“作品”,但是在侵權行為發(fā)生時,它無法承擔相應的后果,其后果只能由與其相關的編程人員、單位或者是使用者來承擔,綜上,本文認為,人工智能無法被賦予法律人格而成為著作權意義上的主體。結合目前實際情況來看,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還是歸屬于編程者、創(chuàng)作單位或者是使用者比較適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四、結語
雖然本文認為暫時還不適宜賦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但是我們不能單純地認為人工智能不能獨立創(chuàng)作出作品,正如有學者所說,在“阿爾法狗”與圍棋天才柯潔的大戰(zhàn)中以柯潔的失敗告終,雖然阿爾法狗是由人類創(chuàng)作出來的,但是其創(chuàng)作者與柯潔對戰(zhàn)也未必能夠戰(zhàn)勝柯潔。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作有一天可能會達到人類無法企及的地步。也正因如此,霍金警醒我們要正確使用人工智能,不能讓它無節(jié)制地發(fā)展,否則有一天人工智能會統(tǒng)治人類,帶人類走向毀滅。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們也不用擔心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問題了。在當下,我們亟待解決的就是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的歸屬問題,其著作權歸屬問題的解決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們的法律也應該未雨綢繆,避免在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著作權問題泛濫。法律必須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歸屬做出約束和保護,以尋求其為科學文化事業(yè)的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1]王遷.著作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35(05):148-155.
[3]孫那.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成果的可版權性問題探討[J].出版發(fā)行研究,2017(12):17-19+61.
[4]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認定[J].知識產權,2017(03):3-8.
[5]呼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歸屬[J].現代交際,2018(02):61-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