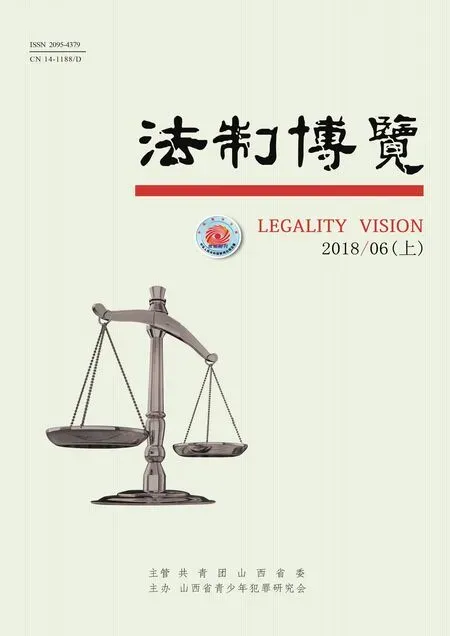試論民法總則設置商法規范的限度及其理論解釋
李佳冶
長春理工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民商合一的重點在于民法典總則適用于民商事關系,包括公司法、保險法、破產法、票據法等特別法。民法學者一般認為,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總則是否能夠規定商法的一般性規定,或者說,對民商事關系一體系適用,應當在民商合一的體例制定民法典總則,因此在民商合一體制下制定民法典,構建一個統一的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民法總則設置商法規范的限度
(一)民法總則對商法規范的抽象能力
民法總則制定是采用了抽象技術來提起公因式,這就對民法各部分進行歸納,并進行整合。民法總則立法者需從個別到普遍進行歸納,避免總則缺乏實用性。同時,民法法典的編撰需要根據立法形式對民法體系整合,而不是創造。因此,如何對商法進行整合,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總則,這也是民商法學界爭論的焦點。在進行歸納過程中,需要在此基礎上,民法典與商法規則的共通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民法總則對抽象能力并不是一個具有確定性概念,并由民法總則所對應的具體規范。如果在選擇商法的規范程度抽象化立法形式,并借此形成民法規范和基本商法規范,形成一個完整的商法規范體系。可以說,立法規范式并不反對民法典中的商事關系的司法規范。其中,民法典含及其抽象更加一般性。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第二層次的商法,需要受到民法總則的限制,就缺乏一定的邏輯性。如果商法總則缺乏通則,民法總則提供的民商關系適用于規定性方法。
(二)決定民法總則抽象能力的因素
民法典中主要囊括了總則和無總則模式,這兩種模式已經成為我國民法典的選項。關于民法典的總則及各部分的抽象,其中關于抽象化的商法規范及抽象化的困難化,需要進行研究,對此,需要進行三個判斷:一體化標準。商法規范和民法總則具有體量的相關限制,從比較角度來看,民法典需要借助抽象化和概念體系對人、物、權利構件等章節做到極致的優化。雖然如此,這些制度具有生公因式因素;立法技術的輔助使用,來發揮商法通則的優勢。雖然《民法總則》的章節編排中包含著主要的內容板塊。在商法總則外部下受到的抽象具有雙重的質疑,在總則中只有依賴剩余技術獲得正當性基礎。
二、民法總則設置商法規范限度的理論解釋
(一)民商法基本原則
公共秩序和權利濫用等民法基本原則,需要在民法總則,自不待言。但有學者認為商法主要包括了民法的基本原則,不需要進行總則抽象。因此,需要指出,一些基本原則是商法存在著“同名不同義”的現象,主要包括了商業營業自由等內容,比如由意思主義轉折到外觀主義,但在實際中,外觀主義在民法和商法具有很多不同。
(二)民商事主體
法律主體關系是法律構建的主體,比如缺乏主體制度。《民法總則》規定了自然人和其他組織構成了民事主體,體現出了民商事主體統一趨勢。民法總則對于民商事件具有主體的抽象化傾向,需要界定法律的適用價值,不應考慮進民法總則。通過構建一個民商主體制度,而對于商事主體的個性化分析,而商法總則需要抽象化,需要進行商事法固定。
(三)民事權利客體
《民法總則》規定的客體包括物權、有價證券等,客觀意義上的營業需要列入權利客體,需要起草民商合一的商業主體營業。因此在財產規范、客體構件等方面具有規則屬于商業法特殊情況,并為商法做出具體規范。就立法而言,商事領域的新型權利及客體的民法原則。實際上,商法在財產關系上已經實現了抽象權利作為行為主體的轉變,需要進行擴展,即便民法作為主體民事權利,需要調整商業關系的主權,同時也具有象征含義。在構建“民法典+商法通則+商事法”過程中,民法典總則需要對商事環境的指導性及適用性時,從比較方法來看,需要進一步統一民法和商法。
(四)法律行為和商行為
民商合一是民法決定性環節,從整體角度來看,法律行為對于商業行為的適用價值。但在法律行為的效力適用商業活動,但是法律行為效力適用于多種商業行為,法律行為的效力規范體系需要根據多種商業行為進行規范,按照民法總則來抽象化[1]。
三、結論
綜上所述,商法自身的體系化,需要由商法的基本法決定。在此基礎上,民法總則對抽象能力并不是一個具有確定性概念,并由民法總則所對應的具體規范;同時,民法行為主體的轉變,需要進行擴展,即便民法作為主體民事權利,需要調整商業關系的主權,同時也具有象征含義。因此,需要構建一個民事法律框架,來實現民事規范化體系。
[1]匡凱.民法科學性的歷史演進與現實回應[D].湖南大學,2016.
[2]蔣大興.論民法典(民法總則)對商行為之調整——透視法觀念、法技術與商行為之特殊性[J].比較法研究,2015(0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