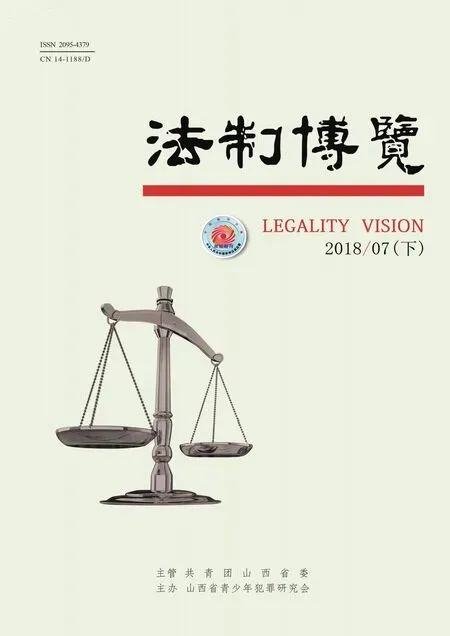知識共享協議的應用現狀及措施分析
陳麗麗 周小音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2001年在美國本土成立了一個新的維護知識產權組織,并于2002年發布了第一版本協議,稱為“Creative Commons License”,即知識共享協。我國雖早已在200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知識共享協議大陸版官方會議,且會議宣布知識共享協議2.5版本正式在中國啟動,并且隨后不斷推出新版本,但由于各種原因知識共享協議未能在我國廣泛使用。知識共享協議是一個相對寬松的版權協議。它通過作者對四種權利(即署名、非商業用途、禁止演繹、相同方式共享)的選擇和組合,同時讓使用者可以明確知道所有者的權利,從而達到不容易侵犯對方版權的目的以及作品可以得到有效傳播的目的。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降低了創作的門檻,但同時增大了使用者的侵權風險。除非有把握“合理使用”或者“法定許可”,但一般人對于諸如“合理使用”的判斷較為困難。因此,要低法律風險地利用已有的素材進行創作就得先取得作者授權,但授權過程于網絡時代下則顯得繁瑣。以知識共享協議為例探討的知識共享模式采取自愿和自由選擇的方式,在鼓勵使用其作品時保護他們的作品——即宣布“保留部分權利”。
一、知識共享協議域外應用現狀分析
(一)中國臺灣應用現狀分析
知識共享協議于2003年被引入臺灣,并被命名為“創用知識共享協議”,由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咨詢科學研究所”提供經費的支持。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臺灣通過四大軸線運作,即基礎建設、咨詢服務、合作推廣和國際交流來完成知識共享協議的本土化。
經過幾年的推廣,在臺灣,使用知識共享協議的機構正在不斷地增加,在私人機構中,臺灣的“臺灣生命大百科”、“臺灣棒球維基館”以及一些開放式課程等都有應用,同時臺灣還通過開放攝影展、讀書會的方式,向公眾宣傳知識共享協議。在公權力機關中,則更加把運用重心放在了教育領域和政府信息公開的領域,如臺灣的“教育部”“智慧局”“臺灣美術館”都在其網絡平臺上開始使用知識共享協議,其政府咨詢網上還專門開設了“創制知識共享協議專區”,并正在努力將知識共享協議運用到政府相關文件公開,從而使知識共享協議得到官方的認可。
知識共享協議在臺灣的應用過程中,也暴露了不少問題。第一,網站中知識共享協議的標識比較隱蔽,不容易被使用者發現,同時還出現了授權標志不統一的情況,導致眾多的使用者在尋找標志和認定標志上都出現了一定的困難。第二,一些網站改版或者合并以后,網站原有的資料授權標識消失或者失效,需要重新認定,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知識共享協議授權中“非商業用途”和“禁止改作”被作者們大量使用,這將不利于對作品的再創作。
(二)國際應用現狀分析
1.知識共享協議在美國的應用現狀
知識共享協議在美國的政府信息公開中被得到了充分地應用,從2014年開始,美國聯邦政府便表示支持在一些開放的政府文件上使用知識共享協議。其中,美國勞動部在執行促進就業輔助計劃時,便采用了知識共享協議-4.0-姓名標示的形式,向公眾發布相關的素材,而美國的教育基金協會推廣的職業進修課程,也是采用知識共享協議-3.0-姓名標示-提供公眾再利用的形式進行共享。美國的政府文件開放計劃是有法律基礎的,即在美國的著作法中,政府的著作不受著作權的保護,但即使這樣,依然會出現政府文件是專屬授權的形式,而通過知識共享協議的改進,則促進了政府文件公開從專屬授權轉變為非專屬授權,從而能夠真正的實現政府的信息公開。
在民用方面,美國國家畫廊采用上傳每幅畫的高清圖像到網絡上供其他人下載和欣賞,并且只限定了姓名標示這一方式。美國國家畫廊通過這一方式,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優秀的作品,且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質量較差的文化遺產圖像。而在教學資源運用方面,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等相繼開設了MOOC,并且開始逐步使用知識共享協議,推進了先進教學資源的共享,打破了由于學校資源的差距造成的教學資源分布不均,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優質的教育。
2.知識共享協議在德國的司法運用
德國是在2016年引入知識共享協議3.0的,并且將該協議在德國得到廣泛的應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不僅停留在傳播層面,而是深入到了司法層面,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在德國2010年一個關于知識產權的案件中,原告作者以署名-相同方式共享的形式分享其一幅作品,卻遭被告不署名便隨意公開使用。在這起案件中,關鍵點就在于知識共享協議是否有效,而德國法院則通過對《著作權法》的解釋承認了知識共享協議的有效性,從而使被告敗訴。
該案表明了,知識共享協議與著作權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相對于著作權法,知識共享協議形式更加簡潔。從德國對知識共享協議在司法層面的應用表明,知識共享協議是可以與現在的著作權法相互融合,互相補充,從而在保護版權的前提下推動知識的共享。
二、知識共享協議在中國的應用現狀及措施分析
本文結合我國現實國情,認為知識共享協議在我國的應用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并針對現狀出現的問題提出了相關解決措施:
(一)應用現狀
1.適用領域具有局限性
在中國,知識共享協議的使用者主要是因為從事創作類事務而了解知識共享協議,其中最多的為從事攝影而了解知識共享協議,這些作者的作品多發布于類似圖蟲等受到知識共享協議保護的網站。使用者普遍而言比較傾向于使用LOFTER、微博等社交軟件,并有一定的活躍度。同時,對知識共享協議有一定認識的或者很了解的一般為美術、音樂及新聞傳播等與藝術創作有關的專業。由此可見知識共享協議目前在中國的適用范圍主要局限于攝影、音樂等藝術創作小圈子內,對于不涉足藝術創作領域的使用者而言則難以接觸并了解到知識共享協議。
2.本土化不足
知識共享協議最初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應對美國的版權保護過甚。因此,直接地生硬地引進中國會造成本土化不足的原因。首先表現為知識共享協議翻譯的較為生硬且其中術語較為晦澀難懂。知識共享協議對于普通的使用者而言可能需要詳細閱讀2-3次方能看懂。這便是協議自身引進中國進程中產生的翻譯問題和推廣問題,導致本土化不足的問題。而對于互聯網用戶而言,不能快速看懂的知識共享協議一般是不會特意耗費較多的時間去鉆研,而只會隨意地選擇知識共享協議的任意一種模式,這就無法實現知識共享協議的應用初衷;其次,中國民眾知識產權意識薄弱,對于此部分民眾而言,加強其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才能夠對其進行知識共享協議的推廣實踐。
3.普及程度低
目前在中國,應用知識共享協議的平臺較少,且存在一些平臺即便應用也未充分介紹解釋知識共享協議。這說明知識共享協議普及程度較低,大多數民眾并不了解知識共享協議,還有較大的普及空間。
(二)解決措施
1.提高知識產權意識
從社會意識層面來看,我國缺乏尊重知識產權的整體意識。在著作權領域有兩種主要表現形式:第一,缺乏保護自身合法享有的著作權的意識;第二,缺乏對他人著作權的尊重。知識共享協議的引入和在我國的適用缺乏良好的意識層面的基礎,因此應該提高知識產權意識。
2.擴大宣傳,提高普及度
首先,擴大組織規模,策劃更多知識分享的活動,讓更多的人有意識地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其次,知識共享組織應擴大分享人群,有目標地發展用戶主體。知識共享協議的推廣不應局限于藝術家或科研工作者,通過開展“走進高校”系列活動,發動校園的力量。最后,知識共享組織應與政府部門合作,與各大機構合作。爭取得到政府在官方上的認可和支持,與其他科研機構及圖書館建立網絡平臺。
3.在司法層面承認知識共享協議的效力,完善救濟途徑
沒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規則是不完整的,知識共享協議在當下的中國也面臨著相同的困難處境。一方面,當權利人依據知識共享協議的相關權利受到侵害之時,其很難尋求法律救濟。在訴訟程序中,我國并沒有承認知識共享協議作為一種標注版權的協議的司法效力,因此,一旦使用知識共享協議而存在糾紛時,如何認定知識共享協議的效力將成為糾紛解決的前提,這樣就使得權利狀態不穩定,不利于知識共享協議的廣泛適用。綜上,應當在司法層面承認知識共享協議的效力,完善救濟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