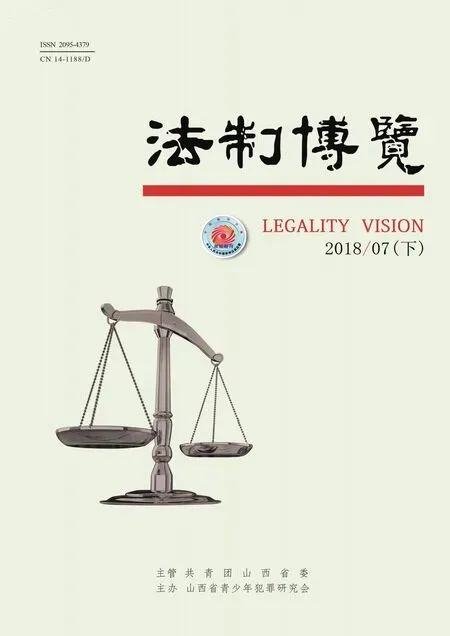電影《十二公民》引發的對陪審制度的思考
付 睿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北京 100083
觀影完由美國經典律政作品《十二怒漢》翻拍的電影《十二公民》后,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所有陪審員走后留下的那一張空蕩蕩的桌子。而筆者想那可能就是在我心中最原始的陪審制度:陪審桌上的人不斷在換,始終不換的卻是那一張桌子,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桌子會不斷破舊但卻愈顯深沉。
“中國是否適合陪審團制度?”對于這個問題,筆者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從最表層來講,存在即合理——能在美國得以運作數百年而今依舊不斷在完善,拋去國家意識形態的對立,就這一點而言對于司法剛起步的我國更應該得到深刻的,尚且不管現實中陪審制度適不適合我國國情,但至少從理論層面上值得我們法律人深刻思考和研究。
陪審員是以證人的形式出現在司法審判中的,其主要功能是協助法官實現審判的準確性。我國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構建人民陪審員制度,試圖防止法官在審判中的恣意妄為,以達到提高司法的民主化的目的。但在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讓人民參審僅僅停留在形式層面,因此對于造成人民陪審制度形式化現狀的問題探究以及成因分析至關重要。陪審制度的制度框架設計雖然存在細節上不完善、實踐中較難落實等問題,但筆者認為,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問題大多還是體現在人的層面即參與陪審的主體——人民陪審員。
得出中國適合陪審制度的結論,筆者并沒有經過多少法律方面的思考,而僅僅是從人性的角度贊同陪審制度的存在。筆者想當法律涉及到尤其有關決定公民的生命權是否保留時,法學的意義就立即與其他學科有了質的區別,這個時候不是因為你是專家,你是權威,就代表你擁有了絕對優先于他人的判斷生殺予奪的權利,而恰恰相反,此時的判斷權反而要下放到其他任何一個不具有專業素養的普通主體手中,為最基礎的公平正義,也為最深刻的人性。
陪審制度在中國可以施行,但得加一個前提:過程漫長。因為最理想陪審制度對即將要駕馭它的主體任意一名普通公民來說提出了最為嚴格的標準,這個標準不亞于共產主義中對于人民的標準,因為無法保證12個隨機挑選的公民中沒有一個出自私心得出最后的結論?對最優秀的法官我們尚不能給出百分之百的保證,又更何況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單從這一點出發,在如今陪審制度運用最成功的美國,其發展也不過處于最初級的階段,而且這一制度改不得也急不得,因為其質量的質提升完全源于公民素質質的提升。
當然也要自我批評,筆者之前的很多觀點都是以絕對理想化和對公民素質極高要求的基礎上提出的,理論上可以進行批判,但一味盲目的批判并得不出任何的現實意義,所以必須要從現實法學的角度來研究能夠符合中國“國情”的陪審制度是什么樣子。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問題發現和改革探討是目前司法界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但此課題并不是個孤立存在的,而和經濟發展狀況、司法環境、訴訟制度、人民素質有著緊密的聯系。借鑒英美法國家的陪審制度對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提出修改的參考意見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與此同時立法者還需要充分立足我國的國情和目前已成型的司法體系。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的出發視角有別于其他制度改革,它從本質上是一個自民眾出發而向立法體系推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司法的強制性屬性很難發揮其在其他立法改革中發揮的作用。陪審制度改革真正達到預期效果的必要前提是我國人民陪審員隊伍整體素質的提升。素質的提升并不僅僅是一句空話,而是一個需要長期立足的過程。人民陪審員選于民、用于民,因此人民陪審員對于整體素質的提升與我國民眾法律素質的水平有著直接的關系。
本文只是就分析問題和制度改革探討方面作出了相應的回答,仍存在諸多不足之處。目前司法界較熱的有關人民陪審制度的存廢之爭,筆者認為過多糾結于此并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立法者應當優先考慮如何布局長足的人民司法教育進程,如何在人民整體法律素質得以提升的前提下篩選出真正適合人民陪審員角色的公民,如何能讓公民主動并且充分投入參與到司法審判的過程,如何增強人民陪審制度的公信力,如何實現人民對有陪審員加入的審判的過程和結果的監督,如何達到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促進司法的整體進步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