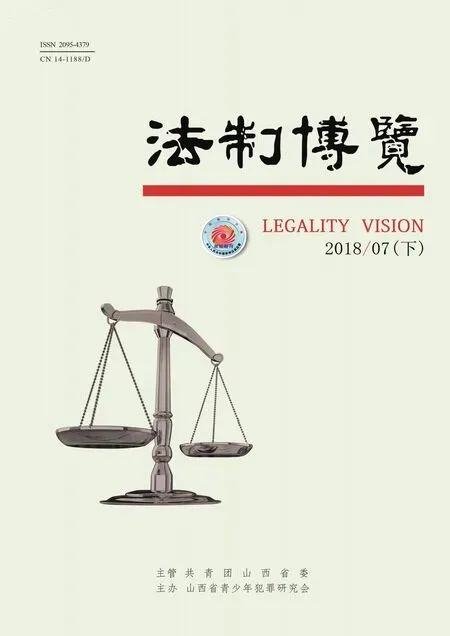論敲詐勒索罪的既遂認定
倪杰嶺 李家琛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0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公私財產被侵犯的狀況日益凸顯,公民自身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利不斷受到侵害。而侵害公民公私財產的犯罪,又在不同程度上體現著不同權能在受到挑戰。對侵犯財產類案件,大致可以分為挪用型、毀壞型和占有型三類。敲詐勒索罪作為占有型的典型代表,在其中占據了較大比重。在司法實踐中,此罪有既遂和未遂之分,但區分的標準卻各有千秋,本文試就此問題做出探析:
一、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一)客觀構成要件
敲詐勒索罪要求以非法占有為主觀目的,要求對被害人存在要挾或者威脅的方式強索公私財物,數額上構成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索取公私財物的要求。要挾或者威脅的行為方式,具體而言是指能夠引起被害人或者第三人心理恐懼的措施,此種行為方式多種多樣,可通過各類通信方式進行傳輸,可行為人自身去表達,也可通過第三人為媒介去進行信息的傳遞,可以是明示或者默示。不管基于何種方式方法,只要行為人對他人的財產權利確實造成了侵害的結果,且符合數額或多次標準,即可認定為敲詐勒索罪。
(二)主觀構成要件
對于行為人做出敲詐勒索行為時的主觀目的,在各國的刑事司法領域存在差異,部分國家并未對該行為的主觀目的做出特別規定,即以實施特定行為作為既遂標準。但以我國為代表的國家,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進行了明示,要求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若不是基于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主張的權利,如債權人以不償還債務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二、敲詐勒索罪的既遂認定在我國刑法學者中的分歧
關于敲詐勒索罪既未遂的認定,我國司法界進行了充分討論,但學者對此問題的爭論始終未停止過。了解不同學者間的觀點看法,對于敲詐勒索罪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刑法修正案后某些學者出版的著述來看,一些學者認為:被害人在恐懼心理的影響下,對自身財產進行了處分,而行為人一經取得該財產,就可認定為行為人敲詐勒索罪的成立。但是此種學者觀點也存在特殊情況,若被害人不是在恐懼心理的影響下處分了自身財物,而是出于憐憫的心理狀態向行為人提供了財物,或者是被害人出于配合司法逮捕而處分自身財物,且行為人在警察的控制范圍內,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拿到該財物,此時顯然不能認定為犯罪的既遂。
(二)另一種學者認為,區分敲詐勒索罪既未遂的
標準是具體的犯罪行為是否最終得逞,但此種是否得逞不單單要求犯罪行為實際成功,以及不法財產的實際取得,又以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為衡量標準。要求行為人在主觀意志的支配下實施了非法侵占公私財物的行為,且該種侵占行為又滿足了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的客觀要求,由此即可認定為敲詐勒索罪的實際構成,即達到了敲詐勒索罪的既遂標準。至于被害人交出財物是由于精神上的恐嚇還是存在其他原因就無須考慮,因而也對敲詐勒索罪的既遂認定沒有任何意義。
但此種觀點也存在著特殊情況,若行為人實施了敲詐勒索的行為,但最終得到的財產卻沒有達到敲詐勒索罪的數額標準,且未達到數額標準的結果是基于行為人意志之外的狀況所造成的,即不能認定為犯罪既遂。在實務案例中:如甲勒索乙10萬元,但后來到手的只有1000元,此種情況是由于乙用假幣欺騙甲導致的,此時即不能認定為犯罪既遂。
三、敲詐勒索罪既遂認定條件探析
基于刑法第274條的規定,敲詐勒索罪滿足多次敲詐或者敲詐數額較大的標準才能構成,若敲詐勒索的財產數額未達到較大程度或者不屬于多次敲詐,則不能認定為犯罪。但在具體犯罪行為的認定中,數額較大以及多次敲詐的數額標準如何認定還需做出聲明,在司法實務的應用中,敲詐勒索公私財產數額較大的標準為:2000元至5000元,兩年內敲詐勒索三次以上即符合多次敲詐的認定。但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現狀,也使得數額認定不能一概而論,也要根據各地區自身發展狀況進行調整,以達到相對的公平。
司法解釋也另有規定:行為人敲詐勒索數額較大,但客觀上存在認罪、悔罪、退贓、退賠等悔過具體行為,具有以下四類情節之一的,即可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情節顯著輕微,對行為人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1)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2)不是主犯的,沒有參與分贓或者分贓較少的;(3)被害人諒解的;(4)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對于敲詐勒索罪,筆者通過犯罪構成要件、犯罪的既遂認定在司法理論界存在的分歧以及罪與非罪的界定進行了系統性闡釋。本文重點也對實務中敲詐勒索罪的既遂標準認定問題進行了剖析,希望可以為司法實踐提供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