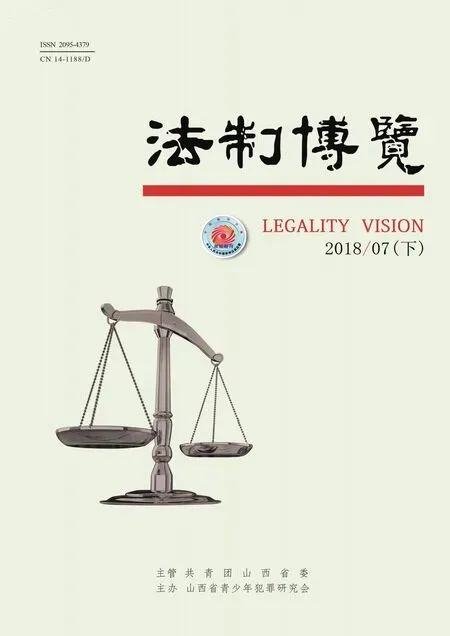網絡直播的監管問題探討
孫翔宇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網絡直播在以其實時性、互動性充分滿足了人們獵奇心理,贏得受眾青睞的同時,由于其受到的監管不到位,而提供服務者在利益面前又缺乏自律,網絡直播秩序曾十分混亂,行業畸形發展。如今,雖然一系列的規范文件出臺,相關部門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收獲了一定的成效。但該行業對社會,對法律的挑戰仍然嚴峻。為了使網絡直播成為主流價值和時代精神的出口,我們應當從監管和立法的層面加以深入思考,規范網絡直播行業的發展,使其良性發展。
一、網絡直播的監管現狀
網絡直播隨著互聯網技術和互聯網文化的興起而出現。它的最初是讓經驗分享像普通大眾敞開大門。[1]而現在,網絡直播速度快、受眾多、影響大,一旦其內容失控,不僅該行業會失去發展前途,更嚴重的是會給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為此,我國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政府部門也陸續出臺了幾份管理規定。包括一些網絡直播企業也紛紛對內整改,還共同制定了《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然而,據筆者調查,有33.63%的人表示沒聽說政府有監管,認為直播的市場秩序混亂。59.29%的人認為規定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但還存在缺漏。這說明,雖然出臺了這些規定,但是網絡直播的各種負面影響仍然存在,甚至情況依舊糟糕。這與監管辦法中監管主體的不確定,監管方式的不明確,監管辦法的不科學密切相關。而對于各直播平臺共同公布的自律公約,因其不具備國家強制力,只能依靠行業內部監督和實施,其效果可想而知。
從寬松到嚴格,從一開始的《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到今天的“凈網2018”專項行動。隨著對網絡直播規范的不斷加強,借助網絡直播實施違法行為的手段越來越隱蔽、多樣。這就對網絡直播的監管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實際上,對網絡直播的監管制度還存在許多缺陷,比如監管主體不明確的問題,法律后果模糊的問題。因此,如果不能在現有的監管體系上加以完善,強化制度設計,網絡直播就難以健康發展,其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也將持續下去。
二、網絡直播監管體制的完善
(一)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網警隊伍建設
依據現有規范,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主體并不具體。概括地說,我國網絡直播監管部門有公安部門、文化部、廣電總局、網信辦等。其中,文化部和廣電總局主要通過審批許可來規范直播平臺的設立,公安部門中則主要依靠網絡警察的巡查執法來實時監控。但各監管部門之間責任不清,監管主體無法確定,監管效率低下。因此,亟需整合政府組織機構,理順管理環節,提高政府管理的工作效率,接受社會的廣泛監督,以適應網絡直播產業發展的需要。[2]
筆者以為,如果把對網絡直播的監管分為三個階段,即事前審查、事中監察、事后處罰。那么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事中的監察,這也是由網絡直播的實時性所決定的,直播者利用已經通過審查的直播平臺實施違法行為,如果不能在其實施時發現,即便該視頻保留半個月,也會無人問津,更談不上處罰了。其他部門往往都是通過被動的投訴舉報才能察覺問題,如此一來,進行實時監察,主動出擊的網絡警察就成了最合適的巡查主體了。但是基于我國國情,各部委交叉負責管理我國網絡警察隊伍,而多部門協作極易出現相互推諉的局面,于是經常發生誰都要管或誰也不管的情況。[3]直播平臺的網絡違法直播行為無人處置的局面也是如此,所以我國網絡警察隊伍的建設需要專業化,需要對網絡警察進行專門培訓。
(二)完善相關立法,明確法律后果
自產生利用互聯網實施犯罪行為后,針對該現象的法律規范就被設立和不斷完善。網絡直播也不例外,然而,除了幾個行政部門出臺的規范文件外,只有《網絡安全法》作為法律約束那些利用網絡直播實施危害社會利益或他人利益以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由于《網絡安全法》規范的行為大部分是以行政處罰措施作為對該行為在法律上的否定評價,難免會有違法成本較低的缺陷。另外,如直播涉及色情內容,由于我國刑法的相關罪名中的一些概念還存在爭議,有時則較難判斷其行為的性質,從而導致法律后果的模糊不清,難以起到真正的威懾作用。因此,一方面,網絡直播法律體系涉及多個主體,如果只依靠個別法規,則會嚴重限制法律的規范作用,故需要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體系。另一方面,網絡直播法律體系涉及多個部門法,單獨制定一部規范網絡直播的法律不太現實,應將對相關需要被規范的行為通過司法解釋等手段分散到各部門法中去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