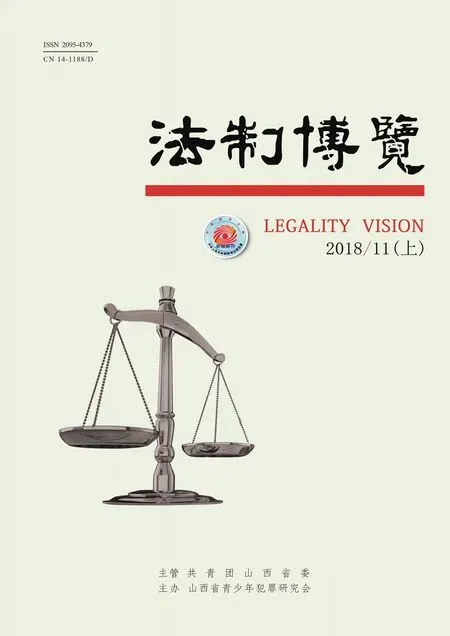淺析全面二孩政策下兒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保障措施
李文淇
武警警官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3
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國出生率提高,雖然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已經在我國實施,但是我國法律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并且在保障兒童權益方面沒有系統的法律加以維護,制定的法律實際操作性差,司法體系、司法程序仍有待完善[1]。因此,為保障兒童最大利益,現對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在我國的法律保障進行研究。
一、兒童權利的特點
兒童權利是屬于人權的,二者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關系。兒童權利具有人權的一般性與自身的特殊性兩個特點[2]。
一般性體現為:一方面,兒童的權利是一種普遍性權利,作為人權的一種形式,它不因種族、貧富、地域等產生差異,而是平等存在于兒童這一群體中的;另一方面,兒童權利適用于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獨立個體,強調這一群體的價值與尊嚴,維護的是這一群體的利益;第三方面,兒童權利具有整體性特點,它體現在教育權、監護權、生命權等各種人權上,如果單獨解讀其中一種人權則不能體現兒童作為人的一種資格,降低了兒童的社會地位。
特殊性表現在:第一,主體年齡有范圍。兒童權利主要適用于年齡在十八周歲以下年齡段的人群,這一時期的人在生理心理上都沒有發育成熟,需要特殊保護,這一時期的保護具有發展性,因為人的不斷成長,保護兒童權益的行動也應該不斷擴大,機制應該更加完備。第二,兒童權利擁有依賴性。兒童權利的保護需要社會、家庭、學校多方面的配合,依賴于國家政策、司法規范等多方面的規定,兒童依賴于家長,老師等多方的幫助。第三,兒童權利遭受到侵犯。兒童作為社會群體中的弱勢者,保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不成熟,能力尚且不足,還有待發展,面對學校、社會、家庭的侵害無法反擊。
二、兒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適用問題
首先是法律概念不明確,法律概念是法律規范的基礎,在法律推理的過程中發揮著首要功能。要研究原則的適用問題,首先應該明確兒童利益最大化在現今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法律概念,這有利于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對這一原則進行具體適用。最大利益原則本身就具有的模糊性,“最大”的范圍無法進行界定,這也恰恰展現了它的不確定性。兒童的最大利益需要根據各國的實務情況進行解決,在司法過程中又可能因為審判者的學識不同,在判定最大利益時肯定會有所差別,所以明確利益的法律概念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是權利之間不平衡,為了維護兒童的權利提出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維護了兒童的利益,但是在平衡兒童與家庭、父母、社會等各項權利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最大的維護兒童利益在有些情況下就會影響其他人或者社會機構權利的行使,甚至會損害他們的合法權利。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是否還應該最大的保護兒童利益,是否需要兒童承擔他們所應承擔的責任,是否要讓成人、國家機構、社會舍棄他們的利益去滿足兒童的需求,這值得我們思考。
三、完善兒童利益最大化法律保障的建議
首先是明確內涵,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本身具有模糊性,但是在新時期全面二孩政策下,需要我們根據國情對這一含義進行明確,這樣不僅對原則的宣傳指導,也有利于有助于該原則的適用。內涵的明確可以更好地進行兒童案件的審理,讓法律更加具體,具有針對性。
其次是完善立法,借鑒外國立法經驗,面對英國、美國、德國在兒童權益保護方面具有體系的規定,我國的立法還有待提高。我國立法原則性太強,不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英國的《兒童法》就對受虐兒童的保護性政策有具體的法律規定,可以實際操作于一些案例中,實用性強。在網絡發展的新時期,網絡這一特殊領域的立法應該學習美國,為了保障兒童在新事物下能夠健康成長,應該在特殊領域進行立法。雖然美國德國在立法上沒有實際說明兒童最大利益原則,但是它們都根據自己的國情對該原則進行了全面的應用,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國也應該根據國情對兒童進行保障性的立法。
再次是健全司法,完善司法程序面對侵犯兒童利益的虐待兒童問題、侵犯兒童隱私權的情況,我國司法體系中并沒有專門的程序進行解決。面對未成年人犯罪,公安局的直接介入是不符合司法程序的,需要在司法執行中加以明確,對于強制措施也應該區別于成人犯罪的條件。面對繁重的案件,我國可以借鑒國外處理兒童案件運用的簡易程序,有效率的進行案件處理,維護兒童心理健康。
四、結語
通過兒童權利內涵的分析,得出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本身具有的模糊性,認為我國應該在當代特色下,與傳統價值觀念相結合,建立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立法、司法、行政體系,需要建立兒童福利專門機構,需要與民間保護組織共同協作保護兒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