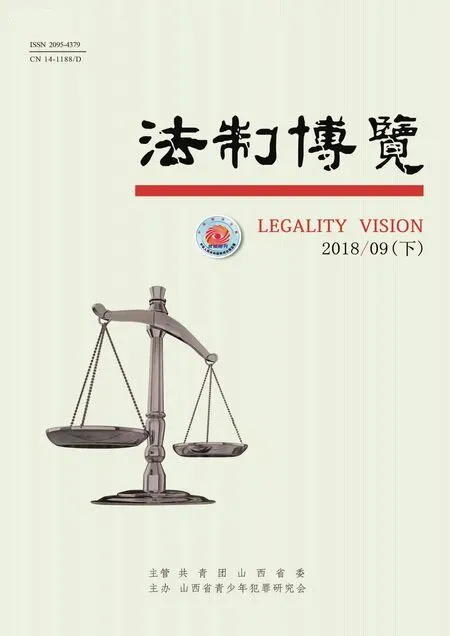民法誠實信用原則再探究
——由“帝王條款”引發的思考
孔盈楓
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一、誠信原則的歷史發展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場交易中的一種道德要求,起初是以商業習慣形式存在。在古代德國,人們以誠實信用為誓詞,起到確保履行義務作用。總體而言,誠信原則的發展歷經了三個階段。
(一)羅馬法時期
隨著羅馬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商品交易關系的復雜化,原有的立法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社會的需要。在此基礎之上,誠信原則作為道德規范植入羅馬法中。而羅馬法中如“誠信契約”及“誠信訴訟”亦為現代誠信原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近代民法時期
文藝復興之后,歐洲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工商業逐漸繁榮起來。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羅馬法以其公平正義又具有普適性的特點,在歐洲大陸被廣泛適用,并產生較大影響。其中以德國為代表,當時的德國并未統一,境內邦國中各自適用符合當地情況的法律,且德國的習慣法并沒有起到統帥作用,因此,誠信原則基本被德國全盤吸收并繼承。
隨著《德國民法典》的頒布,誠信原則作為強行性規范規定下來。然而在該法典中并未承認誠信原則是民法中的一般原則,僅將其的適用范圍從從合同關系的規則擴大至債法的規則。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在當時仍然是作為契約自由原則的補充形式所存在于法律當中。盡管如此,近代民法時期的誠信原則畢竟在立法中得到了形式上的確立,并為其在現代民法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立法基礎。
(三)現代民法時期
二十世紀初期,隨著《瑞士民法典》的問世,標志著現代意義的誠信原則最終得以確認。作為二十世紀的第一部民法典,該法明確授予法官可依誠實信用原則來行駛自由裁量權。自此,誠實信用原則上升為涵蓋整個民法領域的基本原則。
瑞士所采取的此種立法方式極大程度上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需要,該方式亦被各大陸國家陸續效仿確立。在德國,通過法官的司法活動,使原有的誠信條款上升到了基本原則的地位;意大利于1942年頒布的《意大利民法典》中規定了當事人應當依照誠實信用原則進行民事活動;我國大陸于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中亦將誠實信用原則設立為民法中的基本原則。
由此可見,誠信原則從起源到發展乃至最后確立經過了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千于年的積淀使得誠信原則的地位不斷提高,并最終發展成為了民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二、誠信原則作為“帝王條款”地位之分析
誠信原則作為德國民法典中的“超級條款”,幾乎貫穿德國整個法律體系。德國于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中對誠信原則做出了相關規定,擴大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德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亦對法典第242條做了許多司法解釋,并逐步形成具有德國特色的判例體系;此外,德國法學理論學界亦對誠信原則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帝王條款”地位的由來
1.誠信原則的“潛伏期”
十九世紀的歐洲以追求自由為最高理念,將契約自由神圣化,并奉行為自身信條。在此背景之下產生的《德國民法典》縱使將誠實信用原則以立法形式列入法條中,但卻并未將其視為民法的一般原則看待,使得誠信原則仍然作為契約自由原則的補充形式所存在。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十九世紀的德國長期處于概念法學的統治之下,該學說的倡導者認為立法者是萬能的,并且拒絕承認法律存在漏洞。由于制定法為法律的唯一淵源,法官們被迫限制于法條的嚴格適用,幾乎不具備自由裁量權,因此誠實信用原則無法作為判案的依據。
2.誠信原則的“名聲大噪”
二十世紀初期,德國產生了與概念法學對立的自由法運動。該運動倡導者強調審判過程中的直覺因素和感情因素,并要求法官根據正義與衡平去發掘法律。而導致雙方的爭論白熱化的導火索便是1923年德國最高法院依據第242條對匯率進行了成功調整。
1919至1923年間,德國發生了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由此產生的貨幣貶值問題給德國的長期交易契約帶來了大量的問題。在立法者無法提供必要的解決措施的前提下,德國最高法院通過宣布對抵押權將根據其創設時的貨幣價值重新估價等措施,打破了在此之前謹遵的一馬克等于另一馬克的基本原則,并成功挽救了危機局勢。法院從本質上動搖了德國民法領域的既定基礎,該行為亦得到了普遍認可。
3.誠信原則“帝王條款”的確立
1923年的判例迎合了自由運動倡導者所提倡的廣泛自由裁量權的主張,法院的行為亦得到了自由運動倡導者們的支持,自由法運動的先驅將第242條稱為“帝王條款”。自此至今,德國以司法解釋和大量判例擴展或延伸了法律規定,逐步形成了由傳統向現代民商法誠信原則的發展和轉換。
(二)本人對于“帝王條款”的理解與分析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適用讓長期受制于概念學派的自由主義運動倡導者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而本人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其本質和內涵應與該原則所處的社會時代息息相關。只有將其至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才能對其做出理性的判斷。
第一,“帝王條款”之稱反映了誠信原則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性功能。意思自治原則作為十九世紀西方國家民法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奉為不可動搖的準則。但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的意思自治原則已無法適應新環境的需要。1919年至192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導致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新經濟思想的產生,國家機關開始通過法律手段介入私人交易。而誠信原則作為道德義務,開始逐步被立法者所接受和采納,并作為一般原則以形式化,從而對意思自治原則加以適當限制。
第二,“帝王條款”之稱反映了國家通過司法途徑對經濟進行有力干預。司法干預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主要形式,通常是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進行。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陸,多數國家的立法均以司法自治為指導思想,政府活動的范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進入二十世紀后,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由此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逐漸加深。為了避免社會各階級矛盾的惡化,國家開始尋求折中的協調方式。1923年,德國法院通過誠信原則調整匯率,成功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案例說明了該原則作為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方法,巧妙地緩和了資本主義各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國家通過該原則對社會市場進行干預,使得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大大擴展。
第三,“帝王條款”顯示了大陸法系立法及司法模式的本質轉變。十九世紀的大陸法系被概念法學倡導者的觀念所充斥。他們制定包羅萬象的法典以證明法律并不存在盲區,法官遇上任何棘手的問題均可在法典中找到答案,因此法官并不需要自由裁量權。然而時至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新因素的不斷產生,舊法典的內容已無法涵蓋這些新滋生的因素。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中確立了誠信原則,該法典的頒布意味著司法過程中開始出現人性化的因素以彌補法律規則的不足。隨后誠信原則在大陸法系的廣泛確認,使得立法者終于意識到法律的局限性。而法官以誠信原則為依據獲得了自由裁量權,使其將法典中與現實生活相交融,及時將新因素補充進正在運作的法律之中,最終實現法律的與時俱進。
三、結語
作為民法中的基本原則,誠信原則作為“帝王條款”在歷史上所建立的種種功績,更多反映地是其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所包含的道德本質,折射出的是不同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整個大陸法系立法及司法模式轉換的道路和軌跡。因此,對于誠信原則,我們應根據不同的時代背景進行科學定位,不可盲目跟風或全權否定。只有將誠信原則與社會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讓其發揮最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