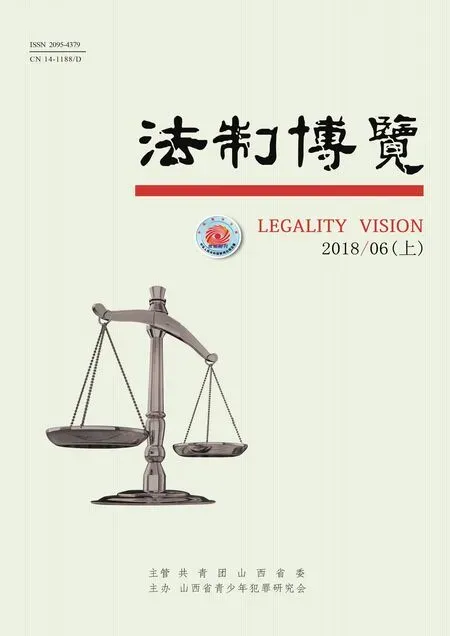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的立法保護
饒思豪 陳 力
中南民族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4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興起源于2009年,國家民委大力推進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工作的展開。各少數民族地區在保護少數民族傳統人文景觀的基礎上,發揮各地優勢文化產業,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旅游,帶動經濟提速。
一、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現狀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是指在某一特定區域,形成的具備民族特色,能夠完整展示民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并集中表達民族文化內容的地域。從概念上來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有文化性、民族性、區域差異性等特點。
特色村寨建設過程中,要著力注重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在保護的基礎上,進行可持續性的開發與建設。保護與發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是實現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是對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的具體實踐。①縱觀當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設如火如荼,但同時也暴露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一)發展動力不足
眾所周知,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是建立在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內容的基礎上的,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斷言:離開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發展就將無依無靠,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同時,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又具有單一性、區域性特征。在特色村寨的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形成“一次性”旅游,很難吸引游客重復性的游覽,從而導致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發展的動力受阻。
(二)發展模式單一
旅游活動是全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綜合展示,給游客以身心最優質的體驗。但我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設似乎偏離了原有發展的軌道。商業化改造嚴重,表現在景區商鋪林立,民族特色文化展示不足,失去原汁原味的民族味道。類似貴州丹寨萬達特色小鎮,湖南湘西鳳凰古鎮等均存在著商業化性質嚴重,破壞了原有的人文特色。
當然,商業化是旅游業帶動經濟的一個重要杠桿,不可完全取締、關閉商鋪。這對于管理者而言,是一個均衡文化展示與商業發展的難題。若是能做到兩者均衡發展,自然是最優質的結果,若如做不到,將是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持續發展的弊病。
(三)利益分成不均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開發模式大多是政府主導,引進開發商,開發管理。所得到的經濟利益,政府與開發商拿走了大部分,當地的居民僅僅只能通過從事一些苦力、表演者獲取少量的勞動力報酬。
少數民族群眾是民族文化資源的擁有者,有權分享民族文化資源開發帶來的各種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現階段特色村寨社區利益失衡的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產權法律制度的模糊、社區整體力量博弈中的弱勢、社區村民整體文化自覺較低、社區村民價值觀的扭曲與變異、社區內部利益缺乏有效的約束。即使是作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委會,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為社區少數民族群眾爭取應得利益。涉及村民利益時候對外界妥協態度,社區居民在維護自身利益中仍然處于弱勢地位②。
(四)破壞性問題嚴重
客觀上而言,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通常存在矛盾,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開發過程中,同樣存在環境問題。民族地區大多位于偏遠山區,生態環境呈現出較為脆弱的狀態,傳統農業的生產中,并不會造成環境的大面積破壞,整個生態系統處于一個穩定可控的狀態下。然而對民族地區經濟性開發的活動中,不可避免的會給當地環境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大量的游客進入景區,或多或少的會引起環境的不適應。
(五)管理經驗不足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是一個新的事物,針對該事物,目前還未形成成熟的管理模式。即使在少數民族旅游業發展較好的地區,對于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管理也處于一個摸索的階段。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管理內容主要體現在運營與規劃,由于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使得特色村寨的管理處于一個較為無序的狀態,具體凸顯在景區物價、游覽文明、配套基礎設施、景區治安等方面。
二、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立法的不足
(一)相關法律缺乏,法律規范不夠完善
我國于2013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以法律的形式將旅游業制度明定下來,但其中直接對少數民族文化產業以及特色村寨旅游資源的規定卻很少述及,致使民族文化資源在開發與保護等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法律規范。
法律的主體與客體混亂,權利、義務與責任的不清,法律監督不到位,交織在一起共同導致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的各種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于法律規范的不完善,相關的法律缺乏。
(二)法條內容籠統,實踐操作性不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六條、第三十八條對于少數民族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有抽象化的提及。《旅游資源保護暫行辦法》作為我國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旅游資源保護辦法有其重要作用,但該法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產業也鮮有提及或者一筆帶過。而事關特色村寨旅游開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也只在第23條單薄地規定,“對自然資源和文物等人文資源進行旅游利用,必須嚴格遵守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符合資源、生態保護和文物安全的要求,尊重和維護當地傳統文化和習俗的需要。”
法條的籠統化,帶來實際操作的弊端:執法、司法過程中,往往因為“無法可依”而讓整個法律活動無所適從。
(三)立法技術不足,法律反應滯后
法律與社會現實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亦步亦趨的。涉及到新興事物的立法規范方面,總會有不同程度的落后。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的立法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建設的過程中發生的諸多問題并沒有有效的法律規范去解決,增加了糾紛處理的難度,甚至影響少數民族文化產業建設的進度。
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立法是民族法制建設的重要部分,如果不能解決立法上的各類問題,就無法為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發展保駕護航,更無法卓有成效的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三、文化產業立法與特色村寨建設的互動
(一)樹立少數民族文化產業法律理念
問題的凸顯是為了提高相應的意識,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在法律的管控范圍里,做適當的努力。法律理論來源于基本直覺:法律應當有指引其主體行為的能力。③故追求法治完善,必須對于民眾法律思想理念的引導,使其愿意將自己的行為置身于法律規范的范圍內。
在全面繁榮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指導思想下,大力培養少數民族的文化法律意識,對于堅持和實行少數民族文化法治局域重要意義。當然,文化法治理念并不是自發形成的,只要經過有意識的教育、培養,少數民族的文化法治意識才能由法律心理階段上升到法律思想體系階段。
(二)細化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立法保護的內容
1.明確立法原則
一般立法原則主要包括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嚴格意義上的立法,立法主體既要注重立法的外在合法性,又要注重立法的內在合理性。④而要做到堅持立法的合理性原則,立法者就必須在立法過程中從倫理角度準確把握立法原則的道德意蘊,充分顧及社會的價值理念,以全面彰顯社會的正義、平等、自由及其共同利益。
細化到細化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立法保護的內容上,不僅需要兼顧一般性的立法原則,還有具備有關于特色村寨立法保護的特殊性。
(1)精確性原則。由于國內對于少數民族的文化產業并未形成具象化的立法,所以在制定該類法律亦或者是規章、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上,更加需要貫徹精確化原則,唯有精準化的立法,方能克服法律實踐與操作時“無所適從”的尷尬。同時,精確性的原則也是對立法者立法技術的考驗,促使立法者在實證研究和理論論證的基礎上,制定出符合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立法。
(2)特殊性原則。具體問題的解決,依賴實證意義上的琢磨與調研,尤其是在少數民族相關問題上,更需要充分的調研,這是因為少數民族問題的特殊性導致的。我們在解決民族問題時,且不可用“一刀切”的標準,給予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以普通村寨的立法保護。所以在制定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立法時,不僅要照顧到少數民族不同的生活習慣、人文特色,還要在民族繁榮上相對性的支持。
2.區分法律主體與客體
(1)法律主體。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設中,其法律主體是指參與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開發、發展活動,依法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一般情況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主體可以是企業、社會組織、自然人個人和政府。除了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資源的需求者之外,還包括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供應方,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供應一方主要包括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項目的投資者,及其他擁有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筑所有權者,同時還包括促成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事業發展的經紀人和有關組織。參與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市場主體還包括提供輔助性服務的第三人,他們為交易的順利進行提供資金、經紀、咨詢等相關服務。
(2)法律客體。法學理論上的法律行為的客體是指法律關系中主體的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即所謂的對象。作為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對象的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之所以可以順利進入旅游市場進行開發和保護,其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人們在對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有巨大的需求缺乏的同時,人們還有不同的評價和社會期望。因此,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資源所提供的服務功能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社會的公共物品,明確而清晰的法律客體對于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市場的形成以及構建我國的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法律制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3.規范權利義務
區分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主體與客體,是為了附著相應的權利與義務。具體來說,當地居民有獲得經濟成果的權利,同時也需要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過程中積極提升自己的保護性法律意識,以可持續的理念規范自我行為。開發商需要因地制宜,不宜強化噱頭而忽視民族文化景觀的特色與內涵,保護性開發與生態化開發同步。政府應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保駕護航,完善基礎設施,為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發展排憂解難。
4.引入法律監督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過程中的法律監督具體體現在旅游產業的開發、建設管理中,嚴厲打擊整個旅游項目過程中的違法的行為。
(三)精細法條,提高法律可操作性、實踐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相關立法一旦制定就不該束之高閣,而是需要運用到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實踐中去,當然,若是能夠順利實施、實踐,也是對于法律自身優劣的證明。正因為如此,需要立法者在制定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立法時,切不可籠統概括,而需要從實踐與可操作性的要求中著手,制定以及完善法律。
[ 注 釋 ]
①李忠斌,鄭甘甜.論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中的文化保護與發展[J].廣西社會科學,2014(11).
②李忠斌,李軍,文曉國.特色村寨建設中民族文化資源開發參與主體權責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6(1).
③[英]約瑟夫·拉茲.法律的權威[M].朱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8.
④肖毅.論立法原則中的倫理意蘊[J].求索,2005(08):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