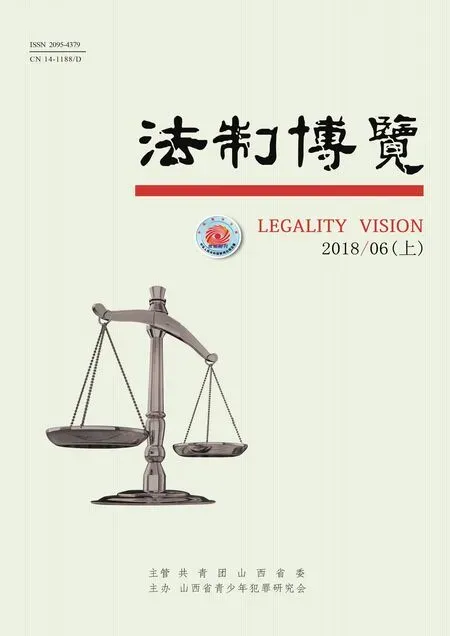關于人工智能畫作在著作權法上的界定
來鑫洋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一、人工智能畫作的基本狀況
人工智能的說法最早源于1956年由約翰·卡麥錫教授組織的達特茅斯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利用計算機在數學、邏輯學、心理學等方面模擬人類智能行為。在第二年的會議活動中正式提出“人工智能”這一說法,神經網絡鼻祖皮茨并對人工智能進行了總結:“(一派人)企圖模擬神經系統,而紐厄爾企圖模擬心智……但殊途同歸。”①人工智能從表面意思來看,它是指通過加工制造類人思維和行為方法,以實現在機器上的智能。后來西方學界將人工智能定義為計算機科學的一部分,是與設計之力有關的計算機系統,那是個奇特的系統,是人類在諸如理解語言、學習、推理、解決問題等方面可以用以交往的智力系統。②可見,人工智能是人類通過對計算機后臺程序的運行,使其具有類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產生一系列的實踐成果。人工智能繪畫正是基于上述人工智能計算機技術發展而來的。智能繪畫最初出現在美國貝爾電話實驗室,其創作成功了《波形》等人工智能畫作,引起了一時的轟動。繼貝爾電話實驗室之后,又出現了本杰明·格羅瑟的交互式機器人、哈羅德·科恩的ARROM、西蒙·克爾頓的“繪畫傻瓜”、谷歌的“開始主義”和Deep Dream等一系列繪畫程序,這些繪畫程序分別有著各自獨特的工作原理。
筆者主要將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物理式創作,它的工作原理是設計者為繪畫提供所需的圖像資料和數據,人工智能對圖像的內容進行識別和分類,并將其與客觀環境所產生的外部信號一同進行提取、整理,并對某些特定的圖像和信號數據進行復制、循環,最終達到內容重構的目的,使一幅新的畫作得以產生。另一類是抽象式創作,由設計者為計算機程序設立一種類人的神經網絡系統,模擬人腦中的神經元即計算機中的分類器對輸入的內容進行分類,一層一層之間互相連接,使每一個神經元都將一些神經元作為輸入,同時在滿足了所需的條件時作為其他神經元的輸出。這種系統可以讓計算機學會類人的思考模式和規則,具有和人相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計算機利用這種想象力來構建自身創作的觀點,在具備類人思考模式的基礎上打破原有的規則對圖像信息進行加工,最終實現創新。
二、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
(一)人工智能畫作的主體
根據對人工智能畫作的分類,畫作的產生有兩種基本途徑。兩者的相同之處在于,創作都是由計算機程序設計者為機器編制一定的程序來實現的。不同之處在于是否具有類人的思維模式。第一種模式的創作主體是計算機程序設計者毋庸置疑,設計者通過設計一種固定的算法,使自己的思想和意圖通過這種程序表現出來。第二種模式是計算機通過自主想象、構思進行創作的,它可以進行獨立的思考,由此產生的畫作是程序思考和想象的產物,而非設計者的直接創造力的體現。人工智能畫作所涉及的著作權屬于知識產權的主要權利之一,而知識產權這一名稱最初為“intellectual property”,我國于1986年的《民法通則》以前,曾稱其為“智力成果權”,后將其確定為“知識產權”。而關于機器能否成為著作權主體,主要分為三大派別,一派認為著作權的設立的包括保護創造力本身,而不僅是保護由人類產生的創造力;一派認為只有具有生命的人類通過思維運作創造出來的作品才可以得到保護,計算機程序設計者才應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主體,如1984年美國《版權實施第二次綱要》指出,作品要獲得版權保護,就必須能追溯至自然人。③;還有一派認為人工智能畫作不應受法律保護。由知識產權的界定范圍來看,筆者認為,知識產權的主體即著作權的主體更加強調是有思想、能思考的人類,其作品具有更多的意識屬性。著作權之所以受到法律的保護,正是出于對人類思想和智慧的智力成果保護這一角度出發。相反,創造力是一種能力,是人或物所具備的特定屬性,不應將其作為法律所要保護的權利。盡管機器存在一定程度的創造力,但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主體應僅限于自然人。
(二)人工智能畫作與智力成果的關系
著作權法制定的目的在于激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這為著作權的客體提出了前提條件,即客體需要是一種智力成果,要具備一定的文學、藝術或者科學價值。如果一種作品沒有價值,沒有人的權益因此遭受損害,法律也就沒有必要對這種作品通過立法加以保護。通常認為,智力成果是指人類通過智力創造的精神財富或精神產品,這說明智力成果具備人類創造性和成果共識性的特征。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計算機程序設計者能夠在計算機程序中設置“人工神經細胞”來模擬人體的神經元,從而使機器具備人腦的思維模式,這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但是不能否認其具備和人類相同的創造性;另一方面,即使是通過物理式創作方式創作出的畫作,雖然畫作并非由人類的思維模式的直接創造產生,但也是人類運用智力創造的程序創作出的畫作,這是人類創造性的間接體現。據新聞報道,在一次藝術拍賣會上Google展示了幾幅人工智能創作的畫作,其中一幅拍賣價格高達8000美元,人們對人工智能畫作的熱愛和追求,恰好體現了作品成果的共識性。綜上,筆者認為人工智能畫作雖然不是人類直接作用下的產物,但通過它的創作模式可以發現人工智能畫作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直接或間接性成果,程序設計者通過一種婉轉的方式實現了創作活動。
(三)人工智能畫作與獨創性的關系
獨創性這一概念最初源于英文Originality,它強調一種從無到有的、獨特的作品的誕生。一般來說,畫作的產生是從動態的創作活動開始,到靜態的作品產生結束。可見,只有創作者獨立完成創作和畫作本身的特色性兼備,才能算作品真正具有獨創性。獨立完成創作要求創作者首先要產生繪畫意圖,進而對畫作構思,最終通過體力和腦力勞動將構思的內容表現于畫作當中。在這個過程中,意圖是主要因素,而構思和勞動只是輔助性因素,若無意圖的構建,則畫作不會產生。而人工智能畫作的繪畫意圖僅僅來自設計者,將其以指令的方式輸入到計算機當中,以可視的數據方式來呈現出來。有學者認為,獨創性要求作者在創作活動過程中付出大量的機能、判斷、創造性勞動等,并且這種技能和勞動須是能夠直接產生作品表達的勞動和機能,從而應該排除基礎性的間接性勞動。筆者認為,盡管計算機能夠獨立執行構思和勞動,但意圖、畫思到勞動都是基于設計者而產生的,設計者雖然沒有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去實現獨立創作,但卻以計算機執行數據的方式來代替其意志的實現。
另外,創作的作品還需具備一定程度的特色性,這要求人工智能畫作的作品與其他作品之間存在差異,不能是抄襲、模仿他人的畫作。這種差異的要求并不意味著所有畫作都要達到絕無僅有的地位,只要該畫作在表現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具有別人所不具備的新的特點,就應該稱其具有特色性。在人工智能畫作中,物理式的創作是基于對其他圖片、畫作數據的分析和整理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提取和整合使新畫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另一種抽象式創作是基于類人的神經網絡系統進行的,抄襲和模仿往往是基于人的主觀能動性,希望通過抄襲和模仿獲得一定的利益,從而將這種意志付諸實踐,而人工智能這種神經網絡系統不具有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決定了人工智能不具有抄襲和模仿的意圖。人工智能通過自主地想象、構思進行作畫,由于不具有這種抄襲和模仿的意圖,即使出現了與其作品相似的作品,也只能認定人工智能產生了與他人的想象、構思相同的情況發生。由于人類的思維的有限性,通常只能通過人的思想和情感和解讀一幅畫,但人工智能畫作往往不帶有任何感情色彩,當一種畫作不包含感情色彩時,人們往往很難解讀它的內在含義,基于此,往往可能得出人工智能畫作不存在特點的答案。然而,正是由于這種情感的缺失,更容易使人發現人工智能畫作所存在的物理上的特點,不能片面地說人工智能畫作不存在獨創性。因此,綜合以上兩種情況來看,人工智能畫作符合獨立創作與畫作特色性的要求。
三、結語
通過對人工智能的產生歷史與發展進行研究,進而對人工智能畫作的產生總結為兩種情況:物理式創作和抽象式創作,這兩種創作原理代表了兩類創作的形式。而任何一種創作作品若想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都應該滿足著作權法對于主體資格、智力成果的表達、獨創性這三點要求。結合人工智能畫作的兩種創作原理,能夠判斷出人工智能程序設計者符合著作權主體所規定的自然人的要求;另外,這兩種創作無論是繪畫意圖、構思,還是通過勞動進行展現,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說明了畫作是設計者智力成果,同時人工智能的創作原理又決定了它本身具有獨創性特點,由此,人工智能畫作符合著作權法對其的要求,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 注 釋 ]
①<中國計算機學會通訊>[J].2016年第三期<專欄>.
②SEHR.Volume.ssue2:Constructions of the Mind Updated.4 June 1995.
③U.S.Copyright Off.,Copy Office Practices Compendium Ⅱ§202.02(b)(1984).
[1]鄭國輝,朱楠,曹陽,姚洪軍,胡水晶.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
[2]朱謝群.創新性智力成果與知識產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周飛.基于智能計算的數字繪畫[J].美術教育研究,2017(7).
[4]楊守森.人工智能與文藝創作[J].河南社會科學,2011(1).
[5]曹源.人工智能創作物獲得版權保護的合理性[D].北京大學,2016.
[6]陳維.論著作權法上的獨創性[D].西南政法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