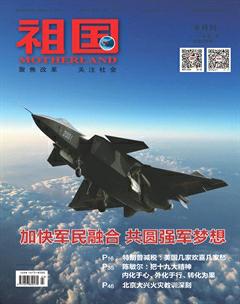孔子生涯發展教育中的“名譽”觀念及其意義
摘要:在孔子的生涯發展教育中,將51歲至60歲設定為事業化階段。“50而知天命”,就是知道了生命的使命,堅守信念,用實際行動來實現和履行諾言,是為踐行。孔子的非凡之處,在于對“大信”和“小信”的區分,奠定了中國文化的使命感觀念:使命感是通過踐行諾言,獲得社會名譽,實現生命不朽,并希望得到歷史尊重的情感體驗。與職業追求職位不同,事業是對生命的承諾,是擔當自己生命的使命,是最深層的生命力力量。“青史留名”,作為孔子開創的人生美學的核心概念,通過一代代人的身體力行,積淀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人生觀念。
關鍵詞:孔子 名譽 使命感 意義
孔子非常重視名,活著要“正名”——“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事不成”;死了,也要“留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著《春秋》,開創的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對歷史上的人進行褒貶評判,體現了孔子的生命信仰,要求人活在現實中,還要追求活在歷史中,青史留名是孔子開創的中國人的人生美學觀念。
一、什么是孔子生涯發展教育中的“名譽”
(一)轉向“事業”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涂。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人生到50歲時,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在職位上將職業轉化為事業;二是另起爐灶,從職業上轉到事業上去。如孔子本人,孔子在50歲時,放棄教育職業,開始了政治事業。在中國歷史中,很多人正是因為從政治職業轉向文化事業,才取得巨大的成就,實現青史留名。
事業在孔子人生美學中是一個很高層次的概念,是國事與私事的統一體,是社會認可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事業”的前提是源于內心的“知”,一個人知道了自己的生命追求,知道了生命的使命。到了50歲,才能夠知道自己的生命追求,才能夠知道自己的理想,才能夠知道自己的事業。在今天看來,這種觀點是符合認識論原理的。
認識的任務是要使主體的思想符合于客體的實際。蘇格拉底認為,“認識你自己”是非常困難的,這與孔子的“50而知天命”有異曲同工之妙。人的理想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是隨著主體認識主體自身和客體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和加深,從而形成對自己的理想的認識和把握。理想必須通過計劃、方案等形式應用于實踐,向現實轉化。所以,理想只能在人生實踐中形成。著述,歌吟,繪事,琴書,玄理,古玩,術數,醫林……所有這些都可以成為“事業”,關鍵在于它們是不是你心靈的呼喚。
事業,是個體生命的潛能在社會中得以發揮,實現個人理想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既產生使命感,又離不開使命感。使命感有著生命的原動力的驅動,是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
使命感是心靈的自由狀態,每個人都希望成為自己所希望的那種人;使命感是人事與生命力效應的高度順應契合時的感覺,是完成自己對生命承諾的一種美感。
(二)“君子貞而不諒”
《易經》曰:“貞固足以干事”。貞者,誠信也。只有堅定誠信,才能夠“足以干事”。
五十而知天命,就是知道了生命的使命。“知道了”就是一種承諾,承諾就必須踐行,這就是誠信。但是,誠信有大有小。孔子區分了“大信”和“小信”,事業指的是大信,是與國家、社會發展相聯系的仁義、正道的誠信,乃是大信;離開仁義、正道這個根本前提,不問是非地死守信用,就是小信。怎樣才是“正直而不拘于小信”呢?孔子通過對管仲的評價來說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孔子認為,管仲體現了“君子貞而不諒”,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拘泥于小信。孟子后來發揮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做大事的人不為小信拘泥。孔子談的理想、事業,誠信,是指“大信”,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崇高理想”、“鴻鵠之志”、“遠大抱負”,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家長里短社會瑣事。日常瑣事是“諒”,常常要求“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孔子用“管仲之貞”,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追求事業的沉著形象。
(三)“三不朽”
名譽是指社會對人的評價。孔子所說的“名譽”,是指因為對社會作出不朽成績而青史留名:“身體”消失后,“名名譽”留存在歷史中。從進入歷史來看,最高名譽是“三不朽”。左丘明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從《左傳》與《春秋》的關系來看,“三不朽”也代表了孔子“留名”的要義。后來,到了唐朝,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做了界定:
“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
“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
立德,不是官居高位,更不是虛無縹緲的許愿,而是實實在在的政績: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不是名列財富榜的位置,而是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剽竊抄襲,雜糅成著,而是哪怕是一管之見、一得之識,只要“言得其要,理足可傳”。
“三不朽”是對孔子名譽觀念的具體化。要想獲得好的歷史名譽,就要對自已的行為負責,勤勤懇懇為國家為社會立德立功立言。
二、人如何達到生涯發展中的“名譽”
(一)扯帆“順應”
此一階段生命力效應從主動性進入了順應性。根據皮亞杰的觀點,順應是主體的圖式不能同化客體,必須建立新圖式或調整原有圖式,引起圖式的質的變化,使主體適應環境,舉例來說,“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都是順向遷移的例子。扯帆“順應”,就是順風扯帆,將原有的人生經驗應用于新的情境,形成一種能包容新舊經驗的更高一級的經驗結構。所以,事業可能是另起爐灶,但不是從頭再來,體現為一種順向遷移、順應趨勢辦事。endprint
(二)致真善美
踐行事業是對真善美的追求。致真,就是做到嚴精實。所謂嚴,就是嚴格標準,做任何事都有標準,決不敷衍了事;所謂精,就是精準作為,決不東一榔頭、西一杠子;所謂實,就是實事求是,決不好大喜功。致善,就是把事情做到最完善。所謂精益求精,就是已經很好了,還要求更好。《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熹集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致美,就是做起事情來,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心曠神怡,境界不斷升華。
(三)貴在踐行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
“踐跡”,本義是踩著別人的腳印走。由于事業是事與生命力效應的契合是一種順應性人事。所以,“踐跡”的內涵是轉換成為“順應性”。只有“踐跡”,才能“入室”,做到最好。
踐行,就是踐行諾言,意思是用實際行動來實現和完成諾言。承諾是對要約的同意,必須是無條件的,不得限制、擴張或者變更要約的內容,否則,不構成承諾。承諾必須清楚明確,不能含糊,是真知不是假知。
“踐行”與“施行”二者的區別在于:施行,指執行,使規章法令等發生效力;踐行,履行、擔當、完成事先約定的事情。
(四)名譽=踐行+事業+順應
“因為我,不在乎,別人怎么說,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對自己的承諾。”承諾不需要通知,只需要用心去做,用心去做,才能卓越。
三、孔子生涯發展教育“名譽”觀念的意義
(一)歷史意義
事業是孔子開創的中國人的自我實現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漢代班彪在《北征賦》說:“夫子固窮,游藝文兮。樂以忘憂,惟圣賢兮”。班固在《答賓戲》中總結說: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包括班固本人著書立說,都是從政治職業轉移到文化事業的結果。到了現代,梁啟超在50多歲時,從政治職業轉移到教育事業,成為文化教育名流。
(二)文化意義
“青史留名”是孔子對個體存在的最高價值的設定。
孔子用《春秋》一書開創了中國史學的文化傳統,用歷史學成功地解決了人身體消失后人的“留存”的問題。后來,司馬遷說,“立名者,行之極也。”把“青史留名”當作人生的最高目標。“青史留名”帶來了中國史學的發達。“事業有成”是中國人的祝福語。成,指留存在青史中的名譽。“青史留名”鑄造著中國人的人格心理,積淀成為中華民族的人生信念。
(三)現實意義
中國官場一直存在有職位不干事的“老混混現象”。《漢書·朱云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尸位素餐就是指不做事,白吃飯。職位來之不易,要保住,情有可原,但是用“混”的方法,不作為,就成了“老混混”。“老混混現象”有三個危害:一是危害自己,大好年華在混混中過去了;二是危害國家建設,耽誤了國事甚至天下事;三是危害社會,本來生機勃勃的社會生活,被老混混們弄得暮氣沉沉。
“老混混現象”的源遠流長,主要源于對人生“理想教育”的錯位,人們由職位產生的成就感強化,由事業產生的使命感弱化。一直以來,中國非常重視理想教育。但是,由于沒有正確理解理想的內涵和本質,把“理想教育”弄成對青少年學生進行的“憧憬教育”。其實,按照孔子的人生美學,“理想教育”應該是對50歲以上的成功人士進行的使命感教育,目標是要從心理上喚醒老同志的人生使命感。
(作者簡介:陳昌茂,青島濱海學院酒店管理學院,副教授,貴州大學旅游美學,碩士生導師,中國青少年美育協會,副主席,研究方向:旅游美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