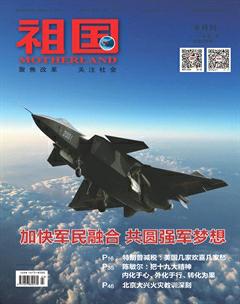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的特點研究
摘要:科爾沁作為蒙古族重要的聚居地,歷史悠久,具有豐富的民俗文化。聲樂、舞蹈、樂器等都是科爾沁民族文化中的瑰寶,也是極具代表性的蒙古民俗文化,具有典型蒙古民俗文化特點。因此,本文主要對科爾沁蒙古民俗文化特點進行分析,包括復合性、多元性、開放性、英雄憂患性等,希望能夠幫助當地人民更好的開展民俗文化建設。
關鍵詞:科爾沁 蒙古族民俗 民俗文化
中國歷史悠久,那種民俗文化是不可取代的瑰寶。不同的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也會產生不一樣的民俗文化。而時代條件、社會條件、物質條件等都是構成地理環境的主要因素。中國有句古話說的好“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各個地區的民俗文化具有不同的特點。科爾沁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其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蒙古族風格,以下是對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特點的具體分析。
一、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具有復合性
蒙古族大多屬于游牧民族,尤其是科爾沁地區,大多數人都是以游牧為主,狩獵為輔。隨著時代的發展,科爾沁的民俗文化也由傳統的草原文化轉向農耕與畜牧結合的復合型文化。該文化類型的轉變,主要由當地的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決定,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隨著文化類型的會轉變,科爾沁草原經濟也得到快速發展,各種商品和農牧產品漸漸出現在市場當中。同時,國家經濟的發達,交通也跟著發展起來,民族之間交流更加頻繁。這樣的變化給科爾沁帶來巨大轉變,目前,除了漢族商人之外,很多蒙古族人民也開始轉向交通運輸、商鋪經營等方向,原本的游牧民族漸漸開始適應定居生活。自此,科爾沁民族文化也漸漸轉變為狩獵、游牧、經商、手工等多種元素于一體的復合型文化。因此,目前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復合性。
二、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具有多元性
在科爾沁地區,生活著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兩者之間相互融合,相互影響,民俗文化不斷交流發展,形成一種多元化的民俗文化。這種文化的交流合作主要在和平的形式中進行,而形成文化交流是由各種歷史事件的影響促進的。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成吉思汗對明安、老斯沁、科爾沁諸部的分封;達延罕時期由哈薩爾后裔居民肚子形成萬戶,促進科爾沁的第二次科爾沁組成;明朝初期,扎菲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等帶領科爾沁部落的遷徙是科爾沁部落的第三次組成;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蘇魯克、蒙古真、喀喇沁、昭烏達、卓索圖等帶領蒙古族人民大量往科爾沁遷徙組成科爾沁第四次部落形成。并且,由于大量蒙古族人民的遷徙,科爾沁民俗文化也從之前的傳統草原文化慢慢轉變為游牧與農耕結合的文化。19世紀初,清朝道光十九年,出臺《禁止私招異旗蒙戶》的規定,但是,這個規定依然沒能組織各旗蒙古族人民之間的來往,文化融合現象也越發明顯,隨著時代的發展,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已經具備了多元性。
三、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具有開放性
經過幾次科爾沁部落大遷徙后,科爾沁民俗文化已經與其他文化漸漸融合,具備一定的張力,自我調節能力和生命力也更加旺盛。異文化的影響造成了文化的變遷,在時代發展過程中,科爾沁蒙古族民族文化與漢族、藏族、滿族等多個異族文化均有過交流,并且不斷發展和衍變。因此,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具備一定的開放性。科爾沁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等自古以來都是蒙古族人民聚集地,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區。在老哈河流域與科爾沁西拉沐淪河地區曾多次發現滿族、蒙古族、女真族、契丹、鮮卑、東胡、匈奴等十多個民族居住的歷史遺跡。科爾沁人民移居到此時,深受各族文化的影響,其民俗文化也逐漸具備開放性,對各種文化的容納性比較高,適應性也比較好。
四、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具有英雄憂患性
科爾沁蒙古族屬于游牧民族,自古以來,為了生存,憂患意識比較強,尤其在近現代社會,由于歷史環境的影響,該民族憂患意識更上一層,這種憂患意識深入到科爾沁蒙古民俗文化當中,是當地居民的一種深層心理特征。同時,科爾沁一向有英雄部落的稱號,當地居民大多英勇善戰。科爾沁的始祖哈布圖哈薩爾曾經帶領一千戶科爾沁衛軍,在蒙古征戰中美名遠揚。北元時期,大延罕重新統一蒙古的戰役當中,哈薩爾的后裔是該戰中的先鋒,長期與衛拉特部以及明廷作戰,曾被譽為“在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的親王。近現代時期,科爾沁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爭當中,發揮出巨大的作用,并且由賓圖王旗帶領蒙古人民組成武裝隊伍,開展武裝起義,公然反抗當時的軍閥和王公。在戰爭中,科爾沁人民不懼強權,英勇斗爭,在史冊上留下重重的一筆。因此,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當中,英雄憂患性與生俱來,是刻在每一個科爾沁人民骨子里的文化意識。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文化的發展,文化發展是民族發展的軟實力。因此,在科爾沁蒙古族的發展當中,同樣不能忽略民俗發展的重要性。民俗文化的形成,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人文遷徙等多個因素息息相關,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歷史烙印,也是多年來歷史文化發展的沉淀,通過探究分析科爾沁蒙古族民俗文化特點,包括復合性、多元性、開放性、英雄憂患性等,能夠讓當地人民更好地認識民俗文化,并且加以傳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軍.內蒙古西部蒙古族民俗文化視覺審美形態探微[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3,(05).
[2]陶繼波,崔思朋,夏琳等.斯文·赫定日記里的內蒙古民俗文化——兼論開展民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與途徑[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4,(07).
[3]五一.論民俗文化的開發與保護——以內蒙古阿拉善游牧民族為例[J].中國民族博覽,2015,(18).
(作者單位:科右前旗第一中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