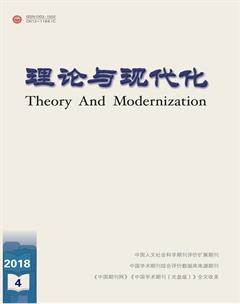通往程序之治
摘要:自主的程序理性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征,程序是現代社會具有基礎性作用的正式調節機制,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與程序化程度正相關。中國古代重視程式步驟,現代程序觀念形成演變則跌宕起伏,程序化建設與現代化進程大致同步:20世紀頭20余年第一次現代化高潮中誕生程序觀念,但混同于程式和手續,受制于權力和道德;20世紀后20余年并延續至今的第二次現代化高潮中再次生發程序觀念,在科學技術程序、經濟管理程序的推進下,政治法律程序注重從中國的實然狀態出發,尊重科學理性,保障公民權利的正當程序獲得較廣泛認同,有效提升了國家社會治理能力。接下來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程序化建設,要在程序表達中更好協調權利、權力和道德三者之間的系統關系。
關鍵詞:程序化;程序觀念;現代化;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8)04-0046-07
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范疇,中國的程序觀念在百余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無到有,日益具有現代性,但若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應具有的程序觀來要求,則還力所不逮。本文在簡述程序化與現代化呈正相關關系的基礎上,簡析中國程序化建設與程序觀念現狀,概覽其跌宕起伏的演變過程,冀望裨益于中國的程序化與現代化進程。
一、程序化與現代化正相關
人類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一直都與基于程序理性的程序行為、程序方法、程序觀念息息相關。經過長期的進化,某些動物的行為具有了一定的步驟性,即能夠有次序地重復某些行為,這是自發的、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人的某些特定行為,比如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利用工具的勞動,不僅具有次序性和重復性,而且有意識地、理性地將這種步驟和機制固化下來,并根據不同環境選擇不同的行為機制、程序方法去改造世界。早期人類之所以形成原始社會,不僅是因為人能夠像螞蟻、蜜蜂[1]、狼群一樣相互協作,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更是因為人能夠借助語言有意識地、理性地將社會性的實然協作機制固化下來,形成具有一定約束力和指導性的社會規范(如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禮樂制度主要體現為程序行為)。我們將人和人類社會起源就具有且必須具有的這種理性稱為程序理性,它是人以其自主意志對有次序的可重復行為的有意識提煉和升華,體現在人的勞動和語言中,與之相伴而生、互補互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類(社會)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的重要標志之一,是人類自主的程序理性及其所決定的具體的程序行為、具體的程序性勞動。這是人的第一次飛躍。
人的第二次飛躍是進入軸心文明。所謂軸心文明,現代化理論重要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認為是“超越秩序”對“世俗秩序”的積極構建,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知識精英,他們意識到必須按照某種“超越的”(用史華慈和張灝等人的話來講是“退而瞻遠”,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跳出來看自己、看人、看人類社會”)觀念積極建構世界[2]。這種超越觀念的制度化,導致對社會內部的關系結構進行廣泛地重新安排(如孔孟用仁義等儒家道德觀念對周禮的重新賦義及其內部關系的重新排序)。正是這種超越理性所重新安排的結構和程序,形成了中國、印度、希伯來、希臘四種文明型態,人類進入軸心時代。人類文明初步成型、成熟的關鍵,是人用更具自主性的超越理性構建了新的制度程序,人的意志更積極地參與到了程序的構建當中。
應當指出的是,由于皇帝君主和宗教權力對人的自主性的壓制,軸心文明興起之初人的程序理性并未得到充分發揮。無論是中國的禮法一體化宗法禮治制度體系,還是西方的羅馬法、教會法,都在實現皇權統治和維護社會秩序時過分強調了權力意志的強制性,而被統治者的自主性空間非常小,所以只能稱之為程式強制,而不能稱之為程序治理。到了近現代社會,人的個性與自由得到尊重和彰顯,而人以其自主性、反思性進一步解放自我,通過科學的受控實驗程序改造自然,通過自然法的法律程序改造社會,人類進入現代文明。這是人的第三次飛躍。據《大英百科全書》載,英文的程序(procedure)一詞大約產生于1611年[3]。這正是現代性如朝日般破曉而出、冉冉升起的年代。在現代性三大要素中,科學理性的具體體現,是科學實驗程序;公民權利的實現,也要靠具體的程序,比如經濟權利的實現要程序性地履行合同契約;政治權利的實現要程序性地制定和執行憲法和法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程序理性的種子在現代性中才真正破土而出,現代性與程序可謂兩者交相輝映、交互融合。
如果把17世紀的現代性和程序理性比喻為花蕾,那么接下來的現代化和程序化就是花朵綻放的過程。18世紀以來,以現代科學和法治為載體,程序精神隨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程序化對于推進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隨著科學技術程序、法制程序的深化和普及,工業發達國家形成了制度化管理并啟發泰羅于19世紀末提出了科學管理程序即“泰羅制”。1889年,作為形容詞的procedural一詞產生,標志著現代程序觀念已經確立,并已對社會產生廣泛影響。我們把程序觀念的普及過程,把社會程序性程度提高的過程,稱為程序化。研究表明[4],泰羅科學管理的實質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對實然機制的程序化、具體化、系統化,它對現代社會影響深遠,極大地推進了經濟政治管理能力的提升。從20世紀初福特的流水化生產線到ERP(流程再造),乃至21世紀德魯克的知識管理,都堅持程序化科學管理的精髓[5];從韋伯的理性化科層制政府到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到今天以新制度主義為重要方法論基礎的治理變革,作為正式機制的程序日益受到重視。由上,我們可以說,現代文明展開的過程,即現代化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理性在科學、經濟和政治等各領域展開的過程,即科學程序化、管理程序化、治理程序化的過程。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程序化程度,體現了它的現代化程度,程序化與現代化正相關。
應當承認,程序化在伴隨著現代化開疆辟土的過程中,也曾被偏頗地理解為形式理性乃至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并借助科學主義形成了對現代社會的形式強制,從而在管理實踐上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并受到各種批評。教訓和批評一定程度上矯正了程序化的航向。二戰后現代社會的自我改善,不僅汲取了第一次現代化的程序化管理經驗(比如,在1952年形成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這一新詞組,幫助實現戰后經濟騰飛),而且通過計算機技術的提高和普及,使程序成為現代科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礎平臺。20世紀下半葉,形容詞procedural又多了名詞的屬性。西蒙有限理性下的滿意決策(主要是程序性決策)觀念浸人經濟管理和公共管理理論;布里奇曼操作觀被重新定義為收斂的操作主義[6];羅爾斯條件契約論的程序化條款提供了新的思路[7]。在又一個千年之交,哈貝馬斯提出了程序性協商的理性重建方案[8]。亞洲學者、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最新潮流,如我國學者季衛東提出了程序和契約收斂于動態平衡的新程序主義。把這些不同領域中的思潮綜合起來考慮,或許表明了程序理性的一種雄心,即要想把人類從無思想和道德虛無感中解救出來,要想重振理性雄風,還是要回到現代性的原點,乃至人類文明的原點去重建程序理性。而這雄心的哲學基礎,就在于程序理性拒絕預設真理或終極價值,但又相信相對真理和情境道德,它通過程序與規律(真理)的相互論證以及實然機制與應然程序的良性互動,收斂于某種動態平衡的社會穩態。
綜上可以得出兩點初步結論:1.現代程序觀是與現代性相伴而生的,它與(科學)理性、個人權利和契約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2.現代程序與現代社會的發展休戚與共,它在現代化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理性的科學、政治的民主和程序化管理這三種形式分別呈現于文化、政治和經濟這三個社會子系統中。了解上述觀點,當然不是說一定要按照西方中心主義去模仿或者采取東方主義式的拒絕,而是為分析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明確了一個程序化的參照系。事實上,它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與我們存在距離的參照系,而是對中國的現代化和程序化進程產生過、并正在產生著切實而深刻的影響的參照系,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甚至可以說,我們必須認真研究。
二、中國程序命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
搜索電子版的《四庫全書》發現,古代有“步驟”“程式”“程規”等詞,但沒有“程序”。同西方在現代性初生之時出現procedure一詞一樣,中國也是在現代性剛剛開始萌芽的20世紀初(1907-1913年)出現“程序”一詞。這似乎表明中國的程序觀念在一開始就具有現代屬性,也似乎昭示著我們的程序化將隨著現代化的演進而演進。
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么中國程序問題的特殊性馬上就會凸顯出來。眾所周知,中國的現代性源起和現代化歷程,相對世界其他許多國家來說要特殊和復雜得多,與其緊密相關的程序和程序化問題,想必不會單純和簡單,必然會存在許多特殊而復雜的細分問題。比如,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程序一詞,但是否一定沒有程序治理的傳統?如果有,這種傳統在哪些方面與現代程序觀念類似?哪些方面可以作為程序資源予以繼承和光大?又有哪些方面與現代程序觀念存在本質不同?哪幾個關鍵詞可以代表中國古代的類程序觀念?這些關鍵詞在第一次現代化之前的1830-1900年,在受到西方文化沖擊時是如何應對的?其內涵有無變化?再比如,1900年后的第一次現代化高潮中出現了“程序”這個詞,是否表明中國的現代程序觀念就此誕生?這個時期的程序觀有多少現代屬性?體現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與現代程序存在隔膜?當時的人們對程序觀念有清晰的自覺和深刻的反思嗎?還比如,在隨后的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進程中,我們的程序觀念受到哪些影響?最后,在20世紀后20余年興起的第二次現代化高潮中,我們在信息化時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計算機程序?它對我們的經濟和政法管理程序有影響嗎?有什么樣的影響?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程序化建設有什么樣的中國特色?這種特色與現代程序是一種什么關系?經過百余年的發展,我們的程序觀念是一種什么狀況和水平?
對于上述許多問題,學術界并不能給出一份清晰的、令人滿意的答案。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對于復雜的程序觀念及其演變歷史,我們還缺乏應有的重視,缺少系統的研究,這使得我們對程序的認識不僅相對膚淺,而且比較混亂。比如,在什么是“程序”這個基礎性的問題上,人們都還缺乏清晰的認識。普及度很高的《辭海》對程序的解釋是“按時間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驟。如工作程序;醫療程序。”[9]200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漢語大詞典》的解釋也基本類似:“行事的先后次序;工作步驟。”[10]綜合看來,程序就是做事情的“步驟”。這個解釋似乎沒有問題,但值得深究的是,兩本辭書對“步驟”又是如何解釋的呢?居然又都回到了“程序”上。如《辭海》說步驟“今指事情進行的程序、次第”[9]48;《漢語大詞典》說步驟是“事情進行的程序、次第。《后漢書·崔寔傳》:‘故圣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隨顯然,在中國頗有影響的這兩本辭書中,關于“程序”和“步驟”都形成了一個同意反復的循環解釋。對程序的科學屬性只字不提,對程序主體的自主性渾然不覺,對程序的應然性及其與實然機制的關系茫然不知,從而將具有現代中國才有的“程序”混同于中性的、古代就有的“步驟”,說明作為程序最基本屬性的現代屬性基本上被作為語言權威的詞典編撰者所無視。這大致體現了國人當前對程序的認識水平。
基本概念不清晰,其運用必然混亂。比如,季衛東在1993年就提出了“新程序主義”,并認為“程序的重要性已經達成跨學科共識”,但他在十幾年后也不得不承認“批評的言論也很強勁”[11]。而且批評者的隊伍還很強大,既有人以“實質非理性”反對程序正義[12],也有人宣稱“‘情理法并重的正義”[13]更符合中國國情。以上爭議大多發生在對程序、對法律程序必須有清晰認識的法學領域,這顯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政法程序觀?到底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現代程序觀?而聲稱“理”比“法”高明,“情理法”比現代組織理論高明,要以中國傳統“超越”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的《中國式管理》一樣[14],在比法學界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管理實務界和學術界受到熱烈歡迎,同樣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不禁要問:變革中的程序觀念必須秉承何種中國傳統,才能夠為國人所接受?它同時又必須堅持哪些基本特征,才能被看作是現代程序而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認可?顯然,目前學術界對程序膚淺而混亂的認識狀況是不可能提交一份令人滿意的答案的。
作為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對程序的認識尚且是如此狀況,我們顯然不能指望為官或為民的普羅大眾對程序概念有更清晰的認識,對程序與傳統程式有更明確的區分,對程序的現代屬性有更清醒的自覺。2016年“雷洋涉嫌漂娟被民警采取強制約束措施后死亡”及其相關的“邢某某、孔某、周某、孫某某、張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務人員玩忽職守案”[15]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引起巨大爭議,正說明程序開始受到廣泛關注,人們對程序存在巨大爭議。當然,爭議未必就是壞事,雖然沒有見到對該事件(從涉嫌嫖娼到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整個事件)的民意調查分析文件,但如此高的關注度已經使它成為中國程序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該事件的關鍵是程序問題。
三、中國程序觀念的主要線索
上述種種問題,凸顯了程序化對治理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現實重要性和理論復雜性。要想從學術上廓清這一問題,必須要對中國的程序觀念史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要有中西比較的現代視野,在認識程序化與現代化存在正相關性、認識到程序性調節機制是現代社會之存續的正式組織力量的基礎上,考察中國程序觀念如何從舊觀念中產生,如何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的歷史過程和內在邏輯,考察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組織機制和調節機制的程序性蘊含,考察程序觀念群如何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中組織機制的變遷而變遷的思想根源。通過對專門為思想史研究而開發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以及一般性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數據庫、“四庫全書”“中國知網”“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等數據庫中程序及其相關名詞的檢索,我們捋清了中國程序觀念演變的主要線索。囿于篇幅,概述如下:
1.傳統中國是以程式理性為社會正式調節機制的宗法一體化社會,中國古代存在忠孝同構、家國同構的程式資源,但有其局限性。通過檢索“四庫全書”中程式及其相關關鍵詞,我們發現儒家倫理一開始就有很強的禮的程式要求,而漢所開啟的“陽儒陰法”“儒表法里”的實質,是將更為嚴苛法家之法的程式要求納入了儒家之禮;經過宋明理學的理性化之后,禮法程式的道德化和情理化更趨自洽。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具備計劃性、步驟性、公開性、嚴密性等諸多程序性因素,為朝廷選拔官員、為寒門通過相對公平的競爭進入國家治理階層、為社會流動作出了極大貢獻,也為基層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家族治理培養了人才,但由于皇權和儒教的主導地位也導致了儒生的思想和行為僵化。科舉制度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中發揮著樞紐作用,是其典型代表;科舉程式的價值及局限,集中體現了古代官僚制度的價值與局限,體現了禮法一體化程式的價值與局限。
2.20世紀頭20余年,中國在第一次現代化高潮中誕生了程序觀念。通過檢索“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我們發現,1840年以后,在西方軍事、技術和國際法的沖擊下,中國傳統程式觀念略有松動,開始選擇性吸收西方程序觀。清末新政前,中國已經實質上接受基于世界公民預設的國際法程序,但欠缺保障國民權利的程序意識。1905年徹底廢除科舉程式[16]1907年“程序”一詞就首次出現[17],但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后人們談到民主選舉時并未用到“程序”一詞,而是受日文的影響用的是比較具有中性色彩的“手續”。在建立現代憲政國家的實踐推動下,1913年到1916年間,程序及其相關觀念(簡稱程序觀念群)出現第一個使用高峰,程序以與程式混同的形式成為中國政法領域的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但更多的是受制于權力和道德。新文化運動重構了上一時期學習到的程序觀念,但對程序的界定并不明確統一,將程序泛化,對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社會治理助益不大。比如,胡適為代表的中國式自由主義用進化論繼承理學循序漸進思想,其講求具體道德的關系網結構作為吸附在正式組織上的寄生機制,一直對中國社會發生廣泛而深刻影響。
3.20世紀中葉,中國出現過一次程序化建設的小高潮。國共合作的革命黨機制恢復了道德程式一體化的結構;中國共產黨向來注重紀律建設,它類似理學的規矩,很少使用程序一詞。國民黨尚“行”而缺乏統一道德,無法以托訓政程序之名的“手續”抵御個人關系網的侵蝕。通過檢索分析“中國共產黨基本文獻庫”“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和“中國知網”發現,新民主主義建設綱領和社會主義改造不乏現代性初生國家和蘇聯模式的理學準程序性,“程序”及其觀念群的使用量位居歷史第三位,掀起了兩次現代化高潮中的一個程序化建設小高潮。通過對慘痛教訓的反思,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認識到實然機制和科學規律不可違背,嘗試在經濟領域播種程序理性。
4.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第二次現代化高潮再次興起了中國的程序化建設高潮,雖略有起伏,但總體上呈持續上升態勢。改革開放樹立起科學的至上權威,程序理性中中性的循序漸進因素在大多數時間段里都居于主導地位,而其現代性因素也隨著全球化、現代化的自主性擴張而擴張。1978年,科學真理和科學革命突破程式性的“兩個凡是”。尊重科學知識,尊重中國國情的實際狀況和運轉機制,20世紀80年代“系統熱”中控制論的試錯性反饋調節機制與“摸著石頭過河”的“初級階段論”[18]極為契合,計算機、自動化、信息技術、經濟管理、政法程序的使用量迅猛增長;“系統的哲學”已經蘊含了超越西方程序理性的零散想法,但由于整個社會程序實踐基礎薄弱,呼之欲出的系統論程序理性并未形成氣候。90年代以后,啟蒙自我瓦解[19],普通民眾的革命意識和政治熱情有所衰減,程序理性在兩種科學主義——一是在經濟學帝國主義下獲得政治哲學上的漸進主義內涵,二是在依法治國中強化其制度化、規范化訴求。簡而言之,尊重實然機制、尊重科學規律,開放的市場經濟使經濟管理程序與世界接軌并推進政法程序進程,程序化與制度化、規范化一道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21世紀多元的價值沖突中,雖然情理化政策和道德化權力也開始回潮,但具有定息止紛的程序正義價值開始從知識分子普及到普羅大眾。當然,依然有不少人習慣于用實質理性對程序進行道德化評價,并習慣于把程序看作形式予以負面評價。不過,經過調研發現,基層,尤其是農村的干部群眾不僅經常將“認程序不認人”掛在嘴邊,而且也確實用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20]。據此我們認為,程序正義已經獲得相當的社會認同,具,有了相當的社會基礎。
綜上,程序是一個重要的現代觀念,程序化與現代化正相關。中國程序觀念的發展跌宕起伏,大致印證了國家社會的現代性與程序性的正相關性,其程序化建設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大致同步。中國程序觀念現代化的關鍵,是要在程序表達中處理好權利、權力和道德三者之間的系統關系;中國程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是要處理好應然程序與實然機制之間的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1]Andreagiovanni Reina,Thomas Bose,Vito Trianni&James A.R.Marshall,Psychophysical Laws and the Superor-ganism[J].Scientific Reports 2018(8):4387.
[2]“軸心文明與二十一世紀”專題討論[J].21世紀,57,58.
[3]大英百科全書[EB/OL].[2018-01-10].http://www.m-w.com/dictionary/procedure.
[4]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學闡釋[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
[5]Drucker,P.F.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M].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inc.,1985(ori-gin worked 1972).
[6]Green,C.D.,Operationism again:What did Bridgmansay?What did Bridgman need?[J].Theory&Psychology,2001,11(1).
[7][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8][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532.
[9]夏征農.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音序[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10]羅竹風.漢語大詞典:第八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87.
[11]季衛東.法律程序的形式性與實質性:以對程序理論的批判和批判理論的程序化為線索[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3(1).
[12]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13]馮象.正義的蒙眼布[J].讀書,2002(7):100-103.
[14]曾仕強.中國式管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5]雷洋[EB/OL].[2018-01-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6%B4%8B/19658789?fr=aladdin.
[1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249.
[17]劉式訓.使法劉式訓致外部法日協約似有干涉我邊務意電[A].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三·二[M]//劉青峰,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
[1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9.
[19]許紀霖,羅崗.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20]涂明君.通往善治之路:互補系統論視角下國家治理現代化求索[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