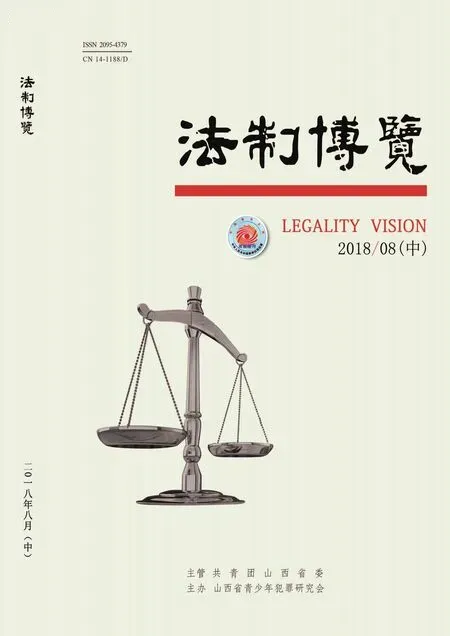偶然防衛定性再認識
——對“無罪說”和“未遂說”的質疑
張寶方 楊 揚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偶然防衛概述
(一)偶然防衛概念的界定
偶然防衛是學術討論過程中基于正當防衛的概念而引申出來的一個學術概念,我國刑法典只在第二十條規定了正當防衛而沒有偶然防衛的明文規定。根據法條文的規定,通說認為構成正當防衛需要五個構成要件,分別是正當防衛的對象條件、起因條件、時間條件、防衛意識條件以及防衛限度條件等。假設行為人沒有防衛意識在此情況下,偶然防衛的情形就會發生。國內學界對于偶然防衛概念的界定,概括來說有以下幾種。
第一,“偶然防衛是指行為人故意對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巧遇對方正在進行不法侵害,其行為客觀上制止了他人的不法侵害的情況。”第二,“偶然防衛是指故意或者過失侵害他人法益的行為,符合了正當防衛客觀條件的情況。”第三,“偶然防衛是指行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實行不法侵害,而故意對不法侵害人實施侵害行為,客觀上發生了防衛效果,且符合正當防衛限度條件的情形。”第四,“偶然防衛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并沒有防衛的意思,也沒有面臨緊急不法侵害的認識,客觀上卻起到了正當防衛的效果。”第五,偶然防衛指“行為人出于一定的犯罪故意,實施其行為,但該行為客觀上發生了防衛效果的情形。”可見,以上觀點的核心爭議主要集中在偶然防衛中是否存在過失偶然防衛問題以及是否需要限度的問題。對于是否存在過失偶然防衛,不法侵害的責任形態既有故意也有過失,此處不能排除過失情況的存在。關于限度問題,只是針對正當防衛而言的,換言之只有滿足正當防衛的其他條件,除了刑法第20條第三款規定的特殊防衛才要求防衛限度。偶然防衛在通說下不滿足防衛意思的條件而不構成正當防衛,因而所謂限度就無從談起。對上述的眾家學說做此番理解的話就不難對偶然防衛做如下定義:偶然防衛是指行為人在沒有防衛意識的情況下其不法侵害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防衛效果的情形。實質上是“不法行為人(防衛人)對不法行為人(侵害人)的侵害”。
(二)偶然防衛的特征
第一,偶然防衛具有偶然性,行為人沒有防衛的意思。一方面行為人根本未曾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害,同時,對于防衛效果是否發生也沒有明確的追求意思,不持該種目的。而這種所謂的有益后果只不過是行為人的所進行的非法傷害行為意外偶然地抑或是碰巧造成的。甚至可以說偶然防衛屬于一種“無心插柳”的行為。第二,偶然防衛具有客觀性,此處所說的客觀性往往是指行為人所實施了非法傷害行為之后阻止了另外一個人的非法傷害行為,這種意外的組織在客觀上使得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或者其他權利免受到侵害,這樣從效果上來看適合正當防衛的客觀效果、因而我們說偶然防衛具有客觀性。當然有人認為還應當包括他人正在進行不法侵害這一特征,個人認為,這在正當防衛中是必要的,但是就偶然防衛來說再填此項雖說不影響正確性,卻是可以影響偶然防衛特征的顯著性,遂不再單列。
(三)偶然防衛的類型
根據上文對偶然防衛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從客觀效果和主觀兩方面對偶然防衛作以類型劃分。從客觀效果方面,偶然防衛可以分為緊急救助型和自己防衛型。所謂緊急救助型就是偶然防衛的效果發生在無辜第三人身上,行為人的偶然防衛客觀上保護了第三人的利益。最典型的的結構模式就是:甲槍殺了正在舉槍瞄射丙的乙,從而使得丙獲救,但是甲對乙正在殺人這件事毫不知情。案例一,顯然防衛的效果是發生在第三人丙身上,緊急救助了丙的生命,遂稱緊急救助型偶然防衛。而自己防衛型偶然防衛是指偶然防衛在兩人之間,防衛的效果發生在行為人身上,但是行為人對于被害人正在不法侵害行為人卻是毫不知情。這是一種雙向侵害的事件。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案件幾乎不可能在實務中發生,因為這種巧合的瞬間實在太罕見。但是試想如下案例:A在B的房間布控定時炸彈后站在房外準備引爆,此時房間內的B開槍射殺了A而炸彈未能引爆,但是B對A布控炸彈的事情卻一無所知。案例二,此番案例恰是自己防衛型偶然防衛的最經典案例。雖說在實務中未找到真實的案例,但是,這種假想的案例也不是沒有可能發生。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來說,偶然防衛可以分為故意型偶然防衛和過失型偶然防衛。此處故意和過失主要是指行為人作出行為時內心的主觀態度而不是防衛意思。如在案例一中,甲瞄槍殺乙是故意的,則是故意型偶然防衛。倘若甲是擦槍走火屬于過失的,則構成過失型偶然防衛。
二、對偶然防衛的定性的域內考察
(一)傳統通說的定性——犯罪既遂說
“我國刑法通說和司法實踐在犯罪的認定上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偶然防衛的定性在傳統觀點看來由于缺乏防衛意思不構成正當防衛,同時依照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標準行為人勢必是構成犯罪的。因為在偶然防衛中,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加害的故意,客觀上在故意心態的支配下也實施了一定的加害行為,而且也發生了行為人積極追求的結果,完全符合犯罪既遂的標準。至于客觀上防衛效果只是在量刑時加以考慮。比如“偶然防衛一方面是不法侵害行為,另一方面在客觀上排除了他人的不法侵害,發生了法律允許的后果,這種結果在處理案件時應當適當考慮。”但隨著德日刑法理論的引進,結果無價值和行為無價值的的爭論也發生在我國刑法領域。國內對于偶然防衛的定性有了新的論調且新論調的支持者在不斷增加,具體說來有行為無價值角度得出的犯罪未遂論和結果無價值角度得出的無罪論。
(二)行為無價值角度——犯罪未遂論
所謂行為無價值:“大體而言,對于與結果切斷的行為本身的樣態所作的否定性評價,稱為行為無價值,行為無價值論者認為行為本身的惡以及行為人內心的惡是違法性的根據。”如果按照通俗的說法去理解,這一學說的核心在于行為人的行為反價值,亦或是說某種行為觸犯了某種規范而被視為無價值的行為因此受到刑法的規制。行為無價值二元論認為,“規范違反和法益侵害同時決定違法性,不僅是法益侵害結果,而且行為方式以及行為人的意圖。目的等內容也是決定違法性的根據。”根據行為無價值二元論者的上述思路,刑法保護規范,但是刑法所保護的是和法益緊密相連的規范,在違法層面行為人違反了以法益為支撐的規范。就此和偶然防衛相聯系,行為人的確違反了“禁止殺人”這樣一個保護他人生命權法益的規范,但是就客觀情況來看,不論是案例一還是案例二,客觀效果是保護了生命權法益。沒有法益受到傷害,所以未發生危害后果,于是就有了未遂論的說法。
“在基于殺意的偶然防衛行為中雖然防衛人殺死了一個罪犯,該結果法律并不反對,可以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殺人既遂的結果無價值,但有未遂的結果無價值。”由此可以發現,周光權教授是從行為當時的情況來判斷的,假設某一個行為該行為更換了時間以及空間場合,但是這種偶然防衛的行為所具有的剝奪其他人生命的危險一直沒有消減,這就說明始終存在殺人未遂這個層面上的結果反價值,如果要是能夠進一步地去考查防衛人持有犯罪故意但是沒有絲毫的防衛意思,那么行為方面就是反價值的,只不過是未遂罷了。由此看來如果在結果無價值和行為無價值同時并存的情況下,偶然防衛的違法性無論如何是不能夠被阻卻的,所以應該把這種情況按照當作犯罪的未遂去處理。如果將偶然防衛認定為正當防衛毫無疑問將會對社會大眾的樸素情感以及內心深處的秩序感造成一定的傷害,內心的安全感也無從談起,沒有合適的導向也就會無所適從。與上述周光權教授觀點的結論相類似。陳興良教授認為“偶然防衛客觀上存在防衛效果,主觀上不具有防衛意思,不符合我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但也不應當全然否定偶然防衛客觀上的防衛性,在殺人型的偶然防衛場合,由于存在相應殺人行為和防衛行為的競合,對此應以殺人罪的未遂處理較為適宜。”
(三)結果無價值角度——無罪論
結果無價值論的最主要論調是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會造成侵害法益的結果作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所在。倘若一個行為傷害了法益,那么這種行為就是一種結果反價值的行為,因而需要受到刑法規制。如張明楷教授所言:“結果無價值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目的與任務是保護法益,違法性的實質是法益侵害及其危險;沒有造成法益侵害及其危險的行為即使是違反社會倫理秩序,缺乏社會的相當性,也不能成為刑法處罰的對象,應當客觀的考察違法性,主觀要素原則上不是違法性的判斷資料,故意、過失只是責任要素而不是違法要素”。依此結果無價值的立場,在偶然防衛中,行為人的行為由于不僅沒有造成實在的法益侵害,反之保護了另外一個法益,因而就不具有違法性。倘若采取乏味意思不要說的觀點,便會得出偶然防衛無罪的結論。其實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偶然防衛與通常的正當防衛并無差別,因為按此邏輯只要沒有超過防衛的一定限度,便可能意味著某種更為優越的法益受到了保護。單純從法益衡量的話是沒有任何損失的,也就沒有違法性,換言之法益保護阻卻了違法。
三、對于“無罪說”和“未遂說”的質疑
(一)結果無價值和行為無價值的哲學根基溯源
張明楷教授認為行為無價值論的根基是規則功利主義,而結果無價值論的根基是行為功利主義。所以二者實質上都是功利主義的表現。而在將兩者都劃入功利主義的范疇后,他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結果無價值論采取的是法益衡量的立場,因而屬于行為功利主義;二元論不是直接進行法益衡量,而是根據行為是否違反了保護法益所需要遵守的規則來判斷,因而屬于規則功利主義。”
筆者對于這樣的觀點有著不同的理解。行為無價值理論始終強調的是社會規范的保護,哪怕是二元論的行為無價值也是在說法益基礎上的倫理保護。但是倫理規范體現的是社會的價值準則,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康德的三大律令——普遍行為法則、人是目的、人為自然界立法是相契合的。所以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行為無價值論將道義論作為哲學根基,規則功利主義不是其實質。同時,由于結果無價值論的核心著眼點在于法益,也就是說犯罪的實質是法益的侵害,倘若無法益侵害則不違法。至于法益侵害的判斷標準,結果無價值論者則引入了利益優越理論,利益是可以進行比較權衡的,一般來說生命權高于健康權,健康權高于財產權,財產權之間便進行數量上的比較,甚至是基于生命權之間也可進行衡量性。誠如功利主義大師如邊沁所言:“功利原理是指這樣的原理:它按照看來勢必增大或減小利益有關者之幸福的傾向,亦即促進或妨礙此種幸福的傾向,來贊成或非難任何一項行動。”而結果無價值恰恰符合邊沁功利主義哲學所宣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要求。如果再細究也可以說“結果無價值是行為功利主義,但兼顧規則功利主義。”
(二)關于結果無價值“無罪說”和行為無價值“未遂說”的檢視
如果如上文所說結果無價值論者只是在宏觀上表現出功利主義的立場傾向的話,那么在偶然防衛的定性上,結果無價值論者所得出的無罪論則是徹底的秉持了功利主義的價值哲學。在此我們試以上文中提到的兩則案例加以分析。
在案例一中,結果無價值論者得出甲無罪的結論核心論據在于甲救了無辜的丙,由于乙正在舉槍瞄射丙,而從結果上看乙被殺丙獲救,意欲殺人者被殺無辜者獲救,這就是結果無價值論者所說的沒有法益侵害進而得出甲無罪的結論。如此一來三個人中只需要有一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遠比兩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要合理,于是就維護了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就此案中為什么在缺乏防衛意識而不構成正當防衛的情況下偏偏乙的死亡就是合理的,是不需要甲付出代價的?既然甲對于乙正在射殺丙全然不知請的話我們甚至可以把整個案件分成兩個案件去看待:一個是甲殺了乙;另一個是乙殺害丙未遂。這樣的話還能說是甲無罪嗎。或者再換一個角度,結果無價值論者主張在考察整個案件時,需要從客觀出發,“按照從客觀到主觀認定犯罪的路徑,應當排除防衛人的犯罪的成立。”我們同樣循著這樣的思路去理解,那么對于乙的死亡該如何解釋,因為從客觀上出發乙也僅僅是瞄射而已,在未發生射殺丙的情況下他卻是為自己的瞄射行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種代價源自于意欲殺死自己的甲,而為何甲卻無需為此付出代價。顯然這是結果無價值論無罪論無法解釋的。
案例二也是同樣的道理,B在對A布控炸彈準備引爆殺害自己的情形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開槍殺死了A就是一個簡單的殺人案。從客觀角度出發,A布控炸彈也僅僅是未遂而已,其未遂的情形無須也不能成為B殺人無罪的理由。如果真要允許B無罪,那么假設在此案中要是A的手速快,先引爆炸彈,B來不及開槍而被炸身亡,無罪的就又會變成A。很明顯這就會嚴重導致刑法的恣意性,產生“先下手為強而無罪”的可怕導向。倘若我們按照道義論的眼光從普遍行為法則的角度去審視偶然防衛。那么就不難看出行為人處于殺人的故意同時做出殺人的動作,這本身在道義上是非法的、應受譴責的。按照道義報應論者康德所提倡的普遍行為法則,在我們實施某一個行為時之前,必須應先問問我自己做出這一行為的規則基礎是什么。接著要思考這條規則是不是普羅大眾所普遍遵守的規則。倘若某一個行為沒法得到普遍化的認同,它就是不正當的。那么以道義論的思想審視偶然防衛,不得殺人的道德律令已被偶然防衛所踐踏,即便以殺人的故意所實施的行為偶然地帶來了善的后果(正當防衛的后果),但是,偶然防衛行為無法得以普遍化,其顯著特征就是偶然隨機性,社會需要穩定秩序、需要良善的價值去維護,而不得殺人就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我們不能犧牲這一價值而免除對于偶然防衛者的否定評價。
對于二元論的行為無價值所偏向道義論這一點本文是極為肯定的,但是這一論者卻在偶然防衛上得出了未遂說的結論使得其立場有或多或少偏離了道義論。二元論的行為無價值認為刑法保護規范,但是刑法所保護的是和法益緊密相連的規范,在違法層面行為人違反了以法益為支撐的規范。就此和偶然防衛相聯系,行為人的確違反了“禁止殺人”這樣一個保護他人生命權法益的規范,但是就客觀情況來看,不論是案例一還是案例二,客觀效果是保護了生命權法益,所以便得出了未遂的結論。但是本文堅持認為法益作為一種法律所要保護的利益,其本身比較模糊,每個人對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利益必須要以倫理價值做支撐,只有在倫理的規制和束縛下,利益才不會成為脫韁之馬。換言之,如果沒有倫理規范的引導,利益就會成為各種非法行為的擋箭牌。我們保護利益是因為這種利益是倫理規范倡導的利益,是值得刑法加以保護的。比如說刑法之所以要保護生命權、身體健康權、財產權等各種個體法益,是因為這是倫理規范的命令。“法益只是倫理規范的載體,在規范以外,法益別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