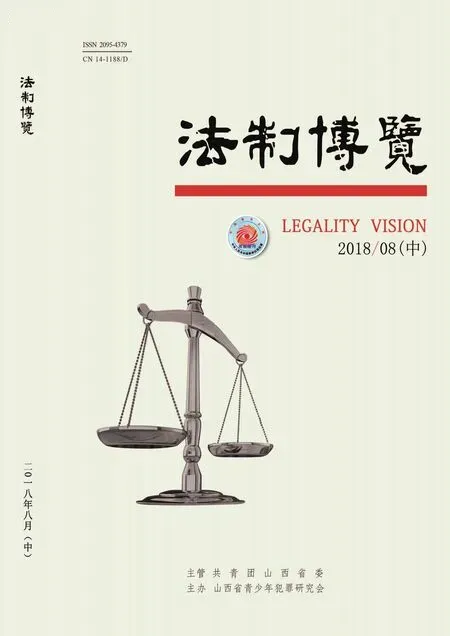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的刑法規制
謝潤康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校園暴力是指發生在校園或主要發生在校園中,由同學或校外人員針對學生或老師的身體或精神所實施的造成某種傷害的侵權行為。直接傷害到在校教師、學生身心健康和財產安全的暴力行為,都能用“校園暴力”來定義。①近年來,校內同學之間的互相斗毆致死、故意傷害事件屢見報端,此等校園暴力犯罪使人們震驚、愕然于如此惡行竟發生在校園這片“圣地”之余,更是給全社會拉響了警鐘,意識到現今校園暴力絕不僅僅是小孩子之間的玩鬧,更呈現出一種殘忍化、復雜化、違法與犯罪行為相交織的犯罪趨勢,部分校園暴力行為更是具備了需要用刑法規制的社會危害性。校園暴力犯罪問題已成為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
一、我國目前對校園暴力犯罪刑法規制的不足
目前,我國對于校園暴力犯罪刑法方面的規制體系仍十分不完善。在立法層面,現有的刑法及其相關規定無法發揮其預防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在司法層面,我國缺乏相應的適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司法指導政策和司法機構作配合。以下筆者將具體論述。
(一)立法層面
1.現存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第三十八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滿十六周歲而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由政府收容教養。”上述的兩個法條,是收容教養制度是指根據刑法規定,對因不滿16周歲而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收容教養一般由當地行政公署以上級別的公安機關審批,由當地少年管教所負責執行。然而,收容教養制度的相關規定除了1979年我國刑法中首次提及“收容教養”這一詞外,與之相關的有權機構、制度內容、具體規定都在法律中沒有規定。由于缺乏具體系統的規定和與之配套的法律法規,在實踐中,收容教養制度出現了許多問題。收容教養的具體期限不明確,一般為1-3年,而其本身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質,時間長,處罰較重,具有刑罰的特點,卻又只由公安機關決定收容教養時間,缺少司法機關的監督,容易出現濫罰或不罰的亂象。
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我國現今有《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部法律和若干關于處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的司法解釋。但是,此類法律和司法解釋的通病在于只規定了應當如何做,沒有規定若違反之,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或應當依照什么法律法規進行處理、由何機關部門進行處理?縱觀這兩部法律,對政府機關和學校等單位的要求皆為宏觀上教育、宣傳的責任,做到一般預防;但個別預防或在犯罪已發生時應如何處理,有關部門應如何應對,皆是無明文規定,在實踐中呈現“無法可依”的狀態。
工讀學校作為未成年人另一項重要矯治措施,在立法層面也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中規定:“對有本法規定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相互配合,采取措施嚴監管教,也可以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工讀學校作為我國對不足刑事責任年齡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行為矯治的重要措施,其從法律依據到運行再到監管存在著一系列“無法可依”,立法缺乏可操作性的問題,令現實中一大批實際上違反刑法,只因為不足刑事責任年齡而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得不到有效的懲戒和教育,極不利于其行為矯正,重回正軌。
2.我國缺乏專門立法
校園暴力犯罪的惡行案件頻發,嚴重威脅著我國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校園暴力犯罪,已成為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但是,在法律層面上,首先,我國對“校園暴力”“校園暴力犯罪”等特定名詞,并沒有明確清晰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的范圍尚未由相關的法律規定進行明確。當下理論學界中,雖然許多學者對“校園暴力”“校園霸凌”“校園欺凌”“校園暴力犯罪”等相關概念進行定義,但是缺乏法律定義,不僅容易使社會上對校園暴力犯罪的看待和處理存在不理性和誤區,更是難以用法律手段科學、系統地應對校園暴力犯罪問題。
其次,目前我國對校園暴力犯罪及其預防等方面并無專門立法。縱觀發達國家,十分重視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尤其是以專門立法的方式保障其在校園環境內得到有效保護。美國多個州早在2000年就通過了禁止校園欺凌的法案,對校園暴力實施“零容忍”政策;日本有專門的《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韓國有《校園暴力預防及對策法》,反觀我國,在校園暴力犯罪日漸成為一大社會問題的當下,卻缺乏與之相對應的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法。與之相近的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專門、全面、系統的預防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的法律,目前我國仍處于空白狀態。
再次,在當下我國缺乏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專項法律的情況下,各地雖然分別制定了有關校園安全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但由于缺乏統一、系統的法律牽頭,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呈現松散、零碎的狀態,難以有效發揮其預防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保護未成年人校園身心健康的作用。此為其一。其二,當前有關校園安全的地方性法規主要涉及的是《中小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防范與處理條例》、《社會治安管理條例》、《學校安全條例》。其中,已制定《中小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防范與處理條例》的省市有:北京市、湖南省、銀川市、鄭州市、蘇州市、西安市、合肥市等等。已制定《社會治安管理條例》的有黑龍江省和天津市等,已制定《學校安全條例》的有天津市、黑龍江省、昆明市,截至止2016年3月,教育部尚在著手研究起草學校安全條例。縱觀上述條例,雖然有關于學生對學生的處罰規定,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有關規定,地方法規能做出的處罰有限,只能模糊地規定“學校可以按照學籍管理的規定給予相應處分;情節嚴重的,由有關部門依法處理。”②由此可見,在目前校園暴力犯罪相關立法體系零散的狀態下,對校園暴力犯罪的規制和對犯下暴行的青少年的懲戒和矯治,無法達到有效效果。
(二)司法層面
在校園方面,目前我國中小學校園內,普遍并沒有設立應對校內校園暴力突發事件的專門安全保衛措施。第一,學校保安一般只負責教學設備及時開關、檢查進出校園人員的身份、維護校內教學設備的正常運行等維護性工作,關于校內巡邏,校內學生安全保障問題基本上難以處理,亦無權處理。再者,學校保安在應聘時和崗位要求上并無要求其對校園暴力突發事件具備應急處理和日常防范的技能,到崗后亦無對其進行專門的應急技能和處理暴力犯罪突發事件的技能訓練,故而在校園暴力犯罪發生時,學校保安基本上起不到及時制止,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的作用。第二,我國校園內普遍缺乏公共場所全天候攝像錄像裝置,特別是在校園內的“死角”位置,例如樓梯轉角、走廊盡頭、雜物間等閉路電視沒有覆蓋的地方,或是廁所內、宿舍內這種不方便安裝攝像頭的地方,是校園暴力犯罪的“盲點”和“黑點”所在,極其容易發生校園暴力犯罪事件。校園由于其環境的特殊性,造成在案件發生過程取證困難,認證困難的情況,不利于后續司法程序的展開。
在公安方面,目前出現的情況是,未成年人所為的,特別是十四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所為的校園暴力犯罪案件難以被公安機關正式受理。因為辦理此類案件一般最終難以被檢察院立案或作不起訴處理。同時,目前缺乏對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相關指導意見,對青少年仍適用寬大處理、寬容處理;由于此類案件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又是在校園這種特殊環境下,令其辦理此類案件時調查取證、驗傷確責流程負責,且最終又難以達到刑事立案的程度,導致校園暴力事件一般難以進入法院層面,就連許多校園暴力犯罪事件亦因此不能經過法院審判,導致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校方對校園暴力犯罪事件的重視程度不夠,無相關人員和設施配備,公安部門對校園暴力犯罪事件怠于處理、工作壓力大、怕麻煩的惰政心態在作祟,造成在此類事件發生時,公安機關一般將此事推給學校處理,當未成年人不滿十四周歲時更是如此,而學校更是希望將此事大事化小,或促成雙方調解,或直接將施暴學生開除學籍了事,導致校園暴力犯罪有關施暴人員一般得不到及時懲戒,而更加囂張;其他潛在失足青年看到情況如此就更加蠢蠢欲動,校園暴力犯罪事件得不到正確的處理,易釀成更多的慘劇。
二、各國對校園暴力犯罪的法律規制
(一)美國
美國對于校園暴力犯罪問題十分重視,并采取“零容忍”政策,對關于學生在校安全有關方面均有相關法案進行規制。從2000年開始至2015年4月為止,美國50個州均通過了反校園欺凌法案。③而美國聯邦政府也先后出臺了預防校園暴力犯罪、保障校園安全的相關法案:1994年出臺有《安全、無毒品的學校和社區法案》、《學校禁槍法案》;2001年發布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上述法案對校園暴力犯罪問題有一定抑制和預防作用。例如,在《學校禁槍法案》中,對接受了聯邦教育基金的各州提出了硬性的校園安全指標,未按聯邦要求配備校園安全人員和設備的,聯邦將取消基金發放;《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要求各個州必須滿足學生對社區內各校園安全情況的知情權,包括何謂“長期處于危險境地的學校”及其認定標準、相關說明、社區內學校校園暴力事件的統計數據和事件處理結果等校園安全情況,均需公開。
美國在校園內部也設立警察制度,旨在加強對校園環境的監控和對犯罪的防治。早在1903年,美國已經建立校園警察制度,而1990年美國聯邦頒布的《1990年校園安全法》,正式落實和規范了校園警察的合法性依據和執行依據。1999年,美國各大中小學開始開展由美國司法部社區警務辦授權、以合作協議的形式的COPS In Schools:Keeping Our Kids Safe 項目。校園警務是學校與警察建立在“校園”這一特殊環境下相互配合,共同建立校園安全防衛系統的具體體現。通過學校領導和School Resource Officer所達成的聯盟,在校內建立防暴小組,在發生校園暴力突發事件時能迅速應對,遏制事態惡化,保護受害者,將施暴者按照正常合法的程序展開調查,有利于共同抵御校園暴力給學校師生帶來的傷害。
(二)日本
日本校園欺凌事件同樣處于高發狀態,因欺凌導致學生重傷或不禁凌辱而自殺的事件屢屢發生。為了處理這一社會問題,日本在2013年6月通過了《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正式為校園暴力問題進行專門性立法,詳細規定了各級政府及學校在防范欺凌事件發生中的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并對具體的應對策略做出了詳細的要求。根據該法案的要求,當有嚴重的欺負事件發生時,文部科學省和各地方自治體都有義務進行逐級報告,各教育委員會和各級學校都要設置欺負事件相關調查機構。對于威脅到學生生命的事件發生時,學校要迅速開展問卷調查并啟動緊急預案進行有效處置;如果被認定為犯罪行為,應當及時報警并提供必要的配合,協助警察進行調查取證。同時,日本也有《兒童福利法》、《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等一系列完整的法律法規輔以應對校園暴力問題。
此外,日本有專門針對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的、獨立于成年人的刑事立法體系,其中包括《少年法》(2014年最新修正)、《少年審判規則》(2015年最新修正)、《少年院法》。對于青少年違法行為或不良行為,日本亦有《少年警察活動規則》、《少年指導委員規則》進行詳細的規定。此外,對于少年案件的搜查、審判、鑒定、賠償、處罰方面,日本的《刑事訴訟法》、《犯罪搜查規范》、《少年審判規則》、《少年鑒別所處遇規則》、《少年院處遇規則》、《有關少年保護案件賠償的法律》均有專門性的規定。
日本同樣建立了校園警察制度,實際上,日本的“少年警察活動”模式正是以美國校園警務制度為參考對象,立足于本土的《少年法》、《少年警察活動規則》及《少年指導委員規則》建立。日本校園警務的基本特點是,在校內設立警務處,建立對校園內日常巡邏和監測,通過教導涉嫌違法的少年、防控校園暴力犯罪的發生、及時疏導少年不良行為以及應對校園暴力犯罪突發事件,遏制事態進一步惡化等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維護校園安全。
(三)經驗與啟示
縱使各國治理模式和方法有所不同,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均十分重視教育,重視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面對校園暴力,首先要提高重視程度,將之作為重大公共議題討論,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解決,要從國家層面端正對校園暴力的態度,一切威脅到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因素都需要被嚴肅認真地解決。
其次,我國需要出臺專門性、專項性針對校園暴力犯罪的法律及與之配套的有關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政策。以專項立法為先導,為現今處理校園暴力犯罪問題的各個部門提供指引,并進一步明確各機關單位、部門職能和職權,明確其責任范圍,做到有法可依。
最后,建立在我國現有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力量,發揮社會各界的力量,公權力機關、學校、社會矯正機構等進行通力合作,以專門性立法為依據,使校園暴力犯罪治理走向法治化治理道路。
三、對我國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刑法規制的建議
(一)增加規制校園暴力犯罪的專門立法和司法解釋
校園暴力業已成為一項重大的社會公共議題,與未成年人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一樣,校園暴力犯罪問題同樣需要被視為需要專門立法應對處理的社會性問題。我國此前曾出臺過各種通知和辦法,其中不乏如2016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此類中央層面出具的處理通知,但是一來,“通知”“決定”形式的文件從法律意義上位階不高,適用范圍有限,當出現犯罪事件,需要引用之處理具體事務時常出現效力不夠的尷尬局面;二者,此類文件未通過詳細調研和專家研討得出解決,其科學性和民主性不可與法律相提并論,其系統性、完善性更是不可等量齊觀。
參見他國經驗,針對校園暴力犯罪出臺專門性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有關部門、單位的職權、職能和職責,建立預防校園暴力犯罪的整套制度和面對突發校園暴力事件時的應對對策及事后處理措施,令各單位機關在處理該類事件中有法可依,嚴格按照法律處理此類事件,使校園暴力犯罪治理走上法治化道路。
(二)加強校警合作,預防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的發生
結合我國國情,加強校警合作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參照社區警務的成功經驗,在校園內設立警務崗,定期巡視校園,避免在監控設備無法顧及的地方發生校園暴力犯罪;二是加強公安機關與學校的合作,學校應定期排查校內是否存在校園暴力的情況,及時向公安機關反映;公安機關應設立有關校園安全的專門負責人,負責轄區內中小學的校園安全,及時應對校園暴力犯罪突發事件和事后處理。
當然,校園警務及校警協作活動的開展必須以法律為依據,要使之發揮作用,法律應當對其具體內容,例如校園警察的任職條件、職權和職責、責任和后果等進行詳細規定,才能使之成為具備現實可操作性的制度。
(三)擴大社區矯正等非監禁制度應用
我國對青少年犯罪現行的刑事政策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八字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針。筆者在提議加強對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的刑法規制,讓青少年對他們已經觸犯刑法的行為承擔應有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亦贊同對青少年不宜濫用監禁刑,在滿足一定條件下應適用緩刑,加強社區矯正等非監禁刑制度的運用。社區矯正強調將犯罪人置之于社會進行改造,不將他們隔絕于社會,避免監禁矯正過程中罪犯之間的相互影響,交叉感染。未成年人的模仿能力強,可塑性強,對未成年人適用社區矯正也正是照顧到他們特殊成長時期的心里承受能力,將他們往正途上指引,接受社會矯正,從而達到矯治和改造。
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研究出臺了《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對社區矯正組織、管理及法律監督的主體作出了明確規定,并對矯正對象日常監管、獎懲制度作出了規定,并提出了對未成年人適用社區矯正的八項指導方針。在此基礎上,筆者建議為加強對青少年的重視,制定專門適用于未成年人的專項社區矯正法律與適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并且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未成年人適用緩刑、適用社區矯正等非監禁刑罰程序等法律法規的完善,發揮社區矯正對青少年行為的矯治作用,使其重回正途。
[ 注 釋 ]
①人民日報、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人民日報三問校園暴力:懲罰不夠還是教育不足?2018-1-19.
②《貴州省學校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預防與處理條例》第四十二條,2014年11月1日開始施行.
③周樂娟.我國預防未成年人校園暴力犯罪問題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論文,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