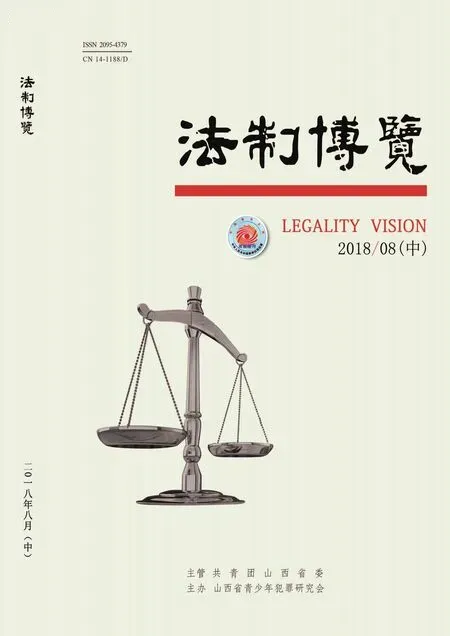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中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的現實困境與保障路徑
丁德昌 丁祉冰
1.湖南文理學院法學院,湖南 常德 415000;2.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北京 102249
一、農村宅基地發展權內涵闡釋
農村宅基地是農村用于以建造村民個人私人用房為核心的包括用于與居住生活有關的附屬建筑物以及生活附屬用地。農民宅基地發展權,是指以提高農村宅基地利用效能而轉讓給他人或者對農村宅基地進行立體化開發綜合利用的權利。農村宅基地發展權是從農村所有權中分離出來的相對獨立的權利,具有財產的可轉移性。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很多農民在城鎮謀生發展甚至在城鎮長期定居,農村房屋長期空置甚至宅基地大量荒蕪。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的設立宗旨是為了提高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效能,提高其使用效益。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一方面,由于大多農民擁有較大的宅基地;另一方面大多農民由于資金有限而缺乏發展的動力,使得自身發展較為緩慢。設置宅基地發展權,不僅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能為農民通過充分利用宅基地發展權獲得一定資金提高其融入城鎮化生活發展的資金支持。農民大多宅基地面積比較大,對于哪些沒有融入城鎮的農民在不影響自身居住的前提下,能行使農民宅基地發展權,轉讓或出租部分宅基地使用權。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宅基地的社會功能除了社會保障功能外,還在向資本功能演化。農民通過行使宅基地發展權獲得一定資金,從而改善農民自身生活條件,不僅對于促進農民主體性發展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于推動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新型城鎮化化進程中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缺失之現實困境
(一)農村宅基地所有權缺失,發展權立法缺位
在立法層面,我國法律沒有確立土地發展權,當然也就沒有賦予農民享有農地發展權。農村宅基地發展權屬于農地發展權的一個子權利,現行法律并未確立農村宅基地發展權。而農地發展權是從農地所有權的派生權利。作為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的母權利的農地所有權也存在明顯的立法缺陷。一方面農村宅基地所有權主體模糊。《土地管理法》第8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然而,改法對農民集體的內涵并未進行明確解釋。同時,《土地管理法》第10條又規定鄉鎮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擁有土地的經營權和管理權,并未規定其享有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筆者認為,真正的“農民集體”應該是一定范圍內的農民個體的集合;問題是,立法又未明確規定從而使得農民集體處于一種模糊狀態,“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權主體與農民集體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不清晰。”[1]另一方面,農村宅基地所有權權能缺失。《物權法》第184條和《擔保法》第37條均規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地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同時,《土地管理法》第63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
立法的缺失必然導致實踐的悖理。我國在立法上并未明確設置農村宅基地發展權,就連作為農地發展權的母權利農地所有權也存在主體模糊和權能嚴重缺失,故而在實踐中存在嚴重誤區。在現行制度背景下,很多試圖進城謀發展的農民往往農村的房子賣不掉,而城里的房子買不起。農村的房子即使賣掉也往往非常低廉。如果農民擁有農村宅基地發展權,農村在出售農地的時候獲得較為合理的資金,從而夯實欲在城鎮發展的農民獲得城鎮購房的啟動資金,從而有力地推動農民城鎮化進程。
(二)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缺失,導致實踐流轉效益低下
“法律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2]權利保障立法層面的滯后或缺失,并不能完全阻止現實中人們的權利訴求及其追求其權利實現的步伐。現實中,很多農民由于融入城鎮生活,農村的宅基地及其房屋對其缺乏使用價值,出售轉讓往往是大部分這類農民的基本需求。實踐中,農民因為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的缺失,農民不能基于自我發展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宅基地發展權,將宅基地進行有效流轉。在政策層面禁止農村宅基地向城鎮居民流轉。1999年5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規定,農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用農民集體土地建住宅,有關部門不得為違法建造和購買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200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土地管理的決定》以及其后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等系列文件,都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禁止農村宅基地向城市居民出售。法律雖然規定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可以流轉,然而本村本組村民經濟狀況基本處于一個層面,農村宅基地及其上面的房屋往往只能低價。很多農民要么忍痛割愛,要么低價裝讓,導致農民房屋財產“沉淀”,農民宅基地發展權很難實現。農民自我財產很難變現,難以為其在城鎮落戶提供有效的經濟支撐。
(三)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缺失,導致征地中農民權益受損
在新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開放商對土地的需求與日俱增。在國家強大的耕地保護政策下,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以低廉成本擠占農村宅基地,然后以高價出讓給開發商進行商業開發。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農民集體的虛化導致包括農村宅基地產權主體的模糊,“農村宅基地產權的模糊化有助于強化政府的宅基地處分權。”[3]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代表實踐中就是村組干部。只要開發商糾結政府部門擺平村組干部,包括宅基地在內的農民土地利益往往就是待宰的羔羊。由于我國法律沒有賦予農民農村宅基地發展權,農村村民缺乏保護自身利益的法律依據。即使土地征用后在分配過程中,村干部往往借口集體利益或基于腐敗侵吞農民包括宅基地在內的土地征收款。如果法律賦予農民宅基地發展權,農民宅基地征收與否、利益享有,農民自身當然享有決定權,必將成為農民抵御農村宅基地征收中農民利益受損的法律利器。沿海有些地方政府利用農民退出宅基地復墾后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從而解決城鎮化戶口的條件,嚴重侵犯了農民宅基地發展權。
三、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宅基地發展權保障路徑
(一)制定《農地發展權法》,賦予農民享有宅基地發展權
立法保障是人權的制度前提,只有通過立法將應然的理想層面的人權納入到現實層面中。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由效的制度安排。”賦予農民依法享有農村宅基地發展權,是廣大農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的重要途徑。為了保障農民享有宅基地發展權,制定《農地產權法》首當其沖,農地發展權應作為重要內容予以規定。農村宅基地發展權作為農地發展權的重要子權利在該法中如下幾點必須重點規定:
首先,宅基地發展權的所有模式。農村宅基地發展權應配置給農戶,由農戶享有因土地發展而享有土地利益。農村土地是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按理農地發展權理應規集體所有,因為宅基地發展權是農地所有權的派生權利,或者說是一種從權利。在法理上,從權利的權屬理應歸屬于主權利。然而,在農村,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理應是村民小組所有;農村宅基所有理應屬于農村村民小組所有。但這種農村集體所有是一種抽象所有,村民分配的宅基地是按戶分配的,是戶戶享有的農村基本生存權利。在現實中,農村村民小組是往往除了一個履行“上傳下達”小組長外并不是一個政治實體,村民領導小組功能嚴重退化。如此就造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處在一種模糊狀態,農村土地主體資格處于虛位。因只有按戶所有,直接將站宅基地發展權賦予農戶,農民才能切實享有農地發展權。這既符合現代產權的“產權明細”權利屬性要求,也和我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并不矛盾,是一種安分享有的農地產權利益的實現。
其次,宅基地權益分享模式。“基于農村宅基地產權完善的收益共享機制的構建,是當前農村宅基地管理的關鍵。”[4]雖然宅基地發展權直接規定為農民享有,但不意味農戶完全獨享宅基地發展利益。實際上,土地發展權導致的土地應發展而產生的利益,國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向宅基地發展權產生的利益可以一定的稅收。為了保障國家稅收的實現,應實現農村宅基地出賣登記制度,沒有登記的宅基買賣無效。
最后,明確規定法律責任。當農民宅基地發展權受到其他主體非法侵害時,作為所有權人的農戶有權直接要求侵害者承擔賠償或補償責任。
(二)賦予農民宅基地發展權有限流轉權,規范農民宅基地有序流轉
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從農民融入城鎮生活是需要一定的資本代價的。對于那些在原地居住的農民,也有強烈改善生活條件的需求。農民的初始資本就是包括宅基地在內的農村土地以及以上的房屋。農村宅基地及住宅流轉,直接關系到農民財產能否轉化為資產進而轉化為資本,直接影響到農民財產性收益的增加。
賦予農民宅基發展權,由農民自身土地發展權、并享有宅基地發展權的利益。這不僅有助于農民通過行使宅基地發展權獲得相應的權利效益,不僅有助于實現十八大黨提出的“讓人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的實現;農民獲得的資金更有助于夯實其融入城鎮化的基礎,有利于新型城鎮化的實現。然而,農民并非每個個體都是非常理性,個別農民為了眼前利益不理性地隨意實現農村宅基地發展權。當有較為理想的價格行使宅基地發展權而出賣宅基地而后面又陷入生活困境,生存權都可能存在問題的困境出現。因此,農村宅基地流轉“應當放置在當事人權利得到保障、公平公正以及社會穩定的基礎上綜合考量,既不可一味地否決流轉,亦不可完全放開而‘自由’流轉”。[5]筆者認為,農民出賣宅基地必須以兩個基本條件為前提:一是必須有另外相對穩定的居所為前提。這里的相對穩定的居所可以是對居所擁有所有權或雖然沒有所有權但可以預見到的時間范圍內享有穩定的居住權;二是自身社保必須購買。如果滿足這兩個基本條件,農民實現其宅基地發展權,其后面的基本生活應該又基本保障。
(三)構建農村宅基地退出制度,保障農民城鎮化的物質基礎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加快,迫切要求城鎮建設用地需求激增;而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不少農民城鎮務工和居住,農村房屋居住率很低,農村宅基地大量閑置甚至荒蕪。因此,為了解決宅基地城鎮化用地需求和農村宅基地閑置的矛盾,建構農村宅基地退出制度勢在必行。傳統意義的農村宅基地的功能,主要就是保障農民的居住權,“宅基地的主要功能是以物質形式提供農村集體成員的生存居住保障,并以此為基礎實現社會穩定。”[6]隨著農民進城謀求發展,作為農民維持基本居住的社會保障載體的農村宅基地,對于這部分農民的使用價值沒有或者很低。農民作為農村宅基地的權利主體理應享有在獲得合理補償的條件下退出農村宅基地的權利。建構農村宅基地退出制度意義重大。一方面,在獲得農村宅基地合理補償退出后,農民獲得相應的資金從而夯實其在城鎮發展生活的資本,其農村宅基地發展權得以實現。另一方面,農村宅基地退出后能在流轉中實現其價值,滿足新型城鎮化對土地的需求,達到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構建農村宅基地退出制度,必須加強相關配套制度或措施:
首先,農村宅基退出必須構建明細的土地產權為前提。產權明晰不僅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促進產權人有效利用資源,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我國農村土地一直以來存在產權主體虛置、權能殘缺現象,必須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宅基地所有權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實行農民按份共有。在此基礎上進行產權登記,“國家認證的、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權證,使農村宅基地流轉程序合法化、正規化。”[7]如此規定,在不違背我國農村土地公有制大背景下為農民個體實現農村宅基地發展權奠定所有權基礎。
其次,明確補償程序和補償標準,完善退出激勵機制。農民退出宅基地,不僅以為著轉讓其宅基地使用權,也意味著轉讓宅基地發展權。對于自愿退出農村宅基地在審查其融入城鎮的生存能力和退出后的社會保障狀況的基礎上,給與合理的退出補償。農村宅基地退出補償應根據該宅基地所處的位置,在不低于當地土地出讓價的基礎上予以確定。各地應明確農村宅基地收回的補償標準和補償程序。對于那些有退出意向又對在城鎮生活缺乏底氣不想完全失去宅基地的農戶,可以采取頒發地權期票、“留權不留底”的靈活處理方式,讓這些農戶在一定期限內保留其作為農民身份的宅基地申請權利。
最后,建立農民住房保障體系,確保農民退出無后顧之憂。
為了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吸引更多的農民退出土地融入城鎮生活。政府應在相關的城鎮特別是鎮這一層面建造農民城鎮化保障住房。農民以出賣宅基地使用權和發展權為代價,購買鎮府修建的保障房。新型城鎮化中農民住房保障工程,一方面,農民能享受城鎮生活的便捷,共享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成果;另一方面,農民融入城鎮退出農村宅基地后為我國集約化、高效率的現代農業發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