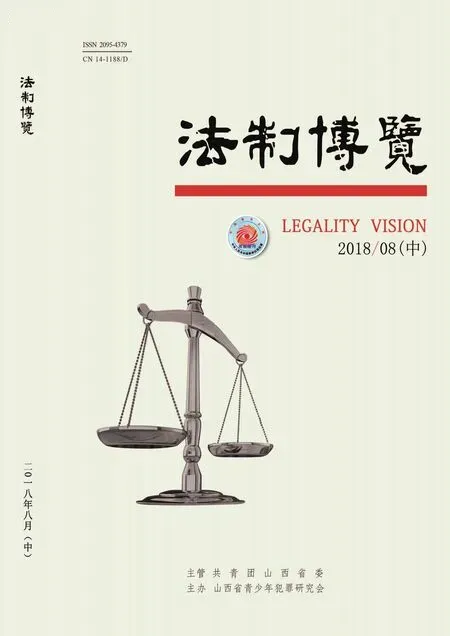論新時代我國信訪制度運行的新特點
黃 丹
中共大連市委黨校,遼寧 大連 116000
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戰略判斷,新時代更加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國的信訪制度運行也呈現出新特點。
一、信訪主體多元化
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急速變化,社會結構出現分化、社會群體出現分化,涌現出很多新興利益群體。如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利益主體更加多元。多元化的利益群體在市場經濟內在動力機制作用之下,也即個人和經濟實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一內在動力驅動之下,相互之間具有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對立沖突的利益追求,帶來以利益訴求為主要表達的信訪主體多元化。
現實中,不同社會階層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明顯不同。特別是那些占人口數量較多、占有社會資源又較少的弱勢群體,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同,當下的信訪主體已不再局限于工人和農民,逐漸擴展到一些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心理極度脆弱、有相對被剝奪感和不平衡感的群體。他們由于缺乏體制內的利益表達渠道和相應的訴求表達能力,難以對關系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有效影響,也不愿通過訴訟、仲裁、復議等權利救濟手段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帶來大量信訪。
二、多重利益訴求疊加
隨著我國的改革向縱深推進,最初的增益型改革已轉為利益結構調整型改革。對全體人民來說,利益是極其重要的事情,如果利益問題解決不好、利益訴求無法解決,就容易引發社會矛盾。
物質需要是最低層次的需求,解決的是生存和溫飽問題,但最低層次的供給已無法滿足新時代人民需求的層次與內容。人民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政治文明的需要或綜合性的需要就提到日程上來,比如法治文明狀態下的人權問題、尊嚴問題、人的全面發展問題,這些既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信訪群眾的訴求表達。因此,一方面,我國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供給無法滿足需求,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新時代群眾的信訪訴求已從單一的物質利益訴求轉向多重利益訴求相疊加。
三、訴求表達以平和方式為主
2009年前后,我國暴力性群體性事件數量達到高點。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地方官群矛盾、警民矛盾激烈,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以一種高破壞的形式爆發出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處理信訪能力較弱,事前沒有制定切實可行的應急預案,事中沒有處理對策,要么手足無措、要么強力打壓或者久拖不決,使很多群體訪經過發酵最終釀成打砸搶燒的暴力性群體性事件,事后也沒有及時調查群眾訴求并保障權益,致使事件出現反彈。
隨著我國和諧社會建設和法治政府建設的發展,以及改善民生和社會保障政策不斷完善,我國百姓維權逐漸走向理性,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近幾年發生的群體訪來看,信訪群眾多表現出極大限度的克制,多采用平和的訴求表達方式,如集體旅游、集體散步、集體喝茶、集體購物等等。信訪行為方式的轉變一方面體現信訪群眾在為規避政治風險尋求著法律邊界,另一方面也為政府解決民眾訴求提供了緩沖。
四、政府從壓力維穩走向制度維穩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在維穩方面出現了這樣的悖論:政府越是強調維護社會的穩定,就越不愿意接受公民的訴求表達,而公民的訴求表達越受到來自政府的限制甚至是壓制,就越要通過其他渠道(包括體制內與體制外、正常的與極端的等)加以表達,導致社會矛盾更加激烈,這些地方政府就越需要投入更多經費用于維護社會穩定。從實際的效果看,維穩投入的增加不僅沒有給當地帶來社會穩定,相反對社會的穩定帶來更多負面影響。
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地方政府逐漸認識到我國發生的信訪問題多是人民內部矛盾,信訪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依法保護并依法解決百姓提出的合理訴求是政府的一項公共職責。據此認識,地方政府就從壓力維穩走向了制度維穩。
在法治層面,通過對公民的利益表達作出某種制度化的安排,讓不同的社會利益主體,特別是弱勢群體有可能有機會自主表達利益訴求,從而為實現公平正義創造條件,實現公民信訪權利的法治保障。同時在處理信訪過程中,黨員干部的思維方式也逐漸從先行思維轉向法治思維,從以堵為主轉向以疏導為主,從大包大攬轉向分類處理,從滿足物質利益轉向保護公民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