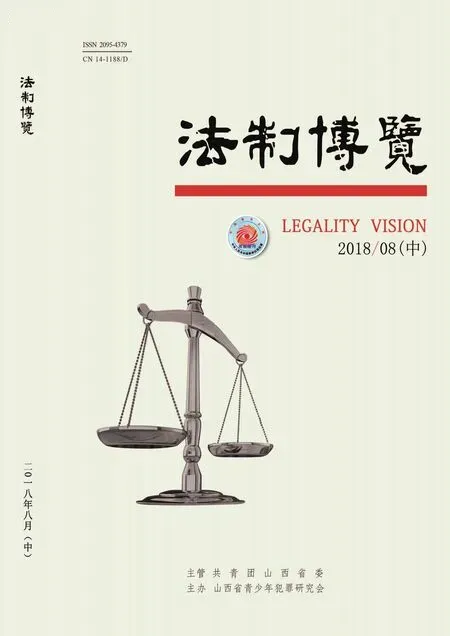認罪認罰制度中審查逮捕若干問題的具體適用
畢 勝 吳俊杰
吉林財經大學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制度是我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要舉措。2014年施行的《速裁程序試點辦法》及2016年六部門頒布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辦法》均反映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我國正在穩(wěn)步的實施。在通常情況下,認罪認罰僅僅只用于審查起訴以及審判等環(huán)節(jié)。然而,在實踐中,我們應當廣泛的延伸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在逮捕審查時也適用相關制度,從而最大的發(fā)揮其功效。
一、公開審查的流程設置
建立健全新型審查逮捕模式,也可以說是在審查批捕之前進行公開審查的相應流程。這樣流程設置的目的在于程序能使控、辯雙方充分表達各自意見,類似于辯論的模式。審查逮捕訴訟化雖然在試行探索階段各地的規(guī)定不一致,但在公開審查的模式下,有一個普遍的共識是不涉及證據(jù)的開示、質證,因為在審查逮捕階段律師并沒有閱卷的權利,試行探索也不能突破法律的既有規(guī)定。那么就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在審查逮捕訴訟化的辯論過程中,偵查機關一方與犯罪嫌疑人一方的爭議焦點必定在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但如果不涉及證據(jù)的開示、質證的話,這樣的辯論是毫無意義的。鑒于上述情況,筆者所在的檢察院在試行審查逮捕訴訟化的過程中,均選取犯罪嫌疑人認罪的案件作為試行的突破口,在犯罪嫌疑人認罪的前提下,雙方圍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社會危險性、是否有逮捕必要進行充分的論證。
二、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具體認定
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員在進行審查逮捕的流程中,要對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進行評估,所謂的社會危險性一般很難有一個確切的指標,我們需要結合犯罪嫌疑人的實際情況具體分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審查逮捕訴訟化的在探討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的問題上存在共通點。根據(jù)《認罪認罰從寬試點辦法》的相關規(guī)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及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是否對其行為認罪認罰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危險性與否的考慮指標。在具體操辦認罪認罰的刑事案件中,辦案人員應當廣泛的聽取被害人、被害人代理人的意見,將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達成相關和解協(xié)議或者積極履行對被害人的損失的義務、是否得到相關人的諒解作為一項量刑的重要參考的指標。
上述對于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以及對于量刑的考慮因素,其實就是審查逮捕階段對于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實務、學理上的分析。在具體實施中,如犯罪嫌疑人有不如實供認或者避實就虛,檢察機關可認定其有逃避偵查等輕微社會危險性。
如犯罪嫌疑人確能供述相關罪行且供述有相應依據(jù),不會導致其他社會危險的,一般應認定為無社會危險性,也就沒有逮捕的必要。
從這個角度來看,認罪認罰從寬的理論其實早已在審查逮捕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只是缺乏一個明確的具有體系性的制度、框架予以規(guī)范。
三、保障律師的合法參與
審查逮捕訴訟化結構性改革,多地實踐不完全一致,但各地試點改革的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均包括了多方參與,這其中就包括了律師方面的參與。最高法、最高檢等六部門在2016年11月出臺了《關于在部分地區(qū)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下稱《辦法》),在《辦法》第5至8條中明確而具體的規(guī)定了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辯護律師參與的原則。刑辯律師在認罪認罰的速裁程序中有著不可缺乏的作用。這無疑與審查逮捕訴訟化結構性改革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審查逮捕訴訟化結構性改革也明確規(guī)定了包括律師在內的訴訟參與人的參與,因此,若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于該階段,便具有實現(xiàn)保障律師參與的先天優(yōu)勢。
盡管目前的實踐當中并沒有法律法規(guī)明確地將審查逮捕階段納入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范圍當中,現(xiàn)實中的審查逮捕工作仍然更多地依據(jù)審查逮捕的既有的法律法規(guī)、辦法。但是,在審查起訴環(huán)節(jié)中適用認罪認罰制度,有可能且有極大可能導致被告人最終被從輕、減輕,而如果在此之前的逮捕階段仍僅僅依照審查逮捕的具體法律法規(guī)、辦法,不利于保障被告的合法權益,這嚴重違反刑法罪刑相適用的原則以及我國寬嚴相濟的政策。因此,未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發(fā)展方向,應當可以考慮將審查逮捕納入其適用范圍。如果未來的刑事訴訟法能夠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于審查逮捕當中,則一定能使我們整個的刑事訴訟各個流程整體和諧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