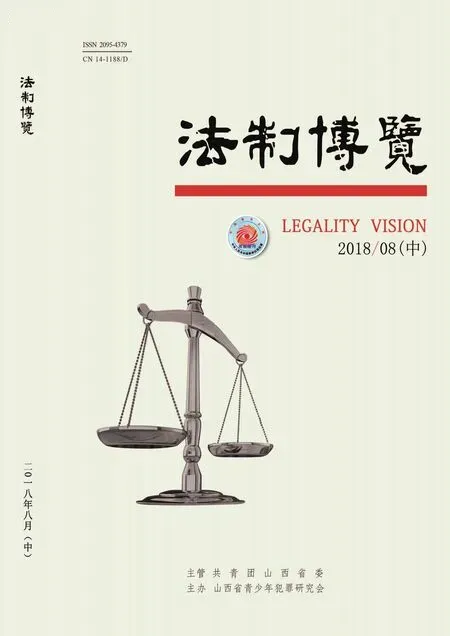老年人非婚同居之財產法律規制
王 軍
吉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103
哲學家黑格爾曾說過“存在即合理”。這就說明老年人非婚同居現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英國人口學家提出了非婚同居發展的四階段理論,而中國正處于此理論的第二個階段。立法服務于社會,就應當跟上社會發展變化的步伐,保護同居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一、法學界關于老年人非婚同居的理論學說
(一)非婚同居財產制
有學者立足于中國的國情,提出了“準婚姻制度”,法律有條件地承認具備某些客觀要件的非婚同居關系的效力,在處理同居雙方所產生的財產糾紛問題時,可以參照登記婚姻的處理辦法予以法律保護。但是有學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這種制度是對非婚同居現象的縱容,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婚姻登記的法律權威,不適用于當前中國社會。
(二)同居財產協議制度
中國司法實踐中主要是依據民法中關于“一般合伙財產”的相關制度來確定同居雙方的財產歸屬問題。但是這種方式過于模糊,因為同居關系不同于合伙公司,同居關系中的情感付出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在財產歸屬問題上,可以借鑒法國的同居協議的模式,同居雙方當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訂立同居協議,事先約定財產歸屬。在同居關系解除時,有事先協議約定的按照約定分割財產,此協議對同居雙方當事人都具有法律約束力。
(三)公平補償制度
美國司法判例中,依據“婚姻生活現實性原則”,法院可以根據公平補償原則,對老年人非婚同居中處于弱勢一方的合法權益加以保護。特別是同居關系中的女性,法律通常情況下不承認其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并且該價值也不可具體量化,鑒于此,老年人在同居期間可以做出特別約定或者在遺囑中特別注明,同居期間承擔較多家務的一方或者對另一半照顧較多的一方,在財產分割是可以適當予以照顧。建議老年人非婚同居期間,簽訂相關的附條件的遺贈扶養協議,在條件成就時贈與給另一方事先約定財產,作為對其在同居期間所付出勞動與心血的經濟補償。如:如果一方在另一方病弱時予以精心照顧和陪伴,則付出多的一方可以獲得某些物質補償等。
二、我國老年人非婚同居財產規制構想
(一)同居財產歸屬問題
老年人非婚同居主要是為避免關系解除時所面臨的財產分割的矛盾,這種方式既不會使自己財產受到
損失也不會間接地損害到子女的相關財產性利益。所以,法院在審判老年人非婚同居財產歸屬的過程中,應當慎重考慮到老年人的這些顧慮。對此,可以借鑒法國的“同居協議制度”,財產分割以約定為主。在沒有事先約定的情況下,主要依據分別財產制度,對于在同居存續期間當事人共同出資購買的且共同使用的物件或者難以判定財產歸屬的物件,通常情況下按照共同共有原則分配財產,必要情況下,可以由法官適用自由裁量權,適當使用婚姻財產制度作為補充。
(二)同居關系自然解除時財產分配問題
老年人不選擇登記結婚另一個原因是子女與老人的伴侶在遺產繼承方面的矛盾,因為婚姻不僅僅是兩個老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大家族的結合,在結合關系中必然會發生財產上的糾葛。
老年人非婚同居期間,若一方老人去世,從法律角度講,另一方不具有法定繼承的資格。但是本著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若另一方在生活上確實困難且在同居期間給予了被繼承人一定形式的照顧,則可以適當申請給予在世一方必要的經濟幫助,對于此,為保護同居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法律應當明文規定出來,這樣才能在實際案例審判中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據。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繼承法對于此種情況設立了一個救濟途徑,即法律雖然沒有承認非婚同居關系中雙方的相互繼承資格,但是其規定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歸在世一方的財產,受法律保護,這樣在世一方就能以繼承人以外的身份獲得被繼承人的部分的遺產。
三、結語
非婚同居屬于公民私生活的范疇,大部分情況下是由道德所調整。公權力的介入需要考慮均衡公平正義原則和保護公民的意思自治兩個方面。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應當適用于社會的發展,合理解決現實中出現的各種糾紛。現行法律雖然不承認非婚同居關系的合法效力,但是不能否認當事人在同居期間所產生的合法財產的正當性。法律應當對同居期間財產糾紛予以全面規制,保護同居雙方的合法利益,合理高效地適用司法實踐,避免社會矛盾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