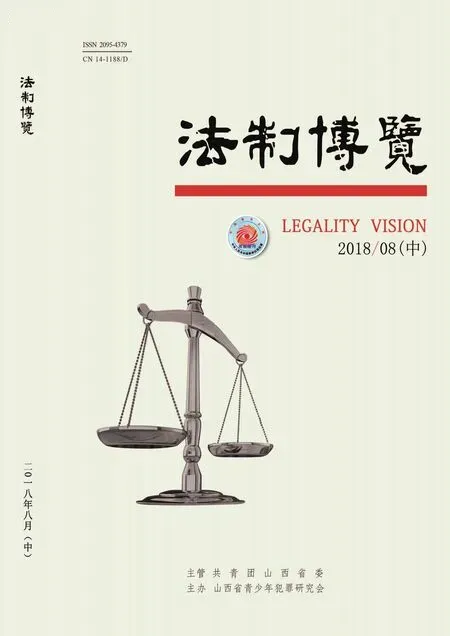法理學中的身份焦慮相關研究
段美先
安徽工程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受法學家梅因觀點的影響,法制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要取消特權身份,事實上隨著國家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完善,特權身份必然會隨之減少,但是目前“身份”問題依舊是法理工作關注的主要重點。在過去數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中國法理學的思想依然受西方傳統法理學的影響,導致中國法治和法治思維核心思想上的矛盾。通過調查分析發現目前中國法理學學人存在一定的身份焦慮現象。
一、“身份”焦慮的主要表現
中國法理學研究人員身份焦慮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法理學者的多重身份特征。
(一)政治上的焦慮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法理學者對階級身份的重視程度在逐漸降低,同時也逐漸接受了現階段社會上的法律價值觀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法理學者研究的主要內容由體制自由逐漸轉向了權力的濫用,各種抱怨的聲音也逐漸在增加。法理學者渴望能夠在法制環境中實現身份的真正自由,然而法治工作本身具有兩面性,因此在賦予一定身份自由的同時也會對身份進行限制。法律不能夠簡單地定義為契約,因此法治理想必須要與調動身份的積極性有效結合在一起。目前人民的領導地位已經在政治學中得到了肯定,但是這一概念在法律上卻很難定義,單純從法律的概念上很難對人民的積極性進行調動。法律上賦予公民一定的權利同樣也規定了公民的義務。
(二)“國別”身份的困惑
目前中國法律學建設基本上是借鑒西方的法理觀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歷史以及實際社會的發展連接不夠緊密,缺乏足夠的主觀性創新。這樣的問題導致中國法理學的許多觀點與當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存在很多不符的現象。盡管法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不受國別的影響,但是研究人員的身份涉及到相關研究工作被認可的程度,但是現階段中國法理學的研究工作不是將法理原理與中國社會實際進行結合,而是希望通過現成的理論原理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
(三)學科獨立問題上的矛盾
目前,很多高校的法學教育工作都面臨著理論貧困以及實踐貧困的二元困境,教育工作大部分都是通過對西方法律原理的分析來對中國的法律體系進行判斷。法學概念中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并沒有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得到充分的重視。法理學科的建設上缺乏獨立性。改革開放以來法理學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立足于不同觀點對法理學內容進行豐富,將不同流派的思想觀點與中國固有思維進行整合,將相互之間矛盾的觀點結合在一起,導致中國法理學科缺乏學科獨立性。
二、如何對“身份”焦慮進行矯正
中國的法理學科要想有突破性的發展,就必須要打破傳統的實質主義思想,必須要改變目前權利為本的觀點,加快中國法治化建設的進程。
(一)構建中國法制建設的話語系統
中國法理學的發展是建立在大國法哲學的基礎之上,因此必須要有法律話語權作為支撐。身份地位本身受歷史因素的影響,需要通過相應的歷史任務來實現身份地位的強化。法治環境作為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軟環境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夠僅僅依賴傳統的權力對其進行約束發展。法制建設的發展同時也是國家管理模式的不斷改變,是對國家治理工具的完善。法理學建設的核心任務應當是以法治絲線為基礎構建理論體系。
(二)重視發展中國法理學實用功能
法學的實用性是通過法律手段表現的,必須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針對法理學的劃分不能采用與哲學一樣的劃分方式否則會導致概念上的混淆。目前很多學者對法理的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晰,這是因為法理學在研究過程中過于重視理論的研究,而忽視其實踐工作。中國法哲學研究工作中強調整體思維模式,將各種矛盾性事物進行整合分析,導致在中國法理界出現一種將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混淆的思維路線。目前中國法理學的系統化建設工作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在法理學的觀點和思路上還有很多模糊的概念,很多理論并沒有進行清晰的界限劃分,對此必須要堅持法律方法論的引導性作用,重視法理學實用化建設,在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的法理思想的引導下實現法律的價值目標,真正實現法理學中規范之理以及法治治理的概念,從而緩解法理學界身份焦慮的現象。
三、結語
綜合上文所述,中國法理學身份焦慮問題主要是受奧斯丁思想的影響,目前在法律思想以及法制方式上還存在很多模糊的情況,對此法理學工作者不僅僅要加強對相關理論的研究和學習,更要將當前社會上的各種規范以及實際情況與法理學的建設和發展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