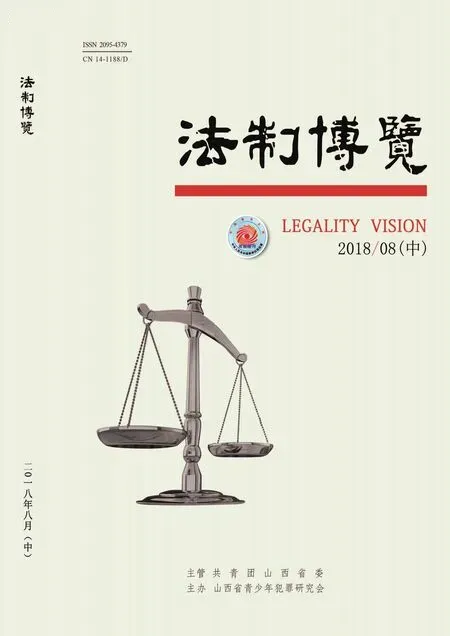簡論中華法系的基本特征
屈夢帆
西華師范大學,四川 南充 637002
中國歷史悠久綿長,中國法制也隨著歷史不斷發展,中華法系就是中國古代法制發展的一個展示,中華法系對當代中國的法治現代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具有諸多值得我們探求的東西,有諸多值得我思考的話題,由于篇幅的關系,我們在此僅就中華法系的特征作以探討。對于中華法系的基本特征,本文以為,應該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以儒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
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國封建時代占據重要的地位。儒學創于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思想由此開始發展。后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同時采取了“焚書坑儒”等措施統一思想鞏固地位,儒學發展遭到嚴重阻礙。到了漢代,為了維護統治,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至此儒學才正式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以儒家思想為基礎逐步形成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維護封建倫理,以家族為本位的倫理法具有重要地位。這是由于中國長期尊崇儒學的原因導致。秦漢以來制定的法典都明確地對家族內部權利義務進行了規定,而且一家一族制定的規則不僅限于對家族內部人員有巨大的約束限制力,而且得到國家的支持,國家承認家規、族法的效力。宗法的倫理精神滲透并影響著社會,特別在封建社會后期,宗族倫理法起著十分突出的政治作用。
二、“出禮入刑”,禮刑結合
西周時期就提出了“出禮入刑”,即是將禮與刑(手段)結合起來共同治理國家,由此開創了世界上獨有的治國模式。儒家為正統思想,特別注重一個“禮”字。但任何社會都會有不遵守“禮”,有不遵守規矩的言行,因此相應的制裁方法便應需而生,統治者將在戰爭場上運用的殺戮殘忍手段,有選擇地演變為刑罰手段,用來懲罰逾禮之人,即所謂的“出禮入刑”(言行超出規范的要求,就會被刑罰懲罰)。所謂的“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原則主要表現在古代在處理民事案件以及輕微刑事案件的時候,雖“禮”處在主要地位,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刑”也是治理的好“幫手”。而禮刑并用,各朝并非單一運用儒家思想,在用道德管理起不到應有作用時,可以采用刑罰,也即是可以采取法家的一些手段進行輔助。其實無論是出禮入刑、德主刑輔還是禮刑并用,強調的都是一個意思,即禮為主,刑為輔,只是由于的時代不同,稱呼不同罷了。
“出禮入刑”法律觀念也給國人的法律思維帶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法律在西方國家人們心中是與公平正義、自由權利相互關聯。而中國從古至今,一談及法
律,首先聯想到的就是“刑”、“罰”,認為法就是殘酷殘忍的。清乾隆年間曾有一言盛傳“法為盛世所不可缺,亦為盛世所不尚”。這種觀念曾長久地影響著國人對法律的認知和評價。
三、行政司法合一,皇權至上
由于古代中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統治,大權集中于君主一人,皇帝始終是立法與司法的核心。可以說,法律是根據皇帝的意志制定的。由此可見,帝王凌駕在法律之上,作為法外之人,他不受法律約束。同時,皇帝也是最大的審判官,雖然有著像“大理寺”、“御史臺”一樣的司法機關,但形同虛設。司法權始終掌握在貴族以及君王的手中。在地方上表現為行政機關兼管司法,各級行政長官直接組織地方審判,司法與行政合二為一。
對比來看,在西方中世紀相當長時間里,各級領主都享有獨立的立法權、司法權,西方也有限制國王權力的法典,比如英國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它成了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限制封建君主權力的法律,也是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法律基石。《大憲章》第39條明確規定了:“未經合法裁判,對任何自由人不得施行逮捕、監禁、沒收財產、放逐出境等處分”,這說明國王若要進行審判,只能根據法律來進行。這一條約束了英王的統治權。為《權利法案》的制定提供了一個模板。中華法系與西方法律最突出的區別就體現在這里,一個是君主享有最高權力;一個是限制了君主的權力,立法權與司法權屬于君主以外的人。
四、重刑輕民
中華法系一直具有重刑輕民的特征,即重視刑法的保護功能,著重運用刑法及其處罰功能,刑在法律體系中也占據著主要地位;相反卻輕視民法的調整功能。在法典制定方面,歷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都采取的是“刑法為主,諸法混合”的結構形式,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在法律的適用方面,也是注重刑訴而輕民訴,刑訴程序比民訴更加清晰完整,甚至古代經常性地會用刑事處罰來解決民事的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