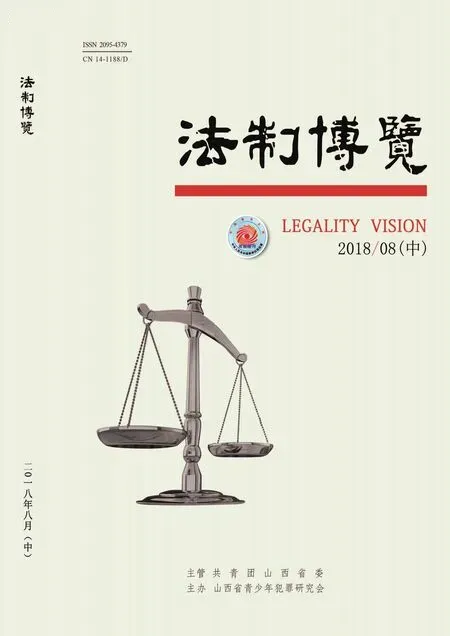被遺忘權中國本土化探究
王靜陽
沈陽工業大學文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870
一、被遺忘權國內法現狀綜述
近年來,我國網絡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與此相對應的保護網絡信息主體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也不斷修訂完善。在部分法條中逐漸出現了與被遺忘權相似的權利規定。網絡侵權責任在《侵權責任法》第36條予以明確,即網絡用戶在受到網絡侵權時可以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刪除、屏蔽、斷開鏈接。這種法律上的刪除權利類似于國外的被遺忘權,有學者認為是被遺忘權在中國的一種法律規范雛形。
收集、加工、轉移和刪除個人信息的具體法律,明確規定在2011年工信部的《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中,其中明確了個人在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可以刪除其認為不再可用的信息。個人要求網絡服務商刪除個人信息的權利,在2012年12月28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度明確通過,規定于《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第八條。以上被學術界普遍認為,已經奠定了中國遺忘權初步發展的基礎。
二、被遺忘權相關制度構建
互聯網記憶隨著網絡技術在全球的普及和應用日漸成為常態,所以,如何合理保障被遺忘權成為全球各國人民所關注的法律熱點之一。在目前已具備被遺忘權相應法律雛形的基礎上,如何將被遺忘權與中國國情具體結合,解決被遺忘權中國化的系列問題,對積極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及創造安全的網絡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概念界定
被遺忘權屬于舶來的法律名詞,對應中國的法律規定,應囊括在個人信息權保護的概念之中。其權利本質與個人信息權本質相同,其法律上的主要權利內容在于刪除,對象是對信息主體不利的網絡信息。有學者認為我國不應沿用被遺忘權這種法律稱謂,而應當重新將其定義為個人信息權。歐盟法律中關于被遺忘權在《一般數據保護條例》中表述為“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我國將其中文翻譯為“被遺忘權”也有失偏頗,并不能涵蓋其英文定義的全部內容。被遺忘權從其權利的運行內容看來,主要核心在于刪除,因此筆者認為根據其權利屬性,應當歸屬于個人信息權的范疇。
(二)具體內容
首先,權利主體。針對被遺忘權區分不同的主體,需要從權利行使受到限制的內容來看。不同的主體享有不同的遺忘權。通常情況下,對于一般公民主體,行使被遺忘權不應受到限制,應當是全面而完整的。而公眾人物作為特殊主體,其被遺忘權的行使應受到限縮。公眾人物在行使被遺忘權時同時與公眾知情權、輿論監督權等其他權利進行交叉,因此其享有的被遺忘權是不完整的。
其次,義務主體。全部的個人信息控制者應當都包含在行使被遺忘權的義務主體之內,包括引擎運營商和自媒體等各種信息媒介。在當前的網絡時代,個人信息在大數據背景下被永久留存,對個人而言造成了種種信息泄露的隱患。對自身信息享有的“被遺忘權”,相對應就成為網絡服務者和個人信息控制者所必須履行的一項義務,即根據權利主體的要求應用技術手段予以刪除相應信息的義務,保障權利主體“被遺忘”權的實現。
最后,適用范圍。對被遺忘權的范圍界定,學術界一般限定在能夠對應具體信息主體身份的特定信息。其主要原則就是,信息主體對屬于自己的信息資料具有相應的公開、保留或刪除的決定權,與該信息對信息主體所造成的影響沒有直接關系。只要在遵循私法自治原則的情況,信息主體對于與自身相關的信息,無論其是否會對自身造成不良影響,都有刪除的權利。但這種私法上的權利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權利,其同樣受到言論自由權、公眾知情權、科學研究權等相應權利的干涉和制約。
三、被遺忘權的保護路徑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定和出臺受到眾多國內法學家的呼吁,有利于獨立地、合法地、高效地保護個人信息,有利于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私權制度,從而實現被遺忘權的中國化。收錄、使用、保存和管理個人信息需要通過法律規定予以明確和規制,同時也亟需建立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運行機制,這也是被遺忘權在中國化進程中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
在《保護自動化處理個人資料公約》中,歐盟國家第一次提出建立個人信息監督機關。我國可以在歐盟規定的基礎進行參考借鑒,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個人信息保護機關,通過對政府部門、公共主體和私營組織等的信息使用上進行介入和管理,使個人信息保護在公權力保護上也得到體現,既充分保障了全社會的個人信息自由,又促進信息使用的合法利用和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