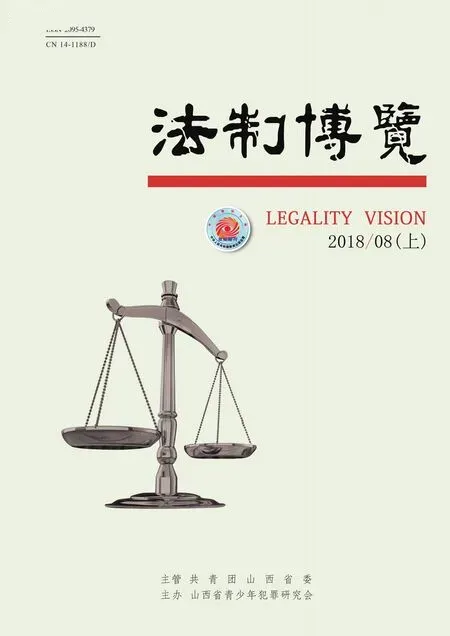法律與自由-刑法視角下的社會秩序與人性
周 航
吉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從社會契約論出發,國家立法來源于公眾對自由的要求,共同締結神圣的契約,保障共同生活。那么是否有人想過,在被法律保護的普遍自由之外,是什么?
一、自由與法,相背而行
似乎有些人注定游離于社會之外,這句話并非嘲諷。
一般觀點認為人性本善,違法者總是因為生活軌跡的偏移才走上歪路,與法律對抗。最后或僥幸得逃,或深陷囹唔。我們對行為標準的判斷也一般分為兩層,上層是符合普遍社會價值觀的道德判斷,底層是符合社會最低容忍度的法律判斷。
為什么總有人從不顧道德批判,也不怕法律制裁?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自由”。
犯罪者中有些人通過教育與勸導能夠回歸社會生活,有些人卻因種種原因從無悔恨,累累重犯。在累犯的原因中,法律意識淡薄、監所環境惡劣、有前科的生活障礙被經常提及,可是論起如何解決,需要投入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卻限制了對犯罪者的改造程度。其實可以理解,市政資源對正常居民和社區環境尚有缺疏,如何指望對犯罪分子施以再生之恩惠?
在刑法規制的領域里,專家學者、一線干警、檢察官法官經常需要探究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犯罪場景,以便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主觀惡性等情節進行評估,依法施以公正的裁判。但促成人轉變的通常都是一個個瞬間、一個個場景的疊加。想追求無限的客觀事實,正應《中庸》所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又怎么去把握每一個人背后的漫漫心路?
人們追求安定的社會,希望社會有如桃源,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當新聞中出現了取人錢財的竊賊,奪人性命的強盜,巧取豪奪的貪官,不免滿面赤紅,憤慨激昂。在保護個人財產時,每個人都渴望只付出最小的生活成本,卻絕難考慮萬千需求疊加時,產生的龐大社會成本以及必然出現的利益沖突。
二、社會秩序,無形的手
石頭能組成社會嗎?
每個人都知道不可能,靜態的石頭無論在哪兒擺成了什么樣子,對石頭本身都沒有任何意義。那么人的社會對石頭有什么意義嗎?當然也沒有意義。對整個世界,整個宇宙呢?想來也是沒有意義的吧。因此說,社會只對人有意義,它是人與人組成的秩序,社會只為了人存在。
但是人,并不一定都能融于社會。他們因為種種原因,比如認知能力障礙、精神或神經疾病、身體殘疾被社會拋棄于角落,與社會的交互少的可憐,與社會的普遍交流范式格格不入。同樣的問題也多多少少發生在不同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的人群身上,發生在不同家庭出身、社會階層的人群之間。雖然所有人互相影響,共同組成了社會,但這并不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確定又純粹、可觀察也可預測,讓每個人都可以毫無壓力的生活在其中。否則社會就成了一塊堅固的鐵板,堅實、規整、無趣。鐵板可不會自己變形,它將永遠是一塊鐵板,與石頭一樣毫無意義,直到被同樣毫無意義的自然規則碾碎。如果人類社會變成了一塊鐵板,也就意味著它離滅亡不遠了。
現在我們應該可以直視人類的差異了,沒有兩個人擁有一樣的成長軌跡,這是毫無疑問的。人生來兼具秩序與混沌的本能,這是進化給予我們的禮物,但是混沌的一面卻屢屢在社會演化中扮演了消極的角色,比如暴躁、嫉妒、貪婪、憤怒等所謂的七宗罪,這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也是必須存在的差異。我們必須正視,這些混沌的人性自人而始,而社會卻形成在后。也必須承認,差異是保證社會活力的必需品,即使它可能使我們忍受痛苦。
三、人性之光,有形之法
回到文頭的問題,自由之外是什么?當然是另一種“自由”。向往此種“自由”的個體可能因種種經歷不擇手段貪戀錢財,可能傾向暴力攻擊他人。對于這些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個體,我們想令他們一勞永逸的消失,可社會秩序又要求我們正視個體之間的差異,差異永遠存在,不能抹除。這個矛盾就是為什么法律必須存在,又確實存在的原因:給予從來都不會統一的社會價值取向一個中間值,以平衡社會需求,保證社會的變化,防止過度的同質化。換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說法:保和諧、促發展。
所以,我們所設計的未來的法律(或法規、規章等一切社會規則和規范),也應該給人性留有足夠的空間。任何秩序內只有充分考慮和容忍差異,才能給予秩序以變化的能力,給予秩序足夠的生命力。
思慮再三,我們是否應把投向不道德、違法、犯罪行為的目光盡量變得更理性一些?他們只是與我們不同的人做出的事,僅此而已。對他們可以施以正義的裁決,但不應并抱以先天的輕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