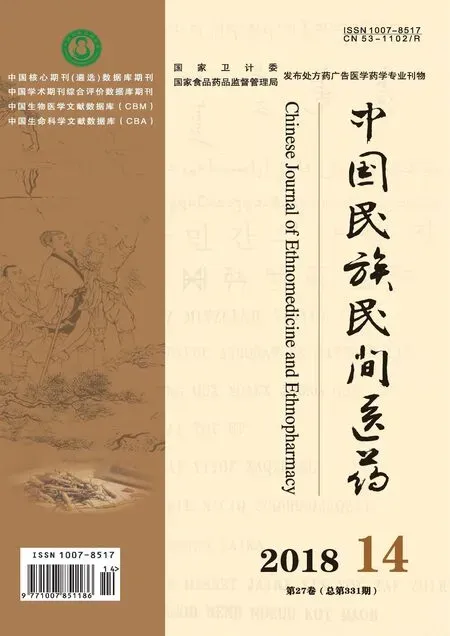東垣灸法淺析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355;2.青島市海慈醫療集團,山東 青島 266000
李東垣師從張潔古,為金元四大家之一,重視脾胃對人身體的作用,強調“脾胃內傷,百病由生”而開脾胃理論之先河。后事醫家多繼承其方藥方面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但卻忽略了東垣在針灸領域的貢獻。明代高武于其所著的《針灸聚英》中,采擷李東垣關于針刺的內容,單編一節,名曰“東垣針法”。后楊繼洲于《針灸大成》轉載了“東垣針法”,自此東垣的針法引起后世重視。雖 “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然,東垣灸法未被詳備整理,實屬遺憾,現淺述其灸法。
1 選穴精妙
東垣雖以內治聞名,但他將組合方藥的精妙法則運用在外治用穴上,選穴突出“脾胃學說”,臨床辨證思維精巧,給灸法的選穴和應用提供新思路。
1.1 “補土”取穴 東垣的治療帶有“補土派”的特色,他認為“清濁之氣,皆從脾出”,“脾胃內傷,百病叢生”。脾胃同居中焦,主司升清降濁,若脾胃功能失常,清氣不升,濁氣不降,則氣化失度而百病生。灸法能夠溫經通絡、扶正固元、溫補脾胃,使陽氣升發而陰火下潛。《脾胃論卷上·脾胃虛實傳變論》[1]中提及“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受損令元氣不足,東垣在補益脾胃的同時亦重視元氣的盛衰,選穴多用足三里、氣海、血海、中脘等穴。《醫學發明卷四·濁氣在上則生月真脹·木香順氣湯》[1]道:“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又以前藥助之,使濁陰之氣,自此而降矣”,體現以胃氣為本的灸療思路。《內外傷辨惑論卷下·說形氣有余不足當補當瀉之理》[1]曰:“若病人形氣不足,病來潮作之時,病氣亦不足,此乃陰陽俱不足也……不灸弗已,臍下一寸五分氣海穴是也。”氣海穴為諸氣之海,灸之可振奮元氣,補下焦陽虛,有益氣助陽之功效,故對于元氣虧虛、脾虛諸證,以灸法補之[2]。
1.2 依證取穴 針灸治療是運用“四診”診察病情,以經絡辨證為特色,結合多元辨證方法,辨證論治,依方施術,以治療疾病的方法[3]。灸法為針灸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施治前固然應辯證分析。東垣在臨床上脈證結合長于分析,《活法機要·心痛證》[1]曰:“脈浮大而洪,當灸太溪及昆侖,謂表里具瀉之。”此處根據脈象而決定采用灸法瀉相表里的足少陰腎經于足太陽膀胱經之氣,是去上沖的少陰、厥陰之氣之意。《蘭室秘藏卷中· 婦人門·經漏不止有三論·涼血地黃湯》[1]中亦提到治療腎水陰虛的婦人血崩,服用涼血地黃湯的同時,加以在足太陰脾經血海二穴處灸三壯,以“治女子漏下惡血,月事不調,逆氣腹脹”。若出現“膝如錐,不得屈伸……小便黃如蠱,女子如妊身。”則加灸足少陰腎經陰谷二穴二壯。在同一證型采用湯劑治療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癥狀表現,選灸不同的穴位。
2 灸量靈活
東垣在灸量的選擇上靈活多變,但多使用較溫和的小灸量。宋朝之前興用化膿灸,治療過程較為痛苦,容易使患者產生畏懼心理。其后隔物灸等更溫和的灸法發展并流行開來,東垣之弟子羅天益提出“不灸破血肉, 但令當脈灸, 亦能愈疾[4]。”一反《千金》中“灸不三分, 是謂徒冤”之說,使用“小竹箸頭大”的艾柱減小灸量,在治愈疾病的同時減少化膿灸的燒灼疼痛。東垣及他的流派傳人倡用小灸量的麥粒灸,如“治小兒疳眼, 灸合谷二穴各一壯, 炷如小麥大。”“凡婦人產后氣血俱虛,灸臍下一寸至四寸各百壯,炷如大麥大,元氣自生。”《醫宗金鑒》曰:“凡灸諸病,火足氣到,始能求愈。”東垣在針對不同的疾病證候時并不一味采用小灸量治法,《針灸大成·頭不多灸策》記載:“觀東垣灸三里七壯不發,復灸以五壯即發秋夫灸中院九壯不發,而漬以露水,熨以熱履,焫以赤蔥,即萬無不發之理。”楊繼洲雖未詳細記載對應的病情,但可見此為積累灸量的同時,為促進灸瘡的發生而采用熱敷、食用辛辣刺激食物等輔助方法。《東垣試效方·瘡瘍門·瘡瘍治驗》[1]中記載:一瘍醫用“五香連翹”治項疽不效,已“有束手待斃之悔”,憂恐間,轉求于東垣[5]。東垣曰:“膏粱之變,不當投五香,五香已無及,且疽已八日,當先用火攻之策,然后用藥。”“午后,以大艾炷如兩核許者攻之,至百壯,乃痛覺,次為處方。”六、七日后,“瘡痛全失去,灸瘢膿出,尋作痂”。這種“用火攻之策”,并且取用大艾炷、上百壯的灸法,灸量之大非一般醫者敢為可為。但只有如此,方能治愈惡瘡頑重之疾,使“瘡痛全失去”。
3 灸藥并用
孫思邈云:“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針灸而不藥,藥不針灸,尤非良醫。”東垣雖未提綱挈領地指出灸藥并用,但在其著作中多處可見以灸法配合藥物治療的記載。《蘭室秘藏·頭痛門·頭痛論》提到張元素頭痛,“潔古曰此厥陰、太陰合病,名曰風痰,以《局方》玉壺丸治之,更灸俠溪穴即愈。”服用玉壺丸熄風化痰的同時,灸足少陽膽經的滎穴俠溪,振奮膽之陽氣,以祛風消痰解頭痛[6]。在治療婦科病中,灸藥配合更為密切,《蘭室秘藏卷中·婦人門·經漏不止有三論·升陽除濕湯》中敘述了升陽除濕湯治療女子崩漏,然東垣自謂“此藥乃從權之法”,若想“尤宜究其根源,治其本經,只益脾胃,退心火之亢,乃治其根蒂也”,故而以“足太陰脾經中血海穴二七壯亦已。”溫煦脾胃之氣,達到標本兼治。
4 小結
東垣施灸前在辨病的基礎上進行辨證,今之灸法重辨病甚于辨證,則選穴泥于病證,不能隨證靈活加減,臨床應用時應先“診”后“治”。取穴則只能效其法, 不可泥其穴, 既可多法多穴聯用, 也可變通使用,如補益臟腑之氣獨取募穴,療效不佳時, 可俞募同用。當代物質生活豐富,難免飲食失節,多傷及脾胃,故東垣的“脾胃學說”于今人意義更甚。且灸法操作較針法簡便,可適用于日常保健,以“補脾胃”為中心的灸法可更好的指導今人養生治未病。
東垣灸法同其針藥一樣對后世影響頗深,但不常被醫家提及,一是其灸法散見于著作中,沒有系統地論述,二是世傳重針輕灸之風。而“若要安,三里常不干”,這種家喻戶曉的體現東垣灸補脾胃思想的養生方法,有力地說明東垣對灸法對后世潛移默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