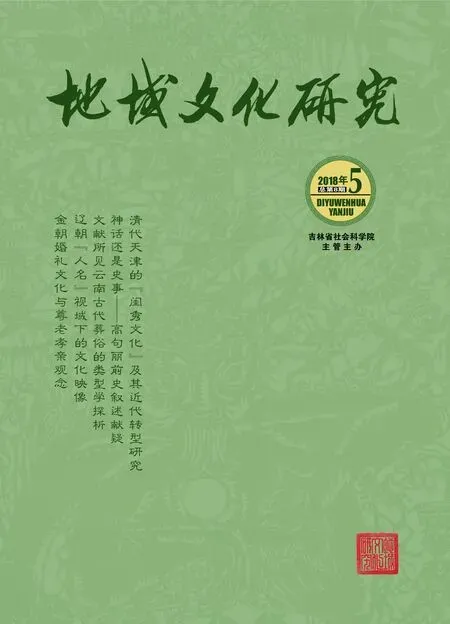熊廷弼反對“以遼守遼”探究
李東梟 吳大昕
“以遼守遼”是明末在遼東問題上一個重要的策略,自薩爾滸戰后即被提出,又被很多人所認同、發揚。①張中政:《袁崇煥軍事思想芻議》,《唐都學刊(西安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孫承宗抗清事略》,《吉林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閻光亮:《孫承宗與遼東防務》,《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季士家:《袁崇煥策略思想探究》,《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1期等文都提到了孫承宗、袁崇煥“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策略,并分析其優點,但并沒有展開,結合現實狀況分析其可行性與實行的狀況。王景哲:《明末20.的“遼人”與“遼軍”》,《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提到了不同時期后金對于遼人的不同政策,分析了不同時期明朝用遼人的可行性,但文中主要是站在后金的視角評價其統治策略的。張士尊:《也論“遼土”與“遼人”——明代遼東邊疆文化結構的多元傾向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第6期則從“遼人”這一群體的構成來探究其政治選擇及明、清政權對于遼人的策略。鮮有文章述及熊廷弼對于“以遼守遼”策略的不同態度,從而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以遼守遼”策略。孫承宗和袁崇煥相繼闡說“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策略,在當時與后世都獲得了不少的認同。孫承宗提出:“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三所、二十七堡之中。以兵以屯,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②(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2,癸亥二月,《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40頁。袁崇煥也提出“南兵脆弱,西兵善逃,莫若用遼人守遼土。”③《明熹宗實錄》卷68,天啟六年二月戊戌,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第3271頁。其要點就在于重點用遼人,亦兵亦農,發展屯田,使得明朝減少從各地調兵調餉的勞苦,避免客兵帶來的不利因素。但作為明末熟諳遼事大臣的熊廷弼,卻是堅決反對這一策略,認為:“乃臣則因是而嘆‘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④(明)熊廷弼:《新兵全伍脫逃疏》,國家圖書館藏《熊經略疏稿》卷2下,第50頁。“主召募者,為‘以遼守遼’之說甚美聽,而遼人余幾?”①(明)熊廷弼:《前經略書牘·與李玄白中丞》,《熊經略書牘》卷1,第2-3頁。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三人都是明末對后金戰爭中的重要人物。三個人在戰略思想上有一貫之處,他們都主張搞好內部建設,穩扎穩打,不求速戰,徐圖恢復。那么為什么會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有這樣大的差異呢?
事實上,雖然三人主持遼東軍事首尾不過十年時間,但遼東戰局瞬息萬變,策略也必然因時而變。在不同的時期,明朝與后金的戰勢不斷變化,“遼人”的現狀也隨之改變,“遼人”是否可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時隨著明朝的財政吃緊,調兵困難,明廷也不得已進行一些調整。另外,對于“遼人”具體所指,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認識。通過分析熊廷弼反對“以遼守遼”策略,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遼人”“遼事”以及明朝政治的諸多問題。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探究,即:明末遼東的殘破與遼民的窘境,遼東豪勢的發展及對朝廷政令的影響,速戰速決與“漸進漸逼”的矛盾。
一、明末遼東的殘破與遼民的窘境
“遼人”一般是指遼東的民眾,而“以遼守遼”的策略則不僅能夠安撫那些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遼東民眾,而且能夠通過征募遼民入伍,減少明朝從各鎮征調軍兵之苦。熊廷弼經略遼東之時,也從利用遼民抵抗后金的方面考量,但其反對“以遼守遼”的態度也與遼東的現實情況密切相關。明末的遼東,因為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已經殘破不堪,其本身應對戰爭的能力下降,且遼民的心理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難以更好地面對戰爭。遼東的殘破并非是遼事爆發以后才有的情況,萬歷中期以后,遼東就呈現出較為衰敗的景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與左翼蒙古的戰爭。嘉靖時期,蒙古俺答興起,成為明朝北邊的大患。但到了隆慶年間,經過高拱、張居正等人的努力,明朝終于與俺答達成“隆慶和議”。但俺答并非蒙古大汗,只是蒙古右翼中的一個分支。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對于蒙古大汗來說是難以容忍的,作為察哈爾正統出身的土蠻汗憤怒地說道:“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②(清)張廷玉等:《明史·張學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854頁。因而以土蠻汗為首的左翼蒙古,在薊遼地區給明朝造成嚴重的邊患,想以此逼迫明朝也與其通貢互市。但其實,明廷的決策就是區別對待,“東制西懷”,激起蒙古左、右翼之間的矛盾,從而坐收漁利。同時,也不能助長土蠻汗“挾賞求貢”的囂張氣焰,另外也有意不全面和解,防止軍隊忘戰、戰斗力下降。在此背景下,薊遼地區的防務壓力最大,尤其遼東,邊境漫長,東西受敵。而在戰略上,還是薊鎮主守,遼東主攻,所謂“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為守,此地以守為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為功,其勢居然也。”③(清)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八,《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56頁。薊鎮用戰斗力強、作戰穩健的戚繼光,保證京師的絕對安全;遼東則用敢打敢拼的李成梁,積極打擊敵人。這種格局更造成了遼東防務壓力的增大。李成梁雖然善戰,但一則遼東實力有限,難以對蒙古各部造成沉重的打擊;二則李成梁也難免失敗,不免因膽怯而不敢拒敵;三則雙方屢屢作戰,難免結仇,尤其搗巢、殺降等行為更會加重仇恨,招來蒙古的報復。萬歷年間,蒙古軍隊時常侵入邊墻,攻陷堡寨,燒殺搶掠,給遼東地區的經濟與社會造成了很大創傷。
然后是“壬辰戰爭”的影響。遼東與朝鮮相鄰,且遼東軍隊善戰,于是“壬辰戰爭”中遼東軍隊成為明朝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壬辰戰爭”對明朝來說,不僅花費巨大,而且遼東的軍力也損失很大。戰爭初期,明朝僅令祖承訓帶領三千人前往朝鮮,結果平壤之戰,“史游擊歿于陣,承訓僅以身免,三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①(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752頁。。祖承訓所率領的三千人都是遼東軍隊,一戰皆沒。碧蹄館之戰,李如松遭到挫敗,而其所率軍隊基本為李氏手下的精銳部隊:“癸巳(1593年)朝鮮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邇,不與他兵分其功。潛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②(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下)補遺卷3,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71頁。這讓當時遼東的李氏集團元氣大傷,也導致其之后軍事上的不作為:“始成梁、如松為將,厚畜健兒,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無復存,而如柏暨諸弟放情酒色,亦無復少年英銳。”③(清)張廷玉等:《明史·李成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6196頁。戰馬數量也急劇下降。據張士尊《明代遼東邊疆研究》一書統計,遼東操馬由隆慶五年(1571)的78,082匹下降到萬歷十九年(1591)的43,000匹,至萬歷二十八年(1599)僅有20,000匹。④張士尊:《明代遼東邊疆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1頁。
還有“高淮亂遼”。萬歷中葉有“三大征”,國力消耗甚大,而萬歷皇帝又索求無度,多方斂財,礦稅監的委派即是其惡政之一。派到遼東的礦稅監以高淮為主,高淮在遼東地區的行為被稱為“窮兇極橫,罄竹難書”⑤(明)董其昌輯,楊時喬等疏:《神廟留中奏琉匯要》(六)兵部卷6,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3頁。,李化龍稱:“臣嘗備員遼撫,故今諫問遼事,其人泣而對曰:‘遼不可為矣。先遼陽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數千之產,為淮搜索已盡,非死而徙,非徙而貧,無一家如故矣。’又有泣者曰:‘遼軍已數年不得錢糧,凡給散錢糧,為將領扣去,軍士分厘皆不得沾矣。’”⑥(明)董其昌輯,李化龍疏:《神廟留中奏疏匯要》(五)兵部卷1,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0-281頁。高淮除了大肆搜刮錢財之外,還插手遼東軍政,迫害遼東吏民,乃至激起民變,嚴重動搖了明朝在遼東地區的統治秩序。遼東不僅受到經濟上的壓榨,而且民眾也因此離心。熊廷弼巡按遼東,正是“高淮亂遼”剛剛結束的時候,據兵備道閻鳴泰向他的報告:
職以去歲季冬受事渡河,四望樹木蕭疏,垣檐空圮,荒涼冷落,不堪舉首。旋見父老無數大呼號泣,曰:“此河那壁即屬虜巢,三尺童子匍匐可踰。我輩冬夏操戈,晝夜防御,焦肌裂膚,萬苦千辛,疲敝已極。近年被高監剝削,家破人亡,剜心摘膽,自恨生不如死。又念君門萬里,控訴無門,死便死耳,誰其知之?與其死,不如逃。”⑦(明)熊廷弼:《請免商稅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9冊《按遼疏稿》卷2,第413頁。
熊廷弼查訪民情,也聽到了“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對頭”這一類的聲音⑧(明)熊廷弼:《請免商稅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9冊《按遼疏稿》卷2,第411頁。。可見高淮在遼東的行為大失民心,勢必造成民眾的不安定。
另外還有邊鎮普遍會有的弊政。如馬政:“自馬價侵費,貨物濫惡,買馬各役又皆圖賤營利,專買一等老病瘦弱之物,以希搪塞,而精壯臕肥者,牽至市口,反皆退回而不受”⑨(明)熊廷弼:《查參馬價疏》,《按遼疏稿》卷1,第361頁。。如羨余問題:“所患苦者,獨無軍耳,未有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為留餉之地者;獨無餉耳,未有有餉而故扣留作羨,不為補軍之用者,有之,自遼鎮餉司始。”①(明)熊廷弼:《除報羨余疏》,《按遼疏稿》卷1,第362頁。如將出私門問題:“照得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后改為十營,委用閑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為私役。”②(明)熊廷弼:《請并營伍疏》,《按遼疏稿》卷1,第374頁。尤其屯田的敗壞,使遼東在面對災荒時幾乎無以自存。熊廷弼指出:“臣惟遼鎮之窮,至今日而極矣。自屯田法壞,歲收子粒虧及國初額數大半,所在軍儲倉空,虛倒廢鞠,為犬豕之場,而各衛預備倉并無收貯贖谷一粒備賑。即孤老數年,不得關領一粒養濟,何論救荒?”③(明)熊廷弼:《常平倉積谷疏》,《按遼疏稿》卷5,第582頁。這都是其自身所親歷的。④這些弊政是明代中后期九邊的通病,相關研究已經很多,暫舉一些整體概括的研究:如馬政的衰敗,可見吳仁安《明代馬政制度述論》,《西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李莉《明代馬政》,《明史論文集——第六屆國際明史學術討論會》,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何平立《略論明代馬政衰敗及對國防影響》,《軍事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衛所制與屯田的衰落、軍官腐敗、勢要占役,可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馬自《明代兵制初探(下)》,《東疆學刊》1986年第1期;馬自樹《明代軍隊衰弱的內在因素》,《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彭勇《明代衛所制流變論略》,《民族史研究》2007年等。
遼東是九邊之首,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從地理形勢來說,遼東本身又十分危險。明中后期,遼東地區西邊、北邊面對左翼蒙古諸部(此時朵顏三衛已經被左翼蒙古察哈爾、喀爾喀所吞并,雖然名義上還說是“朵顏三衛”,實際上是左翼蒙古各部),東北邊面對海西、建州女真,南面是大海,不與華北直接相連,而且海上也有海防的壓力,尤其壬辰戰爭及之后一段時期。熊廷弼指出:“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余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首以百計,控弦數十萬……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界遼為兩段,虜又插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⑤(明)熊廷弼:《論遼左危急疏》,《按遼疏稿》卷2,第417-418頁。所以遼東可謂是“孤懸之地”,不僅壓力重大,而且想要對這一地區進行支援、運送衣食物資,也有相當的難度。
在此狀態下,各種不利因素又同時施加在遼東地區,必然導致遼東不堪重負,遼民不安生業,乃至想要逃離此地,另謀出路。據張士尊對明代遼東地區人口的研究:“從正統到天啟初年(1621)近一百九十余年的時間里,遼東人口沒有大的增加,一直保持在40—50萬左右。”⑥張士尊:《明代遼東邊疆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頁。雖然明代戶籍人口的統計存在很多問題,不能據以斷定人口的實際數字,但遼事爆發之后,逃向各地及后金統治區內人口的大致情況都有比較官方的記載,張士尊據以分析,將各方面人口數字相加,認為總共約有50萬左右⑦張士尊:《明代遼東邊疆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頁。。這里面的人口是根據實際情況記錄的,與戶籍統計上的不作為、弄虛作假不同,所以誤差不會太大。由此可見,遼事初起這一段時間,遼東的人口依然相比明朝初年沒有太大起色。
遼東地區人口長期徘徊不前、經濟發展也較慢,其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遼東地區賦稅重、軍民壓力大,從而影響生產的積極性⑧具體可參見楊旸《明代遼東都司》第十章第一節“繁重的賦稅”和第二節“沉重的徭役”,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0-218頁。;二是遼東地區強敵環伺,屢遭戰禍,對于當地的破壞嚴重,軍民也缺乏安全感;三是明中后期邊鎮普遍出現的弊政,豪勢之家興起,貧富分化,邊政廢壞等;四是偶發因素,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災荒:“巷無炊煙,野多暴骨,蕭條慘楚,目不忍視。問之,則云去年兇饉,斗米主銀八錢。母棄生兒,父食死子。父老相傳,咸謂百年未有之災。”①《明世宗實錄》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甲子,第7967頁。還有“高淮亂遼”也給遼東造成嚴重的創傷。這幾方面同時作用在遼東,遼東本就不堪重負,兵革一興,遼東更是難以自存了。
事實上,熊廷弼一直在追求遼東自存之道,因而在其按遼期間,大舉屯田、修邊。熊廷弼力主從各鎮調援兵和將領,以支撐遼東:“時督臣深以臣言為然。且先已開單咨部,再欲有所征調,以厚集兵力,而樞臣移書與臣,亦言以新餉養援兵,庶可得目前之用,尤勝于新集烏合之眾。大抵所見皆同。蓋應急之法不得不出于此,正唯此輩慣戰,能沖鋒破陣,而非徒以齒牙博得之餉,豢此逐隊隨行之物也。果如科疏曰‘將不習也’,必將皆土產,然后可;曰‘廢將不成也’,必將盡部除,然后可;曰‘援兵遺患也’,必有事不調防,不入衛,然后可;曰‘當用鄰鎮見任將也’,必薊門諸將官各舍其地方之責,而為我領援兵,然后可。此等議論,即該科亦自以為窒礙,直是有心抑損,使邊臣用一人不得,使一卒不得,束手與懦弁弱軍共盡,而己得旁觀其敗,弄文墨為愉快耳。”②(明)熊廷弼:《論援兵疏》,《按遼疏稿》卷5,第594-595頁。當時遼事還未起,熊廷弼認識到遼東局勢的危險,力主調客兵客將,而反對“將皆土產”、“當用鄰鎮見任將”等觀點。
而且遼東地區本來就不設州縣,為都司—衛—所管理體制,相對于布政使司—府—州—縣的體制,缺少文官政治,遼東地區的科舉也不發達。正因如此,熊廷弼對于遼東地區的官員也不滿意,他在按遼時曾提出:“遼東無郡邑,有司事事倚辦于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謀,有何憂慮,有何為國報效之心,有何維桑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既一籌莫施;而狡黠者,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惶恤其后。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御而不備御。”③(明)熊廷弼:《防建夷疏》,《按遼疏稿》卷4,第546頁。
熊廷弼對于“遼將”的印象也不好,認為“遼將素怯戰,畏臣法度嚴明,慮無不人人憤私相語,寧死虜,不死臣法”。④(明)熊廷弼:《請停修屯辯撫院疏》,《按遼疏稿》卷5,第614頁。對遼東的整體印象則是:“蓋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懶傲而上縱徇,全被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己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己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己寬大,本市德避怨,而借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托辭聯屬,大家相濡相沫,只圖做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真上緊為地方干事?而茍有一認真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弄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⑤(明)熊廷弼:《嚴急招尤疏》,《熊經略疏稿》卷2下,第73頁。“遼中邊事,遼弁以欺隱為常,遼人以挾騙為常。每一邊事出,衙役借查訪,視為奇貨。”⑥(明)熊廷弼著,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20,前經略疏牘,《與內閣部科》庚申七月初九日,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1045頁。
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對于遼東地區的人心也有沉重的打擊。熊廷弼描述道:“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后,風鶴自驚。”⑦(明)熊廷弼:《河東諸城潰陷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9頁。“傭徒廝役,游食無賴之流,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①(明)熊廷弼:《遼左大勢久去疏》,《熊經略疏稿》卷1下,第54頁。“今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今沈陽皆已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臣安能保?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②(明)熊廷弼:《遼左大勢久去疏》,《熊經略疏稿》卷1下,第56頁。“豈意才出,而北關又陷。遼人魂魄屢次飛散,開原陷而鐵嶺逃,鐵嶺陷而沈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逃。”③(明)熊廷弼:《申明還兵情由疏》,《熊經略疏稿》卷2上,第1頁。
在此情況下,又發生了新募遼兵大量逃走之事。在遼東募兵,是“以遼守遼”之說在當時付諸實施的主要內容。贊畫劉國縉在遼東南部招募萬余人,熊廷弼稱這些人“素未見戰,照銀差僉派,誘脅使來”④(明)熊廷弼:《性氣先生傳》,國家圖書館藏《熊襄愍公集》卷8,第21頁。。結果等到開原、鐵嶺失陷后,“楊于渭原領一千八百余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余名”“卞為鵬等原領三千三百余名,沙汰及逃回二千六百余名”“此外尚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余名,曲韶領一千九百余名,而臣不敢比驗矣。恐一比驗,復逃走如卞為鵬等所領者,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⑤(明)熊廷弼:《新兵全伍脫逃疏》,《熊經略疏稿》卷2下,第48頁。。熊廷弼指出:“各援兵方日思逃走,而遼人乃首為之倡。奴賊方聞我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陽,而遼人乃更以此風聲示賊也。”⑥(明)熊廷弼:《新兵全伍脫逃疏》,《熊經略疏稿》卷2下,第48頁。乃至“發之總兵,總兵不受;發之將官,將官不領;發之各邊堡,各邊堡不收,且有收之,而恐為賊覬,請再發兵以護新兵者”。⑦(明)熊廷弼:《與京師諸公》己未十一月初十日,《熊經略書牘》卷2,第27頁。可見遼兵不僅無益于地方,而且影響士氣,助長逃脫之風。
就近募兵除了不堪戰而逃跑的情況外,遼東巡撫周永春在給熊廷弼的書信中還提到了兩點問題,一是“舊軍以糧薄,紛紛棄伍,投充新兵,舊營伍無一處不亂。各營衛批拏逃軍,赴弟衙門掛號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變名易姓,難以盤詰”換言之,衛所軍為了得到更好的收入,棄伍變換姓名去應募,反倒增加軍餉支出;二是“奴之奸細無處無之,往往投入新兵中,更難物色”⑧《熊廷弼集》卷14,揭帖,《發抄周毓陽中丞以遼守遼書揭》,第680頁。,也就是努爾哈赤所遣的奸細有可能混入其中。
故而熊廷弼堅持朝廷加緊調兵調餉,支援遼東,而不要指望遼東自身能夠應付這場危機:“伏乞皇上亟敕兵部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徒虛文搪塞。仍敕督臣汪可守,顧總督薊遼之名,而深思其義,同心協力,委曲調發,急救遼陽。”⑨(明)熊廷弼:《急救遼陽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16頁。“伏乞皇上獨斷,如朱萬良事,亟發李懷信帶領家丁,并挑原題未發薊兵一千五百名、退換兵五百名,星夜前來,救此旦夕之急。其兵部題發各鎮兵將,更乞嚴敕催發,如期來援。”⑩(明)熊廷弼:《請發近鎮兵將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28頁。“惟是各鎮諸臣不肯效同舟之義,凡調一將,皆執留不發,凡遣一兵,皆留精銳以自衛,而別倩孱弱不堪者以搪塞了事。”?(明)熊廷弼:《精選援兵疏》,《熊經略疏稿》卷1下,第65頁。乃至要用兵十八萬:“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余萬,及圍楊酋于囤上,猶用十五萬眾。今賊改元僭號,已并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虧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眾,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播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①(明)熊廷弼:《敬陳戰守大略疏》,《熊經略疏稿》卷2上,第16頁。
但實際調兵、調餉之時,又不能按照議定的數字及時調撥。雖然有圣旨催促,也并不奏效。熊廷弼于是批評“兵部尚書黃嘉善、戶部尚書李汝華,身擔兵餉重擔,皆圖全軀保妻子,莫有肯為皇上拼死力爭上緊干辦者,何況各省鎮督、撫諸臣?”②(明)熊廷弼:《部調紙上有兵疏》,《熊經略疏稿》卷2上,第36頁。“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混寫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皇上見之,豈不好看?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③(明)熊廷弼:《欽限考成疏》,《熊經略疏稿》卷2上,第41頁。故而人們對熊廷弼“嚴急”“性剛負氣”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然而奴爾哈赤統治后期在遼東壓迫、殺戮漢人,造成遼東漢人的抵抗、流亡,為淵驅魚,遼民又成為明朝可以信任的一支力量,故而夏允彝說:“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然數戰之后,遼人實可用也。”④(明)夏允彝:《幸存錄》卷中,《續修四庫全書》第4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0頁。
二、遼東豪勢的發展及對朝廷政令的影響
對于“遼人”的實際含義,熊廷弼還有異于眾人的看法,他認為“遼人”與遼東地區的豪勢之家、將門有著重要的關系,而“以遼守遼”這一策略則是他們力主而用以維護和發展自身地位的工具。
明代中后期,衛所制度逐漸衰落,募兵制興起。衛所制是衛所軍服義務兵役,而募兵制則需要出錢招募。同時,募兵制的興起也使軍兵對將領更加依附,家丁制度也逐漸成熟起來。這一過程雖然暫時提升了軍隊的戰斗力,但也進一步破壞了國家原有的制度,加劇了社會分化,壯大了私門,使得一些將領發展成豪勢之家。這些豪勢之家不僅憑借其戰功獲得地位,也會破壞國家的制度,損害國家的利益,而發展其勢力。
對于遼東勢族的危害,姜守鵬在《明末遼東勢族》一文中主要論述了三個方面:一是不斷侵占屯田,加速了明代軍屯的破壞;二是隱占軍丁,官軍家丁化,加速了明代遼東衛所制度的瓦解;三是政權、軍權和地權結合的日益緊密,超經濟強制愈來愈嚴重,加速了遼東軍丁的逃亡與嘩變。⑤姜守鵬:《明末遼東勢族》,《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第204-206頁。總結起來,這些勢族雖然培養起來了一定的實力,在守土平亂的過程中發揮不小的作用,但這是在培養私人的勢力,追求私家利益最大化,乃至可以因為私家的利益破壞國家的利益。因而,勢族的興起、家丁的增多,并不能真正解決明朝面臨的本質問題,反而帶給明朝新的負面影響。
這一問題的典型體現就是李成梁及其李氏集團。李成梁在萬歷年間頗著威名,所謂“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歲賜稠迭。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⑥(清)張廷玉等:《明史·李成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190頁。但李成梁也在不斷地發展其個人集團,發展家丁。他戰功之盛與家丁的英勇作戰密不可分,他通過獎勵機制激勵家丁英勇作戰:“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剿劫帳,或責以御虜先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①(明)夏允彝:《幸存錄》卷中,《續修四庫全書》第4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7頁。可見這些“健兒”與李成梁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李成梁也愿意為了他們的富貴想出各種辦法。在這個時期,李氏集團為了自身的發展,想要建功立業,與國家想要御虜靖邊的意志還能夠比較一致,所以其積極意義還大一些。但也難免為求立功而造假,損害國家利益,如:“曩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他多江上耕與市貂皮者,皆無辜而執,以為虜,一旦群輩死于鋒鏑之下。”②(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11《卜寨·那林孛羅列傳》,《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6冊,第194頁。時有殺良冒功、掩敗為功之事。到了集團利益穩定下來,破敵立功的積極性也就消失了,李氏集團不但在軍事上消極,還利用自身政治、經濟等優勢,壓榨下級,敗壞邊防:“成梁諸戰功率藉健兒。其后健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蕭耗。”③(清)張廷玉等:《明史·李成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191頁。乃至竊據要位,將朝廷職務視為私家的“臥榻之側”,排斥異己,以至于“自撫鎮道將及巡方御史,不出李氏門下親厚,無不立被斥逐”。④(明)李植:《急救戰守先著疏》,《叢書集成續編》第242冊《籌遼碩畫》卷2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760頁。
對此,熊廷弼深知其危害。熊廷弼巡按遼東,就是因為李成梁放棄寬甸六堡,“棄地啗虜”,朝廷要對此事進行勘察。李成梁為了自身的地位,不惜欺瞞朝廷,捐棄國家封疆。因而熊廷弼提出要嚴懲李成梁:“夫人臣有一于此者,法無赦,臣謂楫與成梁當斬也。”⑤(明)熊廷弼:《勘覆地界疏》,《按遼疏稿》卷2,第407頁。
事實上,熊廷弼痛恨李成梁除了其“棄地啗虜”外,更因為其氣焰囂張,子弟盤踞要津,而又損公肥私。熊廷弼曾致書李成梁,指出他“自舉天王爵人予人之事,而濫以為市若此”“濫予親戚、仆役、商賈之類”,指斥李成梁對于他的子弟親近之人,冒予名位,樹立私恩,而壞國家制度。等到“侯閱垣會同胡直指,亦曾疏革冒功人員二百七十余名,不過十之二三耳”的時候,“胡以獲罪,侯立斥去,各豪家巨賈醵金錢巨萬打點內外,及鉆投長公大將軍門下征倭謀復者大半。而后來院、道又各徇情受賄,遂將十年前已經查革、各衛已出甘結者盡數留之”,⑥(明)熊廷弼:《與李寧遠書》,《熊襄愍公集》卷6,第20頁。這些人也稱:“往者行查,賴寧遠公得免。今公又在京為奧援,第醵金錢如前番故事,復何憂?”⑦(明)熊廷弼:《與李寧遠書》,《熊襄愍公集》卷6,第22頁。后又曾對周永春指出“舊功指揮、千百戶、總旗不過二三千員,而自寧遠前后總兵三十年,新添世職至四五千員,何人不費廩俸?何錢不出民膏?”⑧(明)熊廷弼:《答周毓陽中丞》己未八月二十日,《熊經略書牘》卷1,第34頁。李成梁在萬歷十九年(1591)遭彈劾而去職,但到了萬歷二十九年(1601),因為遼東屢易總兵,多無作為,朝廷再次起用李成梁,直至萬歷三十六年(1608)因為“棄地啗虜”之事被劾罷。可見李成梁的再次起用,在朝廷那里有不得已之處,這也助長了李氏的氣焰,“又心以今日之敗為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⑨(明)熊廷弼:《申明款議疏》,《按遼疏稿》卷3,第475頁。甚至在朝野之中,人們都認為李氏不可撼動,“方臣之往勘,而人人為臣危也,謂‘成梁伎倆通神,觸者立碎。’”①(明)熊廷弼:《催勘疆事疏》,《按遼疏稿》卷3,第504頁。
另外,熊廷弼認為邊將貪功,出邊“搗巢”,不僅不能給敵人造成實質性的重創,反而會遭到敵人的報復,使得邊民和邊防受禍,所謂“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邊人以償仇,本務不修,而以人予虜也”②(明)熊廷弼:《再論修屯疏》,《按遼疏稿》卷5,第602頁。。他還列出隆慶五年(1571)到萬歷三十六年(1608)遼東“搗巢”及蒙古方面報復的記錄,而這一時段,絕大部分時間是李成梁擔任遼東總兵,因而熊廷弼所針對的主要就是李成梁。他指出:“每見搗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不敢一報,而搗西虜輒報,報輒殺掠無算,不堵不追,而反趨海、建,取償于東夷以報捷。”③(明)熊廷弼:《再論修屯疏》,《按遼疏稿》卷5,第605頁。可見熊廷弼認為李成梁每每出邊“搗巢”,是為了個人及其集團的功勞,但不管蒙古的報復對于遼東地方造成的傷害。同時為了掩蓋蒙古入境后自己難以有效堵截的事實,又到女真那里發動戰爭以獲得戰功。由此可見,熊廷弼對于李成梁的看法,就是其為了私家利益不惜犧牲遼東的安定,因而認為遼東之禍與李氏有很大關系,所謂“況遼中之事,李氏釀禍,麻氏死難,李氏脫罪,麻氏抵刑”。④《熊廷弼集》卷11,前經略奏疏,《酌議贖罪疏》,第522頁。
我們再看熊廷弼第一次經略遼東時候的情況,鎮臣基本上是外地調來的,如杜松、王威、麻貴、李光榮、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等。熊廷弼初到遼東就上奏罷免了李如楨,指出李如楨有“十不堪”“其人已奄奄忽忽,無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而無心可殫,無力可奮,徒知拼死,而不能滅賊,死更害事”⑤(明)熊廷弼:《主帥不堪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36-38頁。。更指出遼東雖有新募兵丁,但無將領統帶,“昨搜索遼中廢閑,已虛無人,不得已,將新被參劾楊于渭、文濟武、湯遇時等皆行取用,然亦不能充十之一二”,所以議從各鎮調將領“共計九十三員”。⑥(明)熊廷弼:《急缺將才疏》,《熊經略疏稿》卷1下,第43頁。
劉國縉所募萬余人大半逃走之后,熊廷弼批判“以遼守遼”之說,指出:“乃臣則因是而嘆‘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之為此說者,遼人為自用地耳;主此說者,為用遼人地耳。”⑦(明)熊廷弼:《新兵全伍脫逃疏》,《熊經略疏稿》卷2下,第50頁。也就是認為“以遼守遼”這一主張是“遼人”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而提出的,他們不想因為客兵客將的調入而使利益受到損害。顯然,能夠“初為此說”“為自用地”的不能是下層普通的遼民,因為他們并沒有倡導“以遼守遼”這種言論的能力,也不會因此得到很高的地位,所以熊廷弼所指的“遼人”,更主要的是針對在遼東有一定地位的人,如勢豪、廢閑將領等。
然而廣寧之敗后,明朝收復遼東的希望更為渺茫,戰火幾乎要燒到山海關,這是“危急存亡之秋”,而熊廷弼想要維護朝廷綱紀、抑制私門的發展也就更不可能。這個時候,拉攏遼東的上層人物以爭取更多的遼人擁護是一種更為現實的做法。
三、“漸進漸逼”與速戰速決的矛盾
熊廷弼反對“以遼守遼”,指責朝廷大臣在遼事上不能協力同心,是站在經略大臣的角度上來說的,因而也有不能體會到中央朝廷苦衷的地方,從而與中央、地方官員的矛盾愈演愈烈,乃至最終“傳首九邊”。實際上,從遼事初起后,明朝內部對于遼事的態度就有兩種相反的觀點:一是主張先鞏固自身的防線,調兵調餉,讓遼東軍隊具有足夠的實力之后再去收復失地,剿平努爾哈赤;一是主張速戰速決,因為朝廷調集兵丁、糧餉不易,國家財政難以支撐,時間拖得長了,會“師老兵疲”。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主張前者,而皇帝和中央的官員更多傾向于后者。后者更站在中央朝廷的角度看問題,所以知道財政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主張速戰的人也會滑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退縮防線,主守山海關,如王在晉、高第等,或者主張干脆放棄遼東。從薩爾滸之戰到松山之戰,這兩種主張一直在相互博弈,結果卻是兩種主張都無法很好地貫徹,爭端也越來越嚴重。最終明王朝不僅丟掉了遼東,也失去了天下。
薩爾滸之戰的時候,明軍準備并不足,一共八萬余人,又兵分四路,急于出戰,終于大敗:“四十七年正月,我師征調云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期。”①(明)茅瑞征:《東夷考略》,《續修四庫全書》第436冊,第67頁。又據實錄,神宗批示:“東事料理已久,師期將及,一切戰守機宜如何,尚無成議。且北關獲捷之后,虜中情形久無奏報,怠緩若此,安望成功?爾部即馬上差人傳與經略楊鎬,將議定征剿防御方略作速馳奏。今大兵云集,饋餉煩難。倘致師老財匱,責將誰諉?”②《明神宗實錄》卷578,萬歷四十七年正月癸卯,第10946-10947頁。可見朝廷內部以萬歷皇帝為首,都在催促出戰。
熊廷弼對此總結道:“使于清、撫失事以后,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之,將賊兵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③(明)熊廷弼:《河東諸城潰陷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10頁。所以是“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致今日”④(明)熊廷弼:《河東諸城潰陷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12頁。他因此指出,朝廷應該多站在遼東的角度考慮問題:“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征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為?”⑤(明)熊廷弼:《河東諸城潰陷疏》,《熊經略疏稿》卷1上,第12頁-第13頁。保障沈陽等地的安全,各據點成犄角之勢,而逐步將努爾哈赤困死:“今年料賊必犯沈陽,計不先守沈陽、奉集與賊相持,而聽其至遼,為城下之戰,不但驚恐人心,抑且愈示賊弱。所以遼陽工完即修沈陽,沈陽工完即修奉集,而賊果恐我遂成犄角也。”⑥《熊廷弼集》卷10,前經略奏疏,《賊夷分頭入犯疏》,第473頁。熊廷弼引用西漢趙充國的事跡,來闡述他的主張。趙充國平定羌人叛亂的時候,認為“攻不足者守有余”,當時的形勢平定叛亂還不成熟,于是主張屯田,使軍隊亦兵亦農,待時機成熟后再一舉平定叛亂⑦(東漢)班固:《漢書·趙充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81-2983頁。。熊廷弼認為應該待兵力四集,己方無懈可擊之時,再穩步推進,一舉剿平努爾哈赤集團。他也“自知為無厭之求”,但“不如此,不足以抒不佞之窮蹙,而救殘鎮之危亡”。⑧(明)熊廷弼:《與黃梓山本兵、薛對龍兵科》己未十月十六日,《熊經略書牘》卷2,第5頁。
然而,朝廷內主張速戰的人又開始批評熊廷弼:“兵科左給事中楊漣疏論遼東經略熊廷弼:‘邊警日聞,人言屢至,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虜,即當繳還尚方,席藁侍罪,不宜效近日頑鈍行徑。’”①《明熹宗實錄》卷1,泰昌元年九月戊子,第50頁。“廣東道御史馮三元劾其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健兒不以御侮,而以渡壕,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無謀四也。”②《明熹宗實錄》卷1,泰昌元年九月丁亥,第48頁。“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幸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③(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3-24頁。時為山東巡撫的王在晉則從山東的角度指出目前的困難:“東省距北直一塵,進之則為北直應募之兵,退之則為山東思逞之盜……故舉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省之饑民也。”④《三朝遼事實錄》卷3,庚申六月,第409頁。熊廷弼對此解釋道:“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諳軍中情實,而第憑賊報緩急以為戰守。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戰敗,又各愀然,禁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臣收拾才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著,如前漸進漸逼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臣言。”⑤(明)熊廷弼:《奉旨交代疏》,《熊襄愍公集》卷4,第85頁。“官軍未集未練,便謂師老財匱,而馬上促之。及其敗,又不征兵集餉,坐亡開、鐵、北關而不悔。”⑥《熊廷弼集》卷20,前經略書牘,《與內閣戶部兵部兩衙門》庚申五月二十四日,第1015-1016頁。速戰與徐圖恢復兩種觀點的碰撞,最終還是速戰派占了上風,熊廷弼被迫去職。
第二次經略遼東時,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布置策”,即:“廣寧用騎步對壘于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⑦《明熹宗實錄》卷11,天啟元年六月辛未,第543頁。“三方布置策”涉及廣寧、天津、登萊、朝鮮等各地,遼、沈失陷后,遼東地區的重兵都駐扎在廣寧,但廣寧在“三方布置策”中只是吸引敵軍主力的部分,而非收復失地的部分,那么其他各方也必須要有足夠的準備,才能夠達到其效果。他還巡查三岔河、廣寧等地的情況,指出“及至廣寧,問兵,則雖挑有頭敵、二敵,而尚未屬以何將也;問馬,則不及三萬匹,而以缺料倒死者不勝報也;問甲仗,則京運高閣無用,又無匠改造,軍多氈帽布掛,而執棍以立也;問火砲、戰車,則皆無有,雖拒馬槍、牌钁斧、蒺藜之類亦無一備,而無以扎營立腳也……”⑧《熊廷弼集》卷13,后經略奏疏,《備述出關情形疏》,第638頁。各方面都沒有準備好,所以熊廷弼又向朝廷求兵求餉:“尤乞皇上為封疆宗社計,于主調主募者,感之以至情,責之以大義,治之以大法,以信抗違逮治之旨,于天下若如從前嚴旨申飭。”⑨《明熹宗實錄》卷11,天啟元年六月壬辰,第574頁。“欲趁此身在內,與三部將兵馬、糧餉、器械事情求一實落,何意終日講而竟無一著落也。今臣行矣,持空拳而與賊搏,微獨臣自信無此伎倆,即諸臣亦信臣無此伎倆也。愿兵部速解銀兩往各處調募,戶部與兵部通融計處,工部勉為皇上打造供應,此又臣行后無已之望也。”⑩《明熹宗實錄》卷11,天啟元年六月丙申,第580-581頁。
但是當時四川奢崇明叛亂,明廷分身不暇。首輔葉向高認為“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①《明熹宗實錄》卷17,天啟元年十二月己卯,第852頁。“乃善治癰疽者,必節宣其營衛,護其元氣,使毒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克伐之劑,而取效于一時,曰‘我能治癰疽也’,不知癰疽未去,而腸胃已先裂矣”。②《熊廷弼集》卷14,揭帖,《駁葉向高廷議紛紜疏揭》,第701頁。董其昌也說:“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③《三朝遼事實錄》卷6,辛酉九月,第472頁。乃至有人提出以黔國公故事懸賞,“有能復全遼者,即令世守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市租、田賦、山澤之利盡捐與之,俾之專力捍奴,毋累四海內,庶幾有息肩之日乎”,④《熊廷弼集》卷14,揭帖,《駁葉向高廷議紛紜疏揭》,第702頁。至天啟五年(1625)太仆寺卿黃運泰仍提此策:“今宜速下懸賞之令:一應文武官員,有能殲奴酋、克復遼陽者,準照云南黔國例,晉封國公,世守遼陽。”⑤《明熹宗實錄》卷57,天啟五年三月丁巳,第2614頁。
兵部尚書張鶴鳴、遼東巡撫王化貞等人主張以廣寧一帶為主要經營的地區,從此收復失地,所謂“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意”,而且認為“兵日援遼,原為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為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張鶴鳴提出:“撚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矣。”王化貞則提出:“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御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豪杰不足以馳。”“此時過河,我氣百倍,雖少,可以成功;若待其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⑥《熊廷弼集》卷13,后經略奏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第632-634頁。可見張鶴鳴、王化貞主張從廣寧盡快出擊,速戰速決。又借助林丹汗(即虎墩兔憨)的力量,孤注一擲,所謂“人情亦知戰未易言,徒以仆不能守之說,遂欲庶幾僥幸于一擲”。⑦(明)熊廷弼:《與王肖乾中丞》,《熊襄愍公集》卷7,第16頁。但其實,王化貞也知道現實的情況不容樂觀,不能輕易進取,所以“撫臣之進,及今次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⑧《明熹宗實錄》卷17,天啟元年十二月丙戌,第864頁。,“撫臣果移臣書曰:‘兵部不言車馬甲仗作何催發,而但言機會可乘、宜速進取,甚至言廣寧兵有十四萬,真是可笑’”⑨(明)熊廷弼:《遼事是非不明疏》,《熊襄愍公集》卷5,第32頁。,可見王化貞并非不了解自身實力的不足,但也有些迫于壓力,不得不有所“動作”。最終因為廣寧本身的漏洞,造成遼西地區的大潰敗。于是,“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參樞臣張鶴鳴主戰誤國,飾說欺君,乞處分以明國是”,但是“上以公論自明,不必深辯”⑩《明熹宗實錄》卷25,天啟二年八月甲申,第1272頁。,可見天啟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傾向。
廣寧潰敗后,退縮防線的主張逐漸興起,薊遼總督王象乾認為:“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清)張廷玉等:《明史·孫承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6467頁。王在晉認為:“臣嘗謂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后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后可復全遼。不然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明熹宗實錄》卷26,天啟二年九月庚子,第1302頁。孫承宗督師后,對于防守格局的爭論仍然不休:“帝乃罷鳴泰,而以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關議。承宗不悅,乃復出關巡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眾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中后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①(清)張廷玉等:《明史·孫承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469-6470頁。可見主守山海關的意見還是很多。孫承宗認為:“而我自燒寧前……更望經臣于虛活之著,提掇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戰,事事在戰,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內,乃為善守關也。蓋不能戰決不能守,而以戰失守不可,以守忘戰不可也。”②《明熹宗實錄》卷24,天啟二年七月甲寅,第1213-1214頁。
但是孫承宗在與以王在晉為代表的退縮防線派斗爭的時候,自身又面臨速戰與慎戰的矛盾,兵餉問題又被提出來。工科的郭興治指出:“養十三萬之眾,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況又不盡入征戎之腹,徒半充貪弁之囊。”③《三朝遼事實錄》卷14,乙丑三月,第679頁。“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言,從古征戰未有陳師境上數年不進者,亦未有去敵既遠虛設十余萬之眾坐食自困者,有之則守戍之眾而非進取之旅也……今以十四萬之眾,歲費六百萬,雖言唯敵是求,其實百事不辦。”④《明熹宗實錄》卷60,天啟五年六月己卯,第2785-2786頁。孫承宗也不得不承認:“而況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既難久戍,更苦更番。時可烏合,時可烏散,師老財匱,日久變生。”⑤《三朝遼事實錄》卷12,癸亥二月,第640頁。“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之。”天啟皇帝還是想給孫承宗一個機會的,“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于是,“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祿,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萬。”⑥《明史·孫承宗傳》,第6472頁。
還有士兵嘩變的問題。明廷從內地抽調來自陜西、山西、四川、湖北、山東、河南、直隸的軍隊,云集山海關一線。這些遠來之兵,糧餉稍有不繼,輒嘩變逃亡,或是消極避戰,怠惰困守,成為遼東前線一個棘手的問題。“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王在晉也指出:“兵以放寇也。兵無食,即為寇,而其害甚于寇。寇尚有兵以御之,兵為寇,而地方無可御矣。”⑦《三朝遼事實錄》卷3,泰昌元年十月,第423頁。“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墻……有兵無餉,兵即為地方之患。”⑧《三朝遼事實錄》卷6,辛酉九月,第474頁。
后來孫承宗去職,高第又主張重點守山海關。但這一時期,追求速戰的聲音已經不占優勢,無論是主張守山海關,還是主張防線向前延伸,都不會貿然出擊,所以也沒有出現薩爾滸之戰和廣寧之戰那樣的大敗,明軍還在寧遠、寧錦兩次戰役中擊退了后金軍的進攻。
然而至崇禎皇帝即位后,明朝的統治危機更加嚴重,形勢更加危險,崇禎皇帝“求治太速”,所以袁崇煥才會提出“計五年,全遼可復”⑨(清)張廷玉等:《明史·袁崇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713頁。這樣具體的承諾來滿足崇禎皇帝的期待。至松山之戰時,洪承疇仍然提出“且戰且守,久持松、杏,以資轉運”,但明朝行將崩潰,更加拖不起,“用師年余,費餉數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⑩(明)談遷:《國榷》(第二十四冊)卷97,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513-14514頁。,所以催促洪承疇出戰是必然的。
由此看來,明朝與后金在遼東的戰爭中,一直無法擺脫速戰與慎戰、退縮與推進的矛盾,其中財政困難、客兵征調困難是引發這兩對矛盾的重要因素。隨著戰事的推移,熊廷弼那種征調天下人力、財力的做法越來越難以實行。所以,孫承宗和袁崇煥不得不妥協,打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旗號來應對朝廷內部“師老財匱”的批評。但是就算孫承宗和袁崇煥想方設法節約支出,關寧防線每年還是要花費朝廷數百萬兩的白銀。因而李魯生等人不斷指責孫承宗,孫承宗也不得不發動柳河之役。崇禎皇帝指望袁崇煥能夠“五年復遼”,又對他“付托不效”感到失望。可見“以遼人守遼土”的策略沒有本質上解決明朝的財政問題,這一策略更多的是應付朝野的指責。
同時,孫承宗、袁崇煥以及明廷也對“遼將”的任用更寬松了。孫承宗督師遼東后,祖大壽等遼東豪勢人物在遼東地區的地位越來越突出,祖大壽在袁崇煥被逮捕后,“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赍手書慰諭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馳撫諸軍”①(清)張廷玉等:《明史·孫承宗傳》,北京:中華書局,第6474頁。。這不僅因為祖大壽握有軍隊,還因為他在遼東地區的影響。李洵先生指出:“清太宗曾認為明國之所以重視祖大壽,不敢對之加罪,是因為祖大壽‘其族黨甚強’。這里已明白指出,祖大壽的價值就在子他是‘族黨甚強’的‘祖家將’的首領”。②李洵:《祖大壽與“祖家將”》,《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2、3期。所以就算祖大壽曾經欺騙過皇太極,皇太極也要盡力招撫祖大壽,以爭取遼人的歸附。而吳襄、吳三桂父子同樣出身遼東,和祖家有姻親關系,并在明末清初的政局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此可見,天啟、崇禎年間,明朝迫于現實情況,也不得不對遼東的豪勢進行妥協,而讓他們在遼東防務上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結 語
關于明末遼東問題及明金戰爭,涉及很多人物,也涉及很多爭議。在這些爭議之中,有的爭議會有對錯之分,有的爭議則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所導致的。熊廷弼反對“以遼守遼”,是其基于遼東地區的現狀所得出的結論,但其他大臣與熊廷弼屢起爭端,也自有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其中明朝面臨的財政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從熊廷弼來說,他是在為朝廷托付他的封疆重任考慮;從朝臣來說,他們是在為朝廷的財政與天下的穩定考慮。熊廷弼為人盡公不顧私,而朝臣難免懈怠、拖延,但他們的為難也不是沒有道理。拋開簡單的個人得失,我們會對遼東問題以及明朝的滅亡有更深刻的理解。明朝在遼東屢屢失利,看似是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等人的錯誤決策造成的,背后則是明朝內部各種矛盾集中的爆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朝財政管理上的問題,看到國家動員能力的不足,看到朝廷缺乏強有力的核心以致用人不專,看到黨爭的激烈。總結起來,根本問題還是在于明政府的凝聚力、動員力、行動力已經嚴重不足了,遼東的情況則是這些問題最集中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