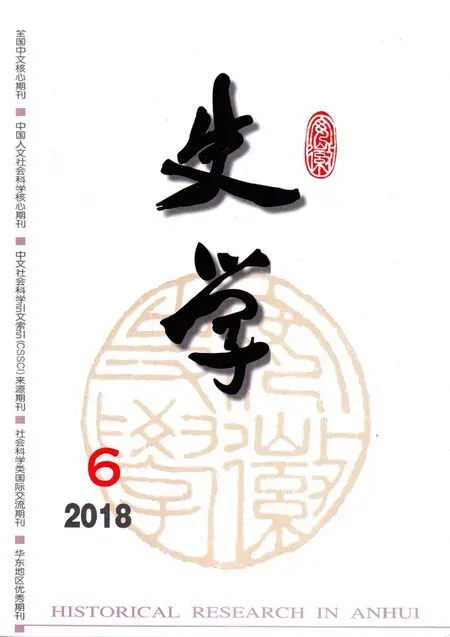北洋海軍購置蚊船、鐵甲船史實補正
陳先松
(江蘇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臺灣,清政府因為對方2只鐵甲船的威脅而以求和告終。在這一背景下,李鴻章建設北洋海軍之初,重點購置“敵有我無”的鐵甲船,以及據說可以擊沉鐵甲船的蚊船。學術界對此多有研究,但主要探討赫德等經辦人的具體作用,相對忽略李鴻章這一核心人物的購艦決策。部分學者在一些史實敘述和結論方面,亦有補充、商榷之處,譬如認為:第一批蚊船的訂購,是赫德與總理衙門的共同決策,出現任何問題,不應歸罪于李鴻章;李鴻章對蚊船的信心產生動搖,始于光緒五年或光緒六年;李鴻章至光緒五年下半年后,已意識到購置蚊船吃虧,卻指使山東等省繼續購置蚊船,是遮掩之前購船錯誤、玩弄權術的結果;丁日昌《海洋水師章程》中提到的大兵輪船即鐵甲船;李鴻章最初不愿購買鐵甲船,并以日意格購船事件為例,說明其理由之一,源于巨炮威脅論;李鴻章最初幾年放棄購買鐵甲船的另一原因,是赫德的阻撓;李鴻章光緒五年之前對鐵甲船的態度是觀望、查詢或阻撓,之后才緊鑼密鼓地購買;丁戌奇荒對李鴻章購置鐵甲船的負面影響,是北洋海防專款的大量挪用;李鴻章光緒五年初決定購置鐵甲船,源于赫德呈遞《條陳海防章程》進而染指海防權力的威脅;李鴻章光緒五年十月停購鐵甲船,是擔心購船后會并入南洋,故“有錢不愿讓南洋分沾”,直至南洋大臣沈葆楨逝世,才又開始購置等等。[注]參見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增訂本),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17—130頁;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26—140頁、153—162頁;羅肇前:《李鴻章是怎樣購買鐵甲艦的》,《福建論壇》1993年第4期;劉振華:《赫德、金登干與晚清艦船的購買》,《軍事歷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曾志文:《西方鐵甲艦議購與晚清海疆籌防——以李鴻章私函為中心》,《學術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擬充分利用新版《李鴻章全集》《清代孤本外交檔案》《李星使來去信》等文獻,以時間為線索,全面梳理李鴻章購艦心態的演變歷程及影響其購艦決策的相關因素,并就學術界已關注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一、李鴻章與第一批蚊船的購置
蚊船是一種守口的浮動炮臺,以較小的艦體裝置一門巨炮,靠調整船體來瞄準射擊目標,在港口防御時與岸上炮臺機動配合,以擊退敵人的進攻。[注]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第120頁。在清末中國,蚊船可以音譯為“根駁船”(gunboat),也可根據外形特征、作戰形式等直譯為“守口大炮鐵船”、“水炮臺船”、“鐵炮臺船”等。
早于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年,李鴻章已聽聞蚊船的音譯名稱——根駁船,但他缺乏了解,以為船體可裝載數門大炮。[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頁。甚至在接下來的數年內,也將根駁船與蚊船的直譯名稱——守口大炮鐵船、鐵炮臺船等相混淆,稱中國除30只根駁船外,還需添置名異實同的守口大炮鐵船20只。[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頁。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犯臺灣,沿海各省紛紛設防,洋商也借機兜售蚊船、鐵甲船等。李鴻章始對蚊船有所關注,并建議江蘇巡撫張兆棟放棄鐵甲船,添置價格相對低廉的蚊船,稱:“吳淞炮臺……若添守口鐵炮船,較有依恃……海口只宜鐵炮臺船也。”[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89、83、89、95頁。文中的“守口鐵炮船”、“鐵炮臺船”等,即指蚊船。李鴻章雖認識到蚊船的守口價值,但限于經費,并無購置意圖,稱:“敝處欲添置槍炮,不名一錢,遑論其它。奉天海口極多,一無防備,誠如尊示,是以中外無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則百了,更不計及此后如何整備也。”[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89、83、89、95頁。
北洋海軍第一批蚊船的購置,最初由總稅務司赫德和總理衙門商議、推動。學術界相關成果,通過《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等文獻,對赫德購船的過程,已有充分研究,但甚少提及赫德通過何種渠道推動蚊船的購置。
查日本侵臺事件以后,赫德與總理衙門多有接觸。同治十三年五月,赫德建議中國不宜購置西洋鐵甲船,“價廉者不合用,合用者價不廉,各國合用者不肯出售,出售者不能合用”,且鐵甲船價格昂貴,每船約銀120萬兩,“一經遭損,修理更難”。[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7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頁。六月,向總理衙門集中反映洋人、洋行兜售軍火的弊端,譬如推薦鐵甲船的某洋行,信譽不佳,歷史上曾兩次倒閉;某洋商代日本購買槍支,打算將質量低劣者轉售中國。總之,“賤價買賤貨耳”。[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7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頁。八月,正式提出蚊船巨炮的設計理念,稱英國新造大炮,可在3里外擊破甲厚24寸的鐵甲船,以致“英國不另造鐵甲船,專做此炮”,而負載此炮,“閩船恐不能支”,需在外洋另求堅固船體。[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7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頁。
赫德與總理衙門的頻繁接觸,產生積極影響。總理衙門后來奏稱:“赫德自上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擾臺事起,屢在臣衙門議及購買船炮各事,經臣等詳細詢究,擬即量力先行購辦,責令該總稅務司經理,以視各口洋行經手購辦者較有責成。”[注]總理衙門片,光緒元年四月初二日,軍機處錄副奏折,3-9381-30。本文所引軍機處錄副奏折,皆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總理衙門此奏,與其當初所想,尚有一定距離。赫德闡述蚊船理念后,總理衙門猶豫不決,稱“誠恐一時難于備辦”,要求李鴻章就南洋、北洋的海防實際等,討論赫德所述各節,以供參考。[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7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頁。自此,李鴻章成為是否訂購蚊船的重要決策者。
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鴻章復函總理衙門。雖然洋商的報價從八月初的每船炮“十余萬內外”[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89、83、89、95頁。,虛漲到“五六十萬元至百萬元不等”,但出于北洋自身利益,李鴻章贊成由總理衙門代置蚊船,稱赫德所述巨炮,“即系鐵炮船上所用,又名蚊子船,又名水炮臺,守海口最為得力……將來南北洋必須訂購二三只,分布要口,認真操練,庶各國兵船不敢覬覦。”[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89、83、89、95頁。
九月初二日,總理衙門收到李鴻章復函后,堅定了購置決心,囑咐后者“籌復商辦”。初九日,李鴻章向總理衙門進一步強調蚊船的海防價值,認為駛近中國口岸的鐵甲船,“鐵甲不過數寸,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為得力,較陸地炮臺更為靈活”,并贊成由赫德代購,“總稅司經辦當較洋行行為可靠”,每船僅銀10萬兩。[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頁。在總理衙門、李鴻章同意下,赫德委托海關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具體負責蚊船的訂購事宜。
光緒元年(1875年)春,赫德攜帶金登干有關蚊船信函以及自己草擬的購置合同,與李鴻章“連日接晤,逐細討論”,議定于英國阿姆斯特朗廠訂購38噸巨炮蚊船、26.5噸巨炮蚊船各2只,相關經費共45萬兩,由江海等關洋稅項籌撥。[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頁。這4只蚊船即龍驤、虎威、飛霆、策電號。
二、李鴻章與后續蚊船的購置
李鴻章對蚊船頗為期待,稱總價不及鐵甲船1只之費,若真能制伏鐵甲船,則“日后添購為費尚省”,即使不確,而“巨炮已為中國所無,船只亦能隨時修理,出入各口,戰守皆宜,似不至糜費無益”。[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頁。至光緒二年,李鴻章檢閱先期抵達的龍驤、虎威號,甚是滿意,“所有炮位輪機、器具等件均屬精致靈捷……運炮裝子全用水力機器,實系近時新式,堪為海口戰守利器”。[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7冊,第211—212頁。
光緒三年底,李鴻章對蚊船的信心有所動搖。因為蚊船的船底鐵板“久浸鹽水,均生茜草”,進而影響航速,李鴻章令福州船政局修理。至光緒四年正月,新聞報紙傳言蚊船到福建后,“有行走不動之說”,時速從原先30里,降到不及10里,引起總理衙門、李鴻章疑慮,“來華未久,行走亦不如從前之速,倘歷有年所,豈不又蹈綠營兵船積習”,“何以閱時未久,相去如此懸殊”。為此,李鴻章致函福州船政局,要求出洋試驗,“據實稟報”。[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239頁;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15冊,第5749—5750頁。
至光緒四年三月,總理衙門、李鴻章對蚊船的擔憂,得到很大緩解。這源于兩個因素。其一,赫德的有力解釋。總理衙門發現問題后,召集赫德咨詢,得出“此等船只似宜動不宜靜,駕船之人似宜勞而不宜逸”的結論,并告之李鴻章[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15冊,第5751、5820—5821、5842—5844頁。,后者贊為“極是篤論”。[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240、293、304、304頁。其二,福州船政局的出洋試驗報告。該報告內容,已不可考,但李鴻章閱后,十分滿意,稱“極為周詳”。[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240、293、304、304頁。參考數月后李鴻章親自檢測的結果,蚊船時速至少達到21里,非報紙所謂的不及10里,“輪機、器具等件均尚精致靈捷,演試大炮亦有準頭”。[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109頁。
不久,總理衙門、李鴻章對蚊船的一點猜疑,即為英國回購事件一掃而空。四月二十三日,英國駐華使館署漢文正使璧利南拜訪總理衙門,商議購回龍驤等4只蚊船。[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15冊,第5751、5820—5821、5842—5844頁。總理衙門、李鴻章認為英國此舉與英俄邊事緊張有關,并以局外中立的原則加以拒絕。然在這一事件中,英國既愿購回,充分說明蚊船的海防價值。李鴻章還打聽到英國亦以此船“專防本國海口,以作水炮臺,抵御鐵甲最為得力”,不僅造有20余只,還打算添造50余只。[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240、293、304、304頁。
英國回購事件,間接促成了北洋海軍第二批蚊船的購置。
其時,清政府劃撥的南北洋海防專款,由于南洋大臣沈葆楨的謙讓,全歸北洋近3年[注]參見沈葆楨折,光緒四年二月初三日,軍機處錄副奏折,3-9382-38。,以致南洋“海防、江防,一無措置”。[注]林海權點校:《沈文肅公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頁。李鴻章應沈葆楨的請求,擬光緒四年初為南洋再購2只蚊船。[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240、293、304、304頁。在英國回購事件中,李鴻章暗示船少,“不敷調撥”,總理衙門認為英國的購船動機“固難盡測”,而蚊船“足適于用可知”,希望李鴻章從海防專款內購置4只。[注]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15冊,第5751、5820—5821、5842—5844頁。李鴻章表態贊同。此4只蚊船即北洋海軍鎮東、鎮南、鎮西、鎮北號,船炮38噸,由赫德具體購置。[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109頁。
可于海口制伏來犯的鐵甲船,是李鴻章一再購置蚊船的重要依據。然至光緒五年,李鴻章日漸清醒:蚊船船小,只能布置于海口,而外國鐵甲船吃水過深,多行駛于大洋之中,兩者直接對敵的可能性很小。若謂守護海口利器,尚屬勉強;若謂足制敵國鐵甲船,則沒有可能。
這在光緒五年赫德向總理衙門自薦總海防司的事件中有明顯體現。赫德自薦的前提條件是:只要假以事權,雇傭西人,認真操練,僅需蚊船、碰快船,“即可以制鐵甲”。[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對此,李鴻章八月十一日致函沈葆楨稱“前定蚊船,原議明可以出海接戰,若徒守口,各口多淺,鐵甲不能深入,殊為無用”[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九月初五日致函曾紀澤稱“赫德謂可海戰,攻破鐵甲,似非確論……(蚊船)既不及鐵甲之乘風破浪,行駛至速,又恐大洋浪戰被炮擊沉,自蹈危險”。[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
李鴻章對蚊船不能制伏鐵甲船的新認識,并非否認蚊船海口設防的巨大價值,前致曾紀澤函即認為“金登干代購蚊子船,經執事查驗,誠為防御海口利器,洵然”。[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九月十一日,李鴻章進一步向總理衙門肯定為“守港利器”,南北洋海口眾多,“若財力有余,盡可添購”。[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與此相關,李鴻章推動了北洋海軍第三批蚊船的購置。
光緒五年十月,因清政府飭令籌議海防,李鴻章稱蚊船“防守海岸最為得力”,要求沿海各省皆自籌經費,購置一兩只,獲得清政府允準。[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511—512頁。按照李鴻章原奏,山東省原只需購置1只,然李鴻章借口浙江、廣東等省未有回音,若僅訂1只,“似難向西廠定造”,勸說山東巡撫周恒祺購船2只,分布煙臺、登州兩處。[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頁。周恒祺欣然允從,于光緒六年初奏請定購38噸巨炮蚊船2只。[注]周恒祺片,光緒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旨日期,軍機處錄副奏折,3-9384-8。此即鎮中、鎮邊號,后歸北洋海軍統一訓練、管理。
三、李鴻章對鐵甲船的態度分析
鐵甲船,是在木質兵輪水線以上部分配以裝甲帶,建一裝甲的中心堡壘,以保護主要武器的安全,具有強大的攻擊和防衛能力。[注]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第155頁。
同治七年,丁日昌草擬《海洋水師章程》,提及可在外海剿匪、“兼用風帆行駛如飛”的大兵輪船。[注]參見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頁;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139頁。此兵輪船并非鐵甲船。丁日昌將兩者區分開,認為鐵甲船視質量等因素,“往往有價賤于兵輪船者”。[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6冊,第225、163頁。
李鴻章聽聞鐵甲船的時間,始于同治十年,認為其用在“防守海口”,接下來的兩年中鮮有提及。[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第229、247頁等。李鴻章對鐵甲船真正有所認識,源于同治十三年的日本侵犯臺灣之役。因為日本兩只鐵甲船的威脅,李鴻章與總理衙門、沿海各級官員頻繁探討鐵甲船的購置問題,參閱了洋商送來的相關圖紙式樣等。[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39、41、48、58、77、80、83、95、105頁。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的海防奏議,是這一時期李鴻章海防思想的集中體現。李鴻章肯定鐵甲船的海防價值,即在洋面“專為游擊之師”,與重視守口的蚊船有別。在海軍建設思想上,李鴻章希望優先購置鐵甲船,東洋、南洋、北洋各2只,“其有余力再置他船”,建議派中國官員親赴外國各廠考究等。[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6冊,第225、163頁。
光緒元年四月,李鴻章受命督辦北洋海防,仍堅持應該購置鐵甲船,五月致函總理衙門稱“約計一軍須兵輪船二十只,內應有鐵甲船一兩只,聲勢稍壯”,七月致函山東省稱“洋面散漫,誠如來示,防不勝防,亦防不能防,將來集有巨款,須照總署原議,創立水師一軍,約鐵甲及大小兵輪船十數只,駐扼廟島、旅順口之間,以固北洋門戶。”[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為購置鐵甲船,李鴻章支持福州船政局學生,“帶往英德鐵甲船學習”,贊為“此舉最為緊急,愈速愈妙”[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以培養駕駛人才。
光緒元年底,曾在福州船政局供事的法國人日意格積極兜售鐵甲船,李鴻章卻致函南洋大臣沈葆楨稱:“各處新聞紙僉謂,德之克鹿卜、英之阿摩士莊新制巨炮,實可洞穿二十余寸鐵甲,而鐵(甲)船轉慮無用,果爾則此事更宜斟酌。”[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這僅是李鴻章婉拒日意格售船的借口。究其實,早于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鴻章通過總理衙門信函,已了解到巨炮可以擊沉鐵甲船[注]參見孫學雷等主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第7冊,第2850—2851頁;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94—95頁。,但如上文所述,并未因此而顯示出對鐵甲船的退縮之意。李鴻章婉拒日意格的真實意圖,一在于對日意格的不放心,“總署惑于浮言,嘗疑日酋(日意格)貪利欺騙,外人亦有附和其說者”,如果購置,需派中國官員出洋,“就便監察,以祛眾疑”[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另在于經費的制約,李鴻章稱北洋海防專款“迄今一年之久,統計各省、關僅解到銀六十余萬,屢催罔應,實解尚不及十分之二……是以幼丹(沈葆楨)函屬(囑)日意格回華商訂鐵甲船一只,尚未敢率允定購。”[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
事實上,海防專款收數有限,以及在此基礎上購船經費的難以籌措,是李鴻章最初愿意而不能購置鐵甲船的主要考慮。光緒元年,清政府為南洋、北洋劃撥海防專款,每年約“四百數十萬兩”,但籌議時未能解決財源問題,劃撥之始即已種下拖欠的惡果。[注]參見陳先松:《晚清海防專款籌議述論》,《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與此相對應,清政府勸李鴻章體諒國家財政困難,對北洋“不云暫緩海防,乃云從容籌備”[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李鴻章不得不表示“能得若干款項,再辦若干兵船,較為穩妥”。[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至光緒三年八月,北洋海防專款僅收存100余萬兩,據當時估算,1只鐵甲船約價100萬兩,連其養兵之費、新建船塢經費等,“統足以舉事”。[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21;429;96、97頁。李鴻章向前福建巡撫丁日昌自嘲為:“無錢逼倒英雄漢,大才將何以處之,時局似急尚緩,務祈從容擘畫,勿過躁迫是幸。”[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21;429;96、97頁。
李鳳苞的建議,是影響李鴻章購置鐵甲船的另一因素。
李鳳苞,字丹崖,江蘇崇明人,“究心歷算之學,精測繪”,同治年間先后調入江蘇輿地局、江南機器制造局、吳淞炮臺工程局工作,接觸近代物理、化學、軍事等書籍,西學知識豐富。[注]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144頁。光緒元年四月,李鴻章慕名召見,贊其“精于輿圖,勤能耐苦,確是有用之材”。[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光緒二年三月,因李鳳苞委帶船政學生出洋,李鴻章令其就近酌購鐵甲船,“較之數萬里外貿貿然徒聽外人指揮者,必更核實節省”。[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至該年八月,李鴻章致函丁日昌,稱鐵甲船應購與否,“須俟丹崖(指李鳳苞)到英后,探討底細,再行定購”。[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由此,李鳳苞成為李鴻章購置鐵甲船的主要參謀。
光緒二年十二月,對鐵甲船多次發表負面評價的赫德,曾正面推動北洋海軍購置鐵甲船,然為李鳳苞所阻撓。赫德向李鴻章所推薦者,系土耳其2只鐵甲船,馬力3600匹,時速72里,25噸大炮4門,鐵甲厚至10寸,每只原需100余萬兩,現因土耳其國“限于資財……情愿虧價相售”,只需銀80萬兩。[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頁。經探詢,李鳳苞認為該船炮位只有4尊,略嫌其少;炮重25噸,卻不用汽機,“自難十分靈捷”;此外還有不合用者數端,例如“機器不用康邦,一也;藥庫近船尾,二也……桅上不裝橫桿,五也;煙通及水鍋之半俱在八角臺外,六也”。不僅質量堪憂,李鳳苞還明確指出,土耳其國在英國另造新船,并非財力匱乏,該二船“久欲求售,并非便宜”等等。光緒三年七月,李鴻章致函李鳳苞,稱其“所議各節,極有見地”,“自應暫作罷論”。[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21;429;96、97頁。
光緒三年底,李鳳苞在歐洲歷觀英法諸國20余只鐵甲船的基礎上,考慮到中國海岸水深多在20尺以內而西洋鐵甲船可進入者甲厚至10寸,建議應在英國繆答廠購置鐵甲船,“以甲厚十二寸、入水十七八尺為率”。李鴻章甚感興趣,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李鳳苞,要求與該廠協商,若“果有新式堅利、吃水不深……價值較廉”的鐵甲船,則“再行議請訂造”。[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與購置決心相對應,李鴻章于光緒四年派遣員弁勘探北洋各口的入水深度[注]參見蔡少卿、江世榮主編:《薛福成日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頁。,以為鐵甲船駐地的選擇提供準確數據。
光緒三年底、光緒四年初,正值華北丁戌奇荒。李鴻章英國繆答廠購船的失敗,與此有很大關聯,但并非因為北洋海防專款的大量挪用。事實上,北洋海防專款用于丁戌奇荒者,大多為借款,約有43萬兩,可由“練餉制錢提還,或議(山西、河南等省)分年解繳”。[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29頁。因借而未還者僅7萬余兩,連同無需償還者,被挪用的總數共32萬余兩。其中,至少約20萬兩于光緒三年秋被挪用,并未阻礙李鴻章光緒三年底的購船決心[注]參見陳先松:《北洋收存海防經費的挪用問題(1875-1894)》,《安徽史學》2013年第2期,第32—35頁。;其余12萬兩,數額較小,對“非存銀三四百萬”不敢購置鐵甲船的李鴻章來說,其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丁戌奇荒,對李鴻章購船真正的影響,是購船經費籌措計劃的破滅。如前文所述,李鴻章建設北洋海防之初,秉持“能得若干款項,再辦若干兵船”的方針。在北洋海防專款僅收存100余萬兩而鐵甲船“非存銀三四百萬不足以舉事”的情況下,李鴻章敢于光緒三年底購置,其關鍵就在于“議請訂造”,即與清廷中樞商議、請撥購船經費。但光緒四年初華北災情加重,李鴻章在清政府的再三垂詢下,自保北洋海防專款尚且吃力,自難以再“議請訂造”。[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29—30頁;第32冊,第452頁。光緒五年六月,李鴻章致函李鳳苞,將光緒三年底英國繆答廠購船的失敗,歸咎于“嗣因籌款維艱中止”。[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
從北洋購船史的角度來說,李鴻章光緒三年底購置鐵甲船的努力,具有另外一層意義,即開始在海防專款收數有限的情況下,打破“能得若干款項,再辦若干兵船”的購船思路,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以籌措大宗購船經費。這為后來定遠、鎮遠號鐵甲船的購置,埋下了伏筆。
四、李鴻章與定遠、鎮遠號鐵甲船的購置
光緒五年,李鴻章再次倡購鐵甲船。這與赫德向總理衙門呈遞《條陳海防章程》無關。查李鴻章閱知赫德章程的時間,是光緒五年七月初十日。然早于六月初九日,李鴻章即已致函李鳳苞,令覓購“于中國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并查明每船需銀若干、分幾批兌付及相關的船塢建設費用,以便與沈葆楨等商量核辦。[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
李鴻章光緒五年六月的購船決心,源于清廷諭旨的授意。該年初,日本廢滅琉球,“舉朝惶遽無措”,李鴻章在京陛辭慈禧時,建議購置鐵甲船,“但有二鐵甲,闖入琉球,倭必自退”。[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此議終被采納。五月十七日,清政府諭令李鴻章等:“至購買鐵艦等物,需用浩繁,應如何籌集巨款,并著該大臣等設法商辦”。[注]《清實錄》第53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13頁。這為鐵甲船購置經費的再次“議請”,提供了可能。
然而,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戶部“議請”購船經費的進程并不順利。按李鴻章原擬計劃,至少需購2只鐵甲船,連新建船塢等約需300余萬兩,時北洋只收存100余萬兩,其余不敷200余萬兩,不論是借洋債還是借戶部存款,“皆非中朝大官所愿聞”。[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九月十一日,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擬盡北洋海防專款的全部購置鐵甲船1只,“來華操演,以為始基”。[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李鴻章之意,更多的是逼迫總理衙門表態:若同意購置,則北洋海防專款已無剩余,鐵甲船購置經費的缺口、建塢經費以及蚊船日后相關費用等,需由總理衙門承攤,或者總理衙門另籌鐵甲船購置經費。九月十六日,總理衙門函復:“籌辦海防若先購鐵甲船一只,只能專顧一口,應另購他項戰艦。”[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頁。
至此,李鴻章購置鐵甲船的計劃,已陷入絕境。十月初五日,李鴻章收到李鳳苞八月初十日的信函。李鳳苞認為北洋現在購置鐵甲船,可仿照光緒二年赫德推薦的土耳其鐵甲船樣式,前往歐洲各廠考核訂購。然就李鳳苞本意來說,他反對操之過急,認為各國“紛議停造鐵甲,如可緩辦,尤為合算”,況且購置鐵甲船需同時舉辦四事:一為炮臺庇護,吳淞等處炮臺不足庇護;一為船塢修理,江南制造局船塢太淺,且離海太遠;一為快船,若鐵甲無快船輔佐,“則孤注而已”;一為水雷,有行雷可以出奇,有伏雷可以堵守,然后鐵甲船不為快船所困等。[注]《李丹崖自德國柏林發來第二十四號信》,《李星使來去信》卷4,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抄本。因為李鳳苞的建議,加之購船經費難以籌措,李鴻章于十月十七日復函總理衙門,正式停止鐵甲船的購置。[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頁。
鐵甲船購置計劃的轉機,源于清廷諭旨的促成。因為之前“預籌海防事宜,尚未定議”,清政府頗為不滿,令總理衙門、李鴻章等再“分別妥議具奏”。[注]《清實錄》第53冊,第505頁。總理衙門不得不轉變態度,令李鳳苞就近查明土耳其兩只舊鐵甲船,“如尚未出售,而價不甚昂,自應購備”。[注]總理衙門折,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一日,軍機處錄副奏折,3-9383-33。李鴻章得知船已歸英國、而英國愿以單價100萬兩轉售時,便力勸總理衙門:“既奏明購備,亦未便置而勿論”。[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頁。
前文已述,土耳其鐵甲船3年前的售價僅銀80萬兩,現在漲幅25%,且質量低下。李鳳苞回復總理衙門,稱“不能出洋交戰”。然而,李鴻章卻力主購買,認為與中國海口最為相宜,甚至辯稱李鳳苞的反對意見是“手書匆促,未暇擇言”的結果。[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頁。李鴻章之所以罔顧事實,購置3年前就被自己否決過的劣質鐵甲船,最根本的原因是遇到了一次難得的籌款良機。
其時,在李鴻章、總理衙門主持下,山東、廣東、浙江等省需籌措5只蚊船購置經費,單價15萬兩,共約75萬兩;南洋需籌措2只碰快船購置經費,單價32.5萬兩,共約65萬兩;福建省需籌措4只蚊船、2只碰快船的購置經費,共約125萬兩。[注]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第512頁;第32冊,第516頁。李鴻章建議“先其所急”,各地“未定之蚊船、碰船皆在可以稍緩之列”。[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頁。經與總理衙門反復協商,李鴻章奏準購置土耳其鐵甲船,一只歸屬福建,另一只南北洋共有,除挪用福建、南洋的“蚊、碰船之款”外,余款可從出使經費內續撥或由各方勻湊,“尚易為力”。[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頁。
不久,土耳其鐵甲船因英國“海部換人”而“作罷論”。對于鐵甲船的購置來說,經費是最大難題,而現在各省已湊撥大宗現款,“尤屬難得機會”。[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頁。李鴻章不愿放棄,奏準李鳳苞從西洋各廠中“查照新式”訂購2只鐵甲船。[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頁。
按照李鴻章原奏,所訂鐵甲船,一歸福建,一歸南北洋共有。李鴻章并不滿意。其時,在戶部和李鴻章的策劃下,兩淮鹽商捐款100萬兩,輪船招商局需歸還各省解撥的官款170余萬兩。李鴻章遂利用光緒六年初中俄伊犁交涉、沙俄兵船在太平洋時有調動的傳聞,從上述兩筆經費中各“議請”100萬兩,為北洋單獨添置2只鐵甲船。[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頁。
李鴻章的購船計劃,系按每只100萬兩估算。然南洋、福建最終解交的購船經費僅150萬兩,李鳳苞在歐洲各廠“擇善訂定”[注]《來信第五十一號》,《李星使來去信》,卷8。的2只鐵甲船卻漲至326萬余兩。光緒七年,李鴻章不得不將兩淮鹽商捐款100萬兩,“挪后就前”,另從自己掌管的淮軍軍餉等款中湊撥購船經費。[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頁。這兩只鐵甲船,即定遠號、鎮遠號。
至于第二批鐵甲船的購置計劃,終被李鴻章放棄。這與兩個因素有關。
其一,購船經費的難以籌措。在定遠、鎮遠占用了兩淮鹽商捐款100萬兩后,第二批鐵甲船的購置經費僅剩輪船招商局官款100萬兩。李鴻章于光緒七年稱:“俟二三年后伊犁償款歸清,各省財力稍寬”,再“請旨敕下總理衙門、戶部籌撥的款”。[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頁。然至光緒八年日本發起朝鮮事端時,李鴻章借機“議請”購船經費[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0冊,第83頁。,卻遭到戶部的委婉拒絕。[注]參見蔡少卿、江世榮主編:《薛福成日記》,第403頁。
其二,定遠、鎮遠號被納入北洋海軍序列。這兩只鐵甲船原歸福建、南洋,但挪用了北洋購船所需的鹽商捐款等,且系李鴻章所訂,為其收編提供了便利。至光緒八年,李鴻章已隱含此種意圖,稱定遠、鎮遠號返華后,將由自己“選將練兵,精心教練”。[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0冊,第83、83、158頁。在達到北洋海軍2只鐵甲船的既定目標后,李鴻章對續購已不再急切,僅以商量的語氣奏稱:“如有余力,亦宜添置。”[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0冊,第83、83、158頁。至光緒九年初,李鴻章借口“鐵船來華,必有精利快船輔佐巡洋,或作先鋒,或為后應”[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0冊,第83、83、158頁。,將購船的重點轉移至巡洋艦方向。
結 論
從海防思想上來說,蚊船以近海口岸的防御為目標,突出守的功能;鐵甲船以“大洋游擊”為目標,突出戰的功能。李鴻章作為傳統文人,曾錯誤地認為蚊船可與鐵甲船直接對敵,但他自同治十三年底開始,對兩者主要的海防價值已有清醒認識。赫德、李鳳苞等人對于李鴻章購置艦船的影響,更多的體現在購船時機、質量選擇,而非應否購置的判斷。
李鴻章最初選擇以口岸防御為目標的蚊船巨炮,主要是購船經費的制約。光緒元年之前,李鴻章“添置槍炮,不名一錢”,自愿推動清政府為北洋置辦蚊船。之后,雖收用北洋海防專款,但數額有限,李鴻章在“能得若干款項,再辦若干兵船”的方針下,只能購置價格相對低廉的蚊船巨炮。但這不代表李鴻章忽視鐵甲船。事實上,李鴻章自同治十三年底就已確定2只鐵甲船的建設目標,直至定遠、鎮遠訂造之后,才將購船重心轉移至鐵甲船艦隊的輔佐艦船——巡洋艦方向。
李鴻章能從蚊船守口的近海防御體系,轉向以鐵甲船為中心的大洋海軍建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擺脫了海防專款收數有限的制約,積極向上“議請”購船經費,并于光緒六年大獲成功。這也是定遠、鎮遠號鐵甲船能夠順利訂造的基礎。然在晚清財政整體困窘的情況下,李鴻章的“議請”往往需要海疆危機的刺激,以及在此基礎上清廷最高統治者的積極干預,這并非海軍建設的正常軌跡。從這個角度來說,甲午戰前10年中外交往相對和平安定,北洋海軍尚需擴充而又未能及時擴充,也就成了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