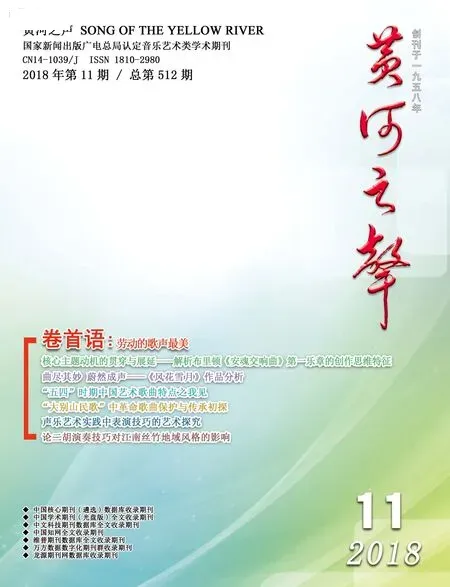淺談桂劇唱腔在民族唱法中的融合與運用*
——以桂劇戲歌《詠梅》為例
齊相月
(廣西藝術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桂劇是廣西的主要地方劇種、地方戲曲之一,起源于清嘉慶后期,流行于桂林、柳州、河池、梧州、南寧等地區北部一帶以及湖南省南部地區和廣東省西北隅,是一個擁有著300多年文化歷史的優秀劇種。桂劇屬于皮黃系統,其唱腔以“皮黃腔”(又稱“彈腔”)為主(“彈腔”屬于板腔體),即以板式和不同板式的不同結合變化來抒發人的思想感情,兼以“高腔、吹腔、昆腔、雜腔小調”為輔。其音樂伴奏分為“文場”和“武場”,采用通俗易懂的桂林方言演唱。在人類生存環境的不斷變化與社會的不斷進步發展下,桂劇經歷了在清末的形成期、民國的興盛期、建國初期的鼎盛期、20世紀50年代的挫折期和改革開放后的不斷發展變化等五個時期,桂劇于2005年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06年被第一批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眾所周知,桂劇歷史悠久,唱腔優美,劇目眾多,表演形式完整并多樣化,雖然在工業文明發展與人民生活方式改變的雙面沖擊下,桂劇的發展經歷著重大的挑戰,但“戲歌”這種新藝術形式的出現與創新為豐富桂劇體裁、弘揚桂劇文化,促進桂劇與時俱進提供了一種新鮮且有利的發展傳播方向。
一、作品簡介
《卜算子·詠梅》這首詞是我國開國領袖,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于1961年12月寫成。當時的中國正處于經濟緊張、內憂外患、百廢待興的困難時期,在三年自然災害和國際反華勢力的雙重壓力下,毛澤東因陸游筆下的梅花有感而發,一改原詩幽怨、低沉的風格,采用擬人和暗喻手法,通過“梅花”不畏嚴寒,在風雪中傲岸挺拔的品質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遇到困難時無私奉獻、堅貞不屈、積極樂觀的大無畏精神,比喻困難即將過去,美好的明天即將到來。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桂劇戲歌《詠梅》是國家一級作曲家黎承信①老師于2010年根據毛澤東的《卜算子·詠梅》這一詩詞,并融合桂劇唱腔元素創作的一首具有新形式新體裁的作品。在創作中,作曲家注入了桂劇中的“陰皮”、“南路”、“文場”等元素,并在演唱中采用了以女生獨唱為主,合唱為襯托的方式,將桂劇戲歌《詠梅》中優美又多樣化的旋律線條、細膩又不失大氣的音樂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作品分析
(一)音樂分析
在桂劇唱腔中以“彈腔”為主,它屬于皮黃系統中的板腔體,又以“高腔、吹腔、昆腔和雜腔小調”等曲牌體為輔。其中“彈腔”(又稱“南北路”)又分為“南路”(即二簧)和“北路”(即西皮)兩大系統,且南北路又各有正調和反調之分。“彈腔”的伴奏樂器為京胡,其中“南路”定弦為“—2”,常用于表現含蓄細膩的情感,其反調(陰皮)定弦為“1—5”;“北路”定弦為“—3”,常用于表現高亢激昂的情感,其反調(背弓)定弦為“2—6”。
從整體來看,戲歌《詠梅》以轉調處為界點將作品分為了兩部分,在桂劇作品中,“南路”和“陰皮”是最易表達抒發深情、含蓄的內涵情感的手法,因此在桂劇戲歌《詠梅》中黎承信老師采用了“陰皮”轉“南路”的音樂表現手法。
第一部分中主要采用了桂劇中的“陰皮”元素。音樂由自由節奏的笛聲開始,表現了梅花在寒冬中盛開的景色;演唱部分以合唱引出女生獨唱以及采用戲曲中散拍子節奏型的方式表現出人們對梅花的贊美;“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的四拍子部分與“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三拍子部分的對比巧妙體現了詩詞中“擬人化”的手法——把“梅花”比做共產黨人,也體現了桂劇“陰皮”元素中抒情性與敘事性相融合的特點。
第二部分中,其音樂表現手法由“陰皮”轉為“南路”,雖歌詞相同,但轉調后的旋律與第一部分形成對比,通過轉調的方式以及器樂上的豐富將音樂推向了高潮。并且在此部分中出現了四拍子變二拍子再變為四拍子的轉換以及音樂上的自由節奏和緊拉慢唱的形式,更加強調了作品中對通過“梅花”這一事物表達共產黨人不畏艱難,有決心迎接美好明天的樂觀態度。
(二)演唱分析
一首成功的聲樂作品,其關鍵不僅體現在詞曲的完美結合,更是要通過演唱者對作品的準確分析以及對作品完美演繹的能力來詮釋這首作品的意韻。戲歌的特色是在聲腔演唱的處理上完美地借鑒戲曲中行腔運腔的唱法,其特點是以字行腔、字正腔圓、剛柔并濟且對比變化豐富多樣,不僅吐字準確,氣口熨帖,音色也要寬廣嘹亮、純美圓潤。
第一部分中的第一段“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的旋律速度較慢,具有抒情性的特征,在演唱時要注意在胸腔和氣息的支持基礎上上將聲音集中為一點從頭腔眉心部分毫無保留地“打”出去,用流動自如的氣息和優美細膩的音色推動音樂旋律的發展,隨之進的第二段“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中的快板形式,通過歡快的旋律描繪一幅山花爛漫,一片柔和溫暖、生機盎然的畫面,喻示了共產黨人不畏艱難困苦,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樂觀態度。演唱時要注意演唱聲音的彈跳性、字與字之間的清晰性和顆粒性,要明確地區別四拍子和三拍子節奏上的強弱變化。
第二部分的旋律與第一部分形成鮮明的對比,作曲家在這一部分采用輝煌、豐富的音樂旋律,生動鮮明地表達像“梅花”一樣的中共產黨人在面對困難時積極向上、威武不屈的態度。因此在演唱時,要更加注意氣息的支撐,此時不僅需要頭腔上的統一,更需要胸腔與頭腔共鳴的配合,利用深度氣息有效地將腔體打開,為大氣磅礴的作品高潮準備充足的發揮空間。演唱整部作品是一定要注意戲歌中“以字行腔、字正腔圓”的特點,要保證咬字的清晰性與韻腔的圓潤等。
此外,戲歌《詠梅》是一首桂劇唱腔的作品,桂林方言是北京話為代表的南方官方語言,其語言聲調優美、抑揚有致,雖說話時的語調、語音、聲腔等方面同北方方言習慣有些差異,但仍保持著語義相近,語根相同,通俗易懂的特點。所謂“細節決定成敗”,因此演唱者在演唱時也要注意該作品細節上的字音變化。例如,在演唱桂劇戲歌《詠梅》時“春”字的讀音應為“cun”、“百”字讀音應為“be”、“時”字讀音應為“si”、“中”字讀音應為“zong”等。
三、表演設計
“唱、念、做、打”是戲曲演員在戲曲表演中最重要的藝術手段與基本功。雖然演唱戲歌時不需完全模仿多樣化的戲曲表演,但是良好的心理素質、舞臺表演力也是一名歌唱演員應該有的專業素養。因此,在演唱每一首聲樂作品時也要擁有將熟練的演唱技巧與從容的表演能力相結合的能力,“手、身、眼、心”的配合才能更加完美地詮釋音樂,從而增加音樂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演唱戲歌《詠梅》時,站姿上一定要擺正,仿佛自己就是不畏嚴寒、傲岸挺拔的“梅花”,要表現一名演員對音樂、對舞臺應有的尊重,切忌不可出現彎腰駝背或與音樂中所表達的內容無關的動作;眼睛要有神、靈活并放向遠方;肢體可隨著旋律的變化有節奏的擺動,通過肢體的自由擺動表現相互“梅花”剛柔并存的特點,從而準確地表現出音樂作品中的思想內涵。
四、結語
總之,“戲歌”的出現是長久以來傳統戲曲與民族聲樂在時代的發展與人民的審美變化、提高的歷史背景下不斷交流碰撞產生的一朵藝術奇葩。桂劇戲歌《詠梅》的創作體現了桂劇唱腔與民族唱法在嘗試融合的道路中都迎來了多元化的發展,中國民族聲樂的發展通過桂劇唱腔特色的融入也帶給了中國傳統音樂中所獨有的美學思想。我們作為一名聲樂實踐者與發展者,即是要通過不斷地實踐和創新來發展中國民族聲樂,在迎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發展的道路中,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有社會價值的元素不斷注入到各種藝術形式里,在人民群眾的生活中傳播,滋養著我們的文化與生活。■
注釋:
① 黎承信:1944年生,廣西河池人。國家一級作曲,從事戲劇音樂創作五十余年,為桂劇寫了八十余個劇目的音樂唱腔。音樂創作涉獵廣,寫過“音樂舞蹈劇”、“歌舞雜技劇”、“音樂劇”,與沈桂芳合作新創了“仫佬劇”。同時也作過漁鼓、彩調、文場、京劇及戲歌的創作。代表作有:桂劇《大儒還鄉》、《泥馬淚》、《烈火南關》、《靈渠長歌》、《人面桃花》等大型劇目。榮獲了國家“文華音樂創作獎”。在廣西九次劇展中都有作品參加并連續九屆獲得“優秀作曲獎”。精心作曲的桂劇《大儒還鄉》入選國家十大精品劇目(排名第二),該劇并榮獲國家“文華劇目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區政府銅鼓獎和桂花金獎等,是廣西獲獎最高最多最全的劇目。《風采壯妹》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1987年作曲并指揮的桂劇《泥馬淚》入京參加國際戲劇研討會展演,外國專家高度贊譽:“《泥馬淚》音樂可與意大利歌劇媲美!”并在中央電臺錄制了全部音樂唱腔。1975年中央唱片社出版了他兩個劇目的音樂唱腔國內外發行。多年來中央電臺和廣西電臺播放了他大量的音樂作品,是廣西戲劇界實力派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