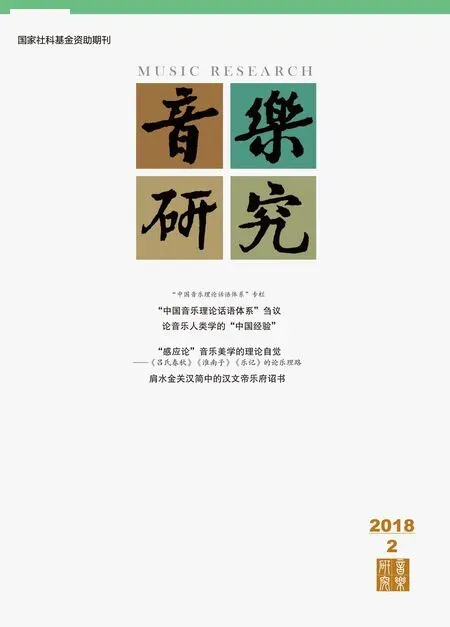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
文◎楊善武
對于中國音樂研究來說,話語構建的過程就是對中國音樂本質特征及規律的認識過程,也就是進行中國音樂理論體系建設的過程。按照“三個來源”及“兩個原則”進行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借鑒西方建設他們自己音樂理論體系的有益經驗,切實避免兩種傾向,經過系統深入研究真正建立起一套扎實可靠的理論體系,到那時才可以說我們具有了中國音樂自己的話語,獲得了對于中國音樂的話語權。當我們對自己的音樂具有了話語與話語權,也就有可能在世界學界贏得尊重、獲得話語權。
本文所講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①本文根據筆者于2017年“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首屆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談的是話語問題,但又是圍繞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建設講的。所以,這個論題也可以理解為,運用何種話語來構建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問題。
我們不少學者早已經指出了,中國音樂客觀地存在一套自己的體系,并由此確立了建立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目標任務。②董維松、沈洽明確指出,“我們的傳統音樂是有自己的體系的”,這種體系“在世界上具有獨特地位”。我們“基本的目標十分清楚”,就是要“建立我們中華民族的音樂理論體系”。薛藝兵也指出“中國傳統音樂歷史悠久,自成體系”,研究的目標是“建立中國傳統音樂的理論體系”,指出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建立不論“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具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以上分別見董維松、沈洽《民族音樂學問題》,《音樂研究》1982年第4期,第35—36頁;薛藝兵《民族音樂學與中國民族音樂理論》,《人民音樂》1988年第4期,第25頁。我們要建立的中國音樂理論體系,實際上是對中國音樂客觀存在之體系的理論反映和話語表達。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建立既有賴于對中國音樂歷史與現實傳存的研究認識,也有賴于明確的話語表達。這樣,我們就有必要構建一套科學、嚴密而適合的話語系統。這其中一系列術語概念,就像《中國音樂詞典》中各詞語條目所顯示的那樣,涉及的都是對中國音樂一個個具體特征與規律的認識,直接指向了對于整個中國音樂本質特征的把握。這些術語概念恰恰是中國音樂理論體系話語構建中最基礎、最重要,也是最薄弱的環節,必須一一把它搞清楚。
從近代以來中國音樂研究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有三個方面的來源。一個是來自音樂歷史文獻的表達與民間音樂的用語,一個是來自對中國音樂歷史與現存實踐的研究,還有一個來自外來的主要是西方音樂理論的話語。我們既然談的是中國音樂理論體系,那么其話語構建,就首先依賴于對傳統話語的研究。傳統話語是中國音樂理論體系最基本的話語,需要從歷史理論與現存實踐中去發掘。對于傳統話語的發掘我感到有兩點需要注意:
一是要厘清傳統話語的實質內涵,并做出明確的界定。只有把一個個概念的內涵搞清楚了,才能自覺而有效地加以使用。我國先秦時期就提出的“旋宮”,一般都把它與現代的轉調相比擬,似乎旋宮就是一個轉調的概念。對于旋宮,《中國音樂詞典》有個定義“十二律輪流作為宮音,以構成不同……的調高”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音樂詞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頁。,這是根據《禮記·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做出的。按這個定義,旋宮可以說是對不同調高的明確。那么,這些調高在具體音樂中又是怎樣的呢?從古代理論中不難看出,它實際是指不同調高的分別使用,不同調高之間并不發生直接的轉接關系,也就是說它不是我們所理解的轉調。類似現代轉調的概念我國古代稱作“犯調”,那是在唐代以后才產生的。④楊善武《旋宮、轉調與犯調》,《人民音樂》2014年9月號,第50—51頁。另見筆者《史學創新與傳統樂學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4頁。
二要注意的是從術語與概念的關系上,把一些傳統話語分辨清楚。古代的一個“宮”字,就有三種不同的含義:可以是宮音,可以是宮調式,也可以是以宮音為代表的調高。同樣一個“黃鐘宮”,在古代理論中可能是指黃鐘為宮的這個音,也可能是指以黃鐘宮音為主音的調,還可能是指以黃鐘宮音為代表的七音之整體高度的均。對這三種不同的含義,在話語研究中就要分辨清楚其具體表達的是哪一種。如果我們對于這些術語概念不能做到明確區分、準確領會,便有可能產生對傳統話語理解上的錯誤,并有可能導致理論認識上的問題。
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除了對傳統話語的研究以外,也需要對西方理論的借鑒吸收。談到對西方理論的借鑒吸收,也就涉及中西音樂文化關系問題,既顯得有些敏感,但又必須把它處理好。中國音樂的歷史發展從來不拒絕一切外來的適合的東西,近代以來的中國音樂理論研究就吸收使用有不少西方理論的術語。對此,我們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對于西方理論我們應有的態度是,立足中華文化的根基,為了中國音樂的傳承發展,而予以批判借鑒、合理吸收。近代以來我們從西方音樂理論所借鑒吸收的不少有益的東西,實際上就有力推動了我們對于中國音樂歷史及傳統音樂的研究認識,今后仍然需要借鑒吸收,以推動我們的理論體系建設。
不同文化之間從來都是取長補短、相互促進的。從已有研究看,我們所借鑒吸收的外來術語及概念,大都是抽象概括類的。這類抽象概括的概念,正是西方理論的優長之處,是我們所欠缺的,是我們在建設自己的理論體系中所需要的。使用這類抽象概念,可以更好地反映和揭示事物的本質。西方的音階、調式概念我們原本沒有,中國文獻中使用的是五聲、七音、起調畢曲之類。所謂五聲、七音,從詞語表面看是五個音、七個音,但又不是隨意的五個音、七個音,而是指音階中的七個音、音階中的核心五音。我們運用音階這個抽象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把傳統所用五聲、七音的實質理解清楚。
除了對傳統話語的研究與對西方理論的借鑒吸收,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更需要根據研究認識加以提煉創立。這個提煉創立不是隨意的,而是基于對中國音樂本質特征及規律的準確認知與系統把握,在對傳統話語研究及對西方理論借鑒吸收基礎上,根據理論體系建設的需要所進行的必要的創新。近代以來,中國音樂研究實際上已經創用了不少新的術語概念與新的理論表達。對于中國音樂所屬的音樂體系,有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就將其概括為“以五聲音階及以五聲為骨干構成旋律”的五聲性體系⑤以下有關五聲性體系的論述參見筆者《黎英海五聲綜合調式理論》一文,載《傳統宮調與樂學規律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301頁。;作為五聲性體系有其不同于西方七聲體系的特殊思維方法,這就是先秦時期已經指明的“以奉五聲”,亦即古代文獻中不斷提及的、傳統音樂實踐中具體反映的以五聲為核心(骨干)的五聲性思維方法。五聲性思維方法有其具體的特殊的表現形態,亦即五聲性形態,五聲性形態在具體音樂中有其豐富多樣的旋法,極具特色的發展變化的手法。對于這種五聲性音樂的認識,有其不同于西方音樂的方法論,亦即五聲性分析方法。這些都是近代以來中國音樂學者在長期不斷的探索研究中所獲得的極具創新性的理論成果與話語成果,正是這些成果奠定了中國音樂理論體系建設的堅實基礎。
上面談了中國音樂理論話語構建的三個來源,這三個來源的構建還必須遵循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要能夠準確反映中國音樂的本質特征與規律;一個是要能夠有效表達并構成統一完整的理論體系。這里的第一個原則是對體系實質內容的要求,第二個是對體系自身規范的要求。第一個原則是根本性的必須首先做到的,第二個原則的貫徹以第一個原則為前提。下面就此舉兩個例子加以分析。
第一個是“音聲”。我們學界好多學者都在文論著述中用到“音聲”一詞,而且這個音聲還比較重要,是把它作為一個核心概念來用的。那么什么是音聲呢?一般定義說它是涵蓋非樂音、非樂聲在內的一個概念,好像除了樂音、樂聲,非樂音、非樂聲也都包括在內了,這樣顯得涵蓋面很廣、很全面、很周到,也很符合音樂的實際,但恰恰是這一點模糊了音樂的本質。音樂的本質并不在于非樂音、非樂聲,而在于樂音、樂聲。我國古代音樂文獻所大量記載的五聲、七音、十二律,一個個都是樂音,不是非樂音;三分損益的計算,無論涉及六十律還是三百六十律,其中每一律都是樂音,不是非樂音。雖然我國古代音樂和現存傳統音樂中所講的都是樂音、樂聲,但又不排斥非樂音、非樂聲,而是在樂音、樂聲的運用中有機地結合了非樂音、非樂聲。也就是說,中國音樂的本質是樂音、樂聲,而不是非樂音、非樂聲。在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話語構建中,這個音樂本質的問題必須要搞清楚。
另一個要分析的是“音腔”。沈洽先生提出了音腔的概念,什么是音腔呢?這是與西方相比較來講的,好像西方音樂中使用的一個個都是直音,都是單個的音,我們中國音樂中的音都是帶腔的,是帶腔的音,把這個作為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一個根本區別。那么我們的音樂,包括古代音樂與現存傳統音樂是不是這樣呢?就我對傳統音樂的了解和對古代音樂文獻的研究,實際上我們的音樂首先強調的是音的明確,在音的基礎上再談腔的問題。在所有戲曲音樂中,音與腔都是相對區分的兩個概念,而沒有音與腔合一的音腔概念。那么為什么會提出音腔的概念呢?從沈洽先生的文章里看到,他的老師于會泳曾經布置了一個任務,要他研究潤腔。⑥沈洽《民族音樂學在中國》,《中國音樂學》1996年第3期,第11頁。由此我看出,所謂音腔其實際上指的是潤腔。潤腔主要是在音樂表演上的一個范疇,它跟構成音樂的作為音階中的一個一個的音并不沖突,只不過是在音的明確基礎上再運用各種演奏、演唱的處理使音樂表現得更好些罷了。音與腔是中國音樂中兩個相對的不同范疇的概念,所謂音腔是不是把這兩個概念沒搞清楚,而彼此弄混了呢?當然,把音腔概念作為一個出發點,以其為根本而構建一個理論體系是可以的,但是這樣構建的體系卻不能說是中國音樂客觀體系的準確反映,只能說是一個主觀的產物,這樣的體系并不是我們進行中國音樂研究、進行話語構建所要達到的理論目標。
近十余年來我一直在進行中國音樂基本理論的探索研究,下面是我就中國傳統音樂基礎理論所設置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十二個部分。
十二律體系;三種律制;五聲性音階及調式;均、宮、調概念;旋宮與犯調;調名法及樂調系統;節拍、板眼及板式;減字譜與唐琵琶譜;俗字譜與工尺譜;五聲性旋律;曲牌體與板腔體;“八音”之器。
在這十二個部分中,我力圖將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現存傳統音樂實踐所涉及的律(音律)、調(宮調)、拍(節拍、節奏)、譜(樂譜)、曲(旋律)、體(結構)、器(樂器、樂隊)等方面的理論加以系統的歸納總結。⑦楊善武《關于中國傳統音樂基礎理論的體系建構》,《交響》2009年第3期,第44頁。另見筆者《史學創新與傳統樂學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頁。具體研究中,我也在努力依照上述三個來源、遵循兩個原則,把基本理論體系作為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將中國音樂客觀體系中最基本的部分以適合的話語明確地表達出來。
經過研究實踐我深深感到,話語問題不單是一個如何表達的問題,實質上還是一個表達什么的問題,表達得怎么樣的問題。對于中國音樂研究來說,話語構建的過程就是對中國音樂本質特征及規律的認識過程,話語構建的過程也就是在具體實施中國音樂理論體系建設的過程,一句話,話語構建也就是在進行中國音樂理論體系的建設。
提起中國音樂理論體系建設,我們需要好好學習西方的經驗:不是學習西方研究非西方民族音樂的經驗,而是要學習西方研究他們自己的音樂、建設他們自己音樂理論體系的有益經驗。西方音樂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扎實可靠的理論,像基本理論系統、技術理論系統、專業教學系統等,這些都在我們的院校內使用著,其不僅扎實可靠,而且極具操作性,有很強的實效性。但這種理論系統畢竟是西方音樂的反映,而跟我們的音樂、我們的傳統有很大的不適應性。為了中國音樂的傳承發展,就有必要建立起一套像西方那樣扎實可靠,但又是屬于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為了保證這種理論體系構建的成功,在目前要特別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一個是按照文化背景決定論將中國音樂虛化、淡化及至實質取消的傾向。一個是將中西音樂對立起來、將對中國音樂的認知推向絕對與極端的傾向。⑧楊善武《民族音樂學某些觀念的片面絕對及后現代發展的極端傾向》,《音樂研究》2015年第5期,第72頁。當我們切實避免了這兩種傾向,通過系統深入研究真正建立起一套扎實可靠的理論體系,到那個時候才可以說,我們形成了中國音樂自己的話語,獲得了對于中國音樂的話語權。而當我們對于中國音樂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話語系統、對自己的音樂具有了話語權的時候,那么我們才有可能在世界學界贏得尊重、獲得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