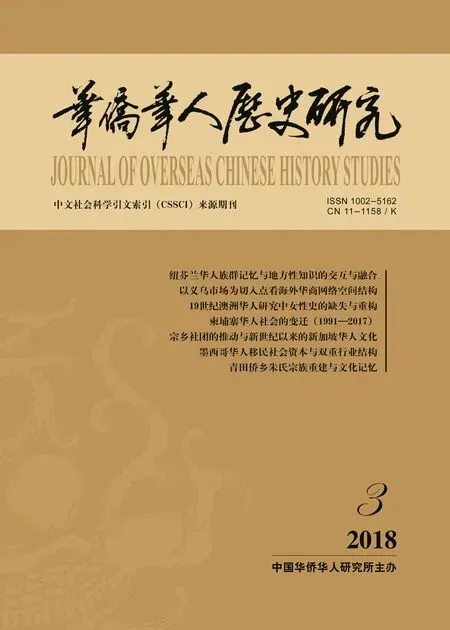邊境戰(zhàn)爭后印度拘禁華僑與中國政府的應對新探*
朱鵬,賈海濤
(1.暨南大學 歷史系,廣州 510632;2.暨南大學 中印比較研究所,廣州 510632)
1962年11月20日,中印邊境戰(zhàn)爭即將停火之際,印度當局突然開始大規(guī)模圍捕居住在其境內(nèi)的華僑①本文的華僑既包括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也包括加入印度國籍的華人。為行文簡便及與當時的稱謂相一致,統(tǒng)稱為“華僑”。,并將部分難僑解送至一千多英里外的迪奧利(Deoli)集中營長期關押。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一方面利用兩國外交關系尚未斷絕的有利條件,積極與印方展開交涉;另一方面迅速組織人力物力,前往印度接運難僑回國。不過,由于印度當局蠻橫堅持按照其確定的數(shù)量、指定的地點和選定的人員“遣返”被拘難僑,導致中國政府的救助行動困難重重,最終未竟全功,大批難僑被迫長期滯留印度。印度當局為什么要圍捕和拘禁華僑并阻撓中國政府救助難僑?過去50多年間,不僅中印官方均對此提及不多,而且兩國學術(shù)界也鮮有專門的研究成果。②從學術(shù)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僅在一些論著和論文中對此略有提及,如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張敏秋:《中印關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趙蔚文:《印中關系風云錄1949—1999》,時事出版社,2000年;尚勸余:《尼赫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關系(1947—196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王宏緯:《喜馬拉雅山情結(jié):中印關系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周衛(wèi)平:《百年中印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張秀明:《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社會的變遷》,《華僑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趙毅:《印度尼赫魯政府排華反華運動評析》,《西部發(fā)展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在與之相關的學術(shù)研究中,研究者們普遍傾向于將印度當局的行為視作其自西藏叛亂以來反華排華活動的延續(xù)。③例如:山下清海在《印度的華人社會與唐人街——以加爾各答為中心》一文中認為,拘禁華僑是“印度當局在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后采取的排華政策”的具體表現(xiàn);周衛(wèi)平在《百年中印關系》一書中認為,邊境戰(zhàn)爭失利使印度當局惱羞成怒,加大了反華排華的力度,采取這種“違反國際關系準則的瘋狂措施”;趙毅在《印度尼赫魯政府排華反華運動評析》中也認為,“中印邊境之戰(zhàn)把印度國內(nèi)反華浪潮推向了高潮”,等等。事實上,尼赫魯政府戰(zhàn)后在華僑問題上的種種作為,并非簡單的排華,而是具有十分復雜的原因和目的。有鑒于此,本文將嘗試利用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和印度外交部編撰的《白皮書》《外事檔案》以及其它文獻,深入探究印度圍捕和拘禁華僑的真實意圖,詳細梳理中國政府救助被拘難僑的具體過程,為相關學術(shù)研究和實踐工作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戰(zhàn)前印度的反華排華活動
中印互為鄰邦,兩國人民往來自古不絕,中國人定居印度者早既有之。至20世紀40年代的鼎盛時期,印度華僑總數(shù)一度達到6萬多人,其中漢族僑胞4萬多人。[1]中印戰(zhàn)爭前,印度華僑的身份比較復雜,既有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也有取得印度國籍的華人;按照民族劃分,大致可分為漢族華僑和以藏族為主的少數(shù)民族華僑;按照所持政治立場劃分,不僅有大量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的愛國僑胞,也有不少國民黨殘余政權(quán)的支持者,還有追隨達賴集團的所謂“流亡藏人”;按照來源地劃分,少數(shù)民族華僑主要來自國內(nèi)藏區(qū),漢族華僑則主要來自廣東、湖北和山東等省。在中印關系惡化之前,印度對華僑的管理一直較為寬松,并沒有因他們的國籍、種族或政治立場不同而加以區(qū)別對待。有些華僑盡管出于各種原因沒有取得新中國頒發(fā)的護照或其他合法身份證明,但也能在印度境內(nèi)正常生存和發(fā)展。
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中印關系的惡化,印度對華僑的態(tài)度逐漸發(fā)生了轉(zhuǎn)變。1959年3月西藏叛亂發(fā)生后,印度當局高調(diào)同情并大肆收留叛亂分子。在印度一些媒體的報道中,中國政府的平叛行動也被描繪為“采取強盜行徑和實行帝國主義”。[2]大量失實的信息迅速激起了印度民間的反華情緒,在印度當局的縱容乃至授意下,4—9月間,印度國內(nèi)連續(xù)掀起兩次大規(guī)模的反華浪潮。在此過程中,認同新中國的漢族華僑首當其沖、深受其害,而那些親臺反共者及“流亡藏人”卻能夠置身事外、安然無恙。在這一時期印度的官方文件中,印度當局對于認同新中國的漢族華僑,無論是否加入印籍,一概稱為“中國公民”(Chinese nationals);對于那些支持國民黨殘余政權(quán),拒不認同新中國,甚至伙同印度敵對勢力等從事反華分裂活動的華僑,[3]則使用“中國僑民”(overseas Chinese)以示區(qū)別;[4]對于藏族僑胞和“流亡藏人”,更是別有用心地以“藏人”(Tibetan)或者“藏人難民”(Tibetan refugees)稱之,以表示其對“藏獨”的支持。[5]
1959年8月“朗久事件”發(fā)生后,印度當局開始以發(fā)現(xiàn)華僑從事“間諜活動”和“反印活動”為由,對華僑進行甄別和登記,甚至剝奪了一些華人的國籍,迫使許多人離開印度。1960年2月,噶倫堡、加爾各答的地方當局先后向旅居當?shù)氐牟糠秩A僑發(fā)出通知,勒令其在三個月內(nèi)離境。此后不久,印度又將驅(qū)逐范圍擴大至中資機構(gòu)的工作人員。在印度當局有針對性的迫害下,至1962年,漢族華僑的數(shù)量由高峰時期的4萬余人驟降至1.6萬人。[6]
二、戰(zhàn)后印度圍捕和拘禁華僑
中印邊境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印度當局一改此前排擠、迫害甚至強制驅(qū)離的做法,轉(zhuǎn)而限制乃至禁止華僑離境。1962年10月26日,印度頒布了專門針對華人的《外國人法(實施和補充)條例》。按照該條例的規(guī)定,只要父母或祖父母一方曾是印度交戰(zhàn)國的公民,即使已經(jīng)取得印度國籍,也被視為“外國人”。[7]11月2日,加爾各答地方當局發(fā)布通知,對屬于“外國人”的華僑實施最嚴格的“保安限制”,勒令他們“不得離開這個城市或不得離開家里過夜”。[8]華僑聚居的加爾各答塔壩區(qū)受到當?shù)剀娋膰烂芊怄i,華僑“出門超過封鎖線的就要被判刑或罰款”,他們的企業(yè)也被作為“敵產(chǎn)”查封或沒收,致使該地逐漸陷入“一片凋零,成了一個變相的集中營”。[9]
11月20日,印度當局突然在臨近前線的阿薩姆邦和西孟加拉邦大規(guī)模圍捕和平守法的華僑。21日,中國政府主動宣布停火撤軍后,印度當局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抓捕的范圍。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印度當局就拘捕了三千多名華僑。
與以往的反華排華活動相比,印度當局此次圍捕和拘禁華僑有幾個顯著特點:一是時間特殊、行動迅速。邊境戰(zhàn)爭前印度驅(qū)逐華僑一般都會提前發(fā)布通知,明確申訴或離境的最后期限,最短也有幾天的時間。印度此輪圍捕華僑是在印軍全面潰敗之后驟然動手,提前沒有任何通告,就在短期內(nèi)抓捕了數(shù)千人。二是強調(diào)數(shù)量,不關注“質(zhì)量”。此前印度逮捕、驅(qū)逐華僑大多選擇有一定影響力的重要人物或者青壯年男性。這一輪的行動中印度當局卻不分男女老幼、不辨國籍,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圍捕華僑,直到拘押人數(shù)達到其預設的數(shù)額方才罷手。三是意在扣押,而非驅(qū)逐。邊境戰(zhàn)爭前印度排華活動都是以驅(qū)離為主,有些華僑行動稍有遲緩,就會被強制押解出境。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印度當局非但不準華僑擅自離境,反而將他們中的很多人長期扣押起來。對于被拘者既不審判,也不明確罪名和刑期,導致他們在無過錯、無罪名的情況下被關押數(shù)月乃至數(shù)年之久。
三、印度拘禁華僑的原因和目的
從中、印、美等國已公開的檔案中可以看到,印度當局之所以在軍事潰敗后大規(guī)模圍捕并長時間拘禁華僑,主要源于其對中印邊境戰(zhàn)爭性質(zhì)和戰(zhàn)后國際國內(nèi)形勢的認識與判斷,其目的則是要以華僑為人質(zhì),換取戰(zhàn)俘問題上的所謂“對等”,維護國家的“體面、尊嚴和自尊”,[10]同時,也向印度國內(nèi)展示其對華強硬姿態(tài)、安撫各方的不滿情緒。
印度當局認為,這場戰(zhàn)爭是中國用突然襲擊和“人海”戰(zhàn)術(shù)實施的“侵略”。因此,當中國軍隊攻破藏南要地瓦弄和邦迪拉后,印度國內(nèi)陷入一片恐慌,總理尼赫魯甚至以為整個阿薩姆邦很快就會被中國軍隊攻陷。[11]為應對中國軍隊“全面入侵”的燃眉之急,印度當局一方面在臨近前線地區(qū)大規(guī)模圍捕華僑,企圖以之為人質(zhì)要挾中國政府、遲滯中國軍隊的進攻;另一方面緊急向西方國家求救,請求美國立即派遣12個中隊的超音速戰(zhàn)斗機和2個中隊的B-47轟炸機馳援印軍。[12]
11月20日,肯尼迪收到尼赫魯?shù)那笾藕螅芸毂銢Q定派遣一個以助理國務卿哈里曼為首的高級代表團前往印度商討軍事援助的具體事宜。同時,美國緊急調(diào)派了12架C-130大型運輸機,幫助印軍向前線運送增援部隊和物資,并調(diào)遣第七艦隊的海空力量前往孟加拉灣支援印度。[13]12月10日,肯尼迪批準向印度提供6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14]20日,肯尼迪在拿騷會談中成功說服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使其同意按照50:50的份額共同援助印度1.2億美元,幫助其建設6個山地師。[15]此外,在美國的協(xié)調(diào)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相繼表示將向印度提供軍事和經(jīng)濟援助。
在西方國家向其施以援助的同時,蘇聯(lián)也在積極拉攏印度。蘇共二十大后,隨著中蘇分歧的加劇,蘇聯(lián)就已逐步加大了對印度的扶持力度。[16]邊境戰(zhàn)爭期間,蘇聯(lián)雖然曾基于對抗美國的需要而短暫支持過中國,但由于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并沒有因此而彌合,古巴導彈危機緩和后蘇聯(lián)便迅速改變了立場,公開同情印度、指責中國。[17]11月14日,蘇聯(lián)決定恢復對印軍售。20日,蘇聯(lián)與印度簽署《航海運輸協(xié)定》。[18]12月4日,蘇聯(lián)給予印度明確答復,將幫助其建設一條飛機生產(chǎn)線,并在短期內(nèi)交付其此前訂購的新型米格戰(zhàn)斗機。[19]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fā)表演講,指責中國“入侵”印度,挑起中印戰(zhàn)爭。在蘇聯(lián)的授意乃至直接帶領下,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等國的共產(chǎn)主義政黨紛紛指名攻擊中國共產(chǎn)黨。[20]
除美、蘇兩大集團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對印度的立場表示理解和支持。亞洲的伊朗、約旦、泰國、菲律賓等國和非洲的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埃及)、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等國均公開支持印度,部分國家還點名批評了中國政府。[21]12月10日—12日,錫蘭、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阿聯(lián)、加納在科倫坡召開亞非六國會議,討論和調(diào)節(jié)中印爭端,通過了有利于印度的“科倫坡建議”。
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和支持使印度當局逐漸擺脫了軍事潰敗后的沮喪狀態(tài),自信心再度膨脹起來。但另一方面,來自國內(nèi)的質(zhì)疑和批評卻使其倍感壓力。印軍在前線一敗涂地以及近4千人被俘的事實使尼赫魯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各種質(zhì)疑和批評紛至沓來。11月19日,當尼赫魯在人民院宣布瓦弄和色拉失守后,[22]“從反對黨席位上爆發(fā)了憤怒的質(zhì)問和訓斥”。[23]同日,尼赫魯在對全國的廣播講話中稱:“我很理解我們阿薩姆邦的朋友們現(xiàn)在的心情”,“我希望未來能夠經(jīng)常與你們保持聯(lián)系”,“我們將向美國和英國求助”。[24]尼赫魯?shù)闹v話不僅遭到了反對黨的嚴厲批評,指責其企圖拋棄阿薩姆邦,而且也使其支持者懷疑印度將背棄“不結(jié)盟”的中立政策,卷入東西方兩大集團的對抗之中。尼赫魯?shù)膫€人威望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感都出現(xiàn)了嚴重的下滑,印度國內(nèi)一度流傳出“克里希納·梅農(nóng)(前國防部長—筆者注)將取代尼赫魯成為政府首腦”的謠言。[25]
不僅如此,國大黨內(nèi)部對尼赫魯?shù)呐u也越來越尖銳。總統(tǒng)拉達克里希南公開表示,對華戰(zhàn)爭的主要教訓就是尼赫魯及其團隊犯了“嚴重的錯誤”。尼赫魯曾經(jīng)的親信、邊境戰(zhàn)爭的前線指揮官考爾被解職后也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尼赫魯,批評他“把中國當作印度的朋友”,在處理中印邊界爭端的過程中獨斷專行、一錯再錯,最終招致災難性的后果。[26]
讓尼赫魯及其領導的政府更為被動的是,明顯對印度有利的“科倫坡建議”在議會內(nèi)卻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反對者認為,科倫坡會議六國沒有指出誰是侵略者、誰是受害者,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不予譴責,“這個建議傷害了印度的榮譽、主權(quán)和領土完整”,“在科倫坡建議的基礎上與中國談判就相當于向中國投降”。[27]為此,尼赫魯不得不在人民院和聯(lián)邦院中一再聲明:如果中國不恢復1962年9月8日的實控狀態(tài),印度絕不與其直接談判。[28]
在國際援助和國內(nèi)壓力的雙重作用下,印度當局戰(zhàn)后的對華政策日趨強硬,在兩國交涉中更加強調(diào)印度的“體面、尊嚴和自尊”。11月,印度外交部連續(xù)發(fā)布三個聲明,一再要求中國軍隊撤至其主張的1962年9月8日實控線以內(nèi),并聲稱將“利用友邦供應武器和裝備的援助”來對抗中國。[29]12月10日,尼赫魯在人民院的演講中宣稱,即使付出最大的努力和犧牲,也要在與中國的斗爭中贏得勝利。[30]不過,由于中國作為戰(zhàn)勝方已經(jīng)主動宣布停火撤軍,印度無論從軍隊士氣還是從道義上,均不適合再次向中國發(fā)動進攻。印度當局認為,最具可操作性、最有主動權(quán)的手段就是利用華僑做文章,不僅能以其為人質(zhì),要挾中國政府在邊界爭端中做出妥協(xié)讓步,而且能“以華僑抵印被俘人員”,[31]維護國家的“體面、尊嚴和自尊”,安撫國內(nèi)上下的不滿情緒。
在具體實施中,印度當局刻意從以下幾個方面彰顯其強硬姿態(tài):一是繼續(xù)圍捕華僑,使被拘難僑的總量不少于被俘印軍的人數(shù)。邊境戰(zhàn)爭中,印軍共有3944名官兵被俘,卻“沒有任何中國俘虜”。[32]為實現(xiàn)“對等”,印度當局在中國主動停火撤軍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仍不停抓捕華僑。雖然無從知道被拘難僑的確切數(shù)據(jù),但是從歸國難僑反映的情況和印度媒體發(fā)布的消息可以判斷,[33]印度各地拘押的華僑總數(shù)應不小于被俘印軍的規(guī)模。二是制造困難,使難僑返華的時間不早于中國遣返戰(zhàn)俘的日期。印度當局一方面通過在集中營制造暴力事件、沒收財產(chǎn)、拆散家庭等手段逼迫被拘華僑放棄回國訴求,另一方面遲遲不向中方提交擬釋放的難僑名單,并阻撓中國使館為難僑辦理回國登記,直至中國開始遣返印軍戰(zhàn)俘兩天,才允許第一批難僑返華。1963年5月25日,第二批難僑啟程時,中國已將全部印俘遣返完畢。三是拒絕中國接回全部難僑的正當要求,使返華難僑的數(shù)量不多于中國遣返的印俘人數(shù)。1962年12月,中國釋放716名傷病員和15名協(xié)助看管印軍被繳武器的戰(zhàn)俘以后,滯留的印俘尚有3213名。印度當局便以此為參照,限制中國接僑的人數(shù),導致最終僅有2394名被拘華僑獲釋離境,大量難僑被迫長期滯留印度。
四、中國政府大力救助被拘難僑
中國政府對印度當局圍捕和拘禁華僑的行為高度重視,外交部及駐印使館、華僑事務委員會、交通部等單位為營救受難僑胞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終接回了部分難僑,并使其得到妥善安置。
(一)敦促印度釋放被拘難僑
1962年11月23日,中國政府得知印度當局大規(guī)模圍捕華僑后迅速作出反應,立即指示駐印使館向印度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24日,中國外交部正式向印度發(fā)出照會,“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釋放全部被拘押的華僑,停止對華僑的一切迫害,切實保障華僑生命、財產(chǎn)的安全”。[34]其后,駐印使館又多次與印度有關部門交涉,敦促其立即停止圍捕華僑的行動。28日,周恩來總理在致尼赫魯?shù)男胖兄赋鱿M《炔灰尅斑@種不正常的情況……再繼續(xù)下去”。[35]12月10日,中國駐印臨時代辦陳肇源親赴印度外交部交涉,當面要求印方“提供華僑情況及安排訪問被拘華僑”。但印方中國司司長梅農(nóng)卻故意將被拘華僑同印軍戰(zhàn)俘相提并論,僅表示“印度愿意在對等的基礎上通過國際紅十字會交換關于這些人的情況”。在雙方交涉中,“印方以華僑抵印被俘人員的企圖已極明顯”。[36]中國政府了解印度當局的真實意圖后,隨即指示駐印使館,要“充分利用印方并未同我絕交或宣戰(zhàn),中印仍有外交關系的有利有理條件對印方展開斗爭以保護華僑利益”。[37]同時,中國政府還準備了2000個裝有食品和衣物的包裹,通過印度紅十字會轉(zhuǎn)交給被拘難僑,以解決他們的生存之需。
12月18日,中國外交部再次向印度發(fā)出照會,直截了當?shù)亍百|(zhì)問印度當局,印度是不是打算利用大批拘禁華僑作為人質(zhì)來對中國政府進行訛詐”?[38]并正式要求印度當局“立即停止迫害華僑,釋放全部被逮捕和拘禁的華僑,歸還他們的財產(chǎn),賠償他們所受的損失;立即提供被捕華僑的人數(shù)、名單和關押地點,并且對中國大使館提出的探視和其他合理要求提供便利”;“對愿意返回祖國的華僑,保證他們自由離境,并且允許他們攜帶資金和財產(chǎn);對愿意繼續(xù)在印度居留的華僑,保證他們的人身自由和生命、財產(chǎn)的安全,不進行任何歧視”;“對中國政府接運難僑回國的措施給予應有的合作和必要的便利”。[39]其后,中國外交部又多次照會印度當局,強烈要求印方停止迫害華僑并允許難僑回國。在此期間,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也對外發(fā)表談話,為解救被拘華僑向印度當局施加壓力。[40]
(二)派船接運難僑回國及安置歸國難僑
在中國政府的多番抗議和催促之下,1963年3月7日印度勉強同意“遣返”約2400名“自愿回國”的難僑。[41]盡管這個人數(shù)與被拘華僑的總數(shù)還有很大差距,但中國政府認為不宜與其糾纏,應把握機會盡快接回這些難僑,然后再爭取問題的徹底解決。因此,中國政府一方面繼續(xù)敦促印方提供被拘華僑的名單并允許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前往探視,另一方面就派船接僑的細節(jié)于3月14日向印方提出了六點要求,以確保這些難僑能夠順利回國。[42]經(jīng)過多輪磋商,最終確定了接僑的具體時間、地點和批次。為防止節(jié)外生枝,中國政府立即決定派“光華輪”和“新華輪”次日(3月27日)就前往印度當局指定的馬德拉斯港接僑。[43]
不過,印度當局并不愿讓中國政府順利接回難僑。3月26日,中印磋商甫一結(jié)束,印度當局即在對華照會中指責“中國政府扣押三千多名印軍戰(zhàn)俘作為人質(zhì)”。[44]29日,印度當局再次批評中國違反日內(nèi)瓦公約,扣押印軍戰(zhàn)俘作為“人質(zhì)”,[45]并以此為借口阻撓中國政府救助難僑。同日,為逼迫被拘華僑放棄回國,印度當局勾結(jié)臺灣特務在集中營制造了有組織毆打難僑的嚴重事件,導致80多名難僑不同程度受傷,100多人被關進特設監(jiān)獄。[46]事件發(fā)生后,印度當局不僅拒絕調(diào)查和懲辦直接行兇者,而且以部分難僑在集中營實施暴力犯罪為由,扣留了80位已在首批釋放名單上的難僑。另外,印度當局還以“不得回家處理或收集他們的資產(chǎn)”、扣留家屬等手段,[47]阻撓難僑回國。對此,中國政府向印方表達了強烈的抗議。[48]4月9日,中國政府向印方提出六項要求,著重強調(diào)應按照既定的人數(shù)和名單實施交接,不得隨意刪減人數(shù)。[49]然而,在印度當局的故意刁難和迫害下,很多難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印方原本承諾釋放的995名華僑只有909人得以登船離境。
4月27日,中國政府根據(jù)首批歸國難僑反映的情況,再次向印度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并重申了釋放全部難僑的要求。[50]然而,對于中國政府連續(xù)不斷的抗議和合情合理的要求,印度當局或置之不理、或避重就輕,甚至反誣中國列舉的事實都是虛假宣傳。印度當局還蓄意制造“兩個中國”的話題,謊稱有些華僑并不愿意返回“大陸中國”[51]。5月17日,印度再度聲稱“他們不準備強制遣返那些不愿意返回中國的人”。[52]25日,“光華輪”抵達馬德拉斯港后,印度當局又一次自食其言,將此前已明確同意釋放的842名難僑扣留了178人,導致僅有664名難僑登船。當中國政府要求印方做出解釋時,[53]印度當局竟然聲稱“既不強迫也不阻止他們?nèi)ブ袊保磺卸寂c其無關。[54]
更為惡劣的是,中國方面協(xié)商接運第四批難僑時,印方卻回復“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愿意被遣返的有中國血統(tǒng)的人了”,斷然拒絕了中方繼續(xù)接僑的要求。[55]事實上,當時仍有大量難僑被印度當局關押在集中營和各地的監(jiān)獄。在迪奧利集中營和諾岡監(jiān)獄尚有700多名難僑等待救助。[56]印度媒體《印度斯坦旗報》則報道,僅在迪奧利集中營就有多達1000名要求回國的被拘難僑。[57]除此之外,在加爾各答、孟買等地的監(jiān)獄也還關押著大量難僑。鑒于這種情況,中國政府不得不繼續(xù)通過外交渠道與印度當局交涉,要求其盡快釋放全部在押難僑并同意中方再次派船接僑。但中國政府的這些正當要求均遭到了印度當局的拒絕,接回所有被拘難僑的計劃最終落空,部分難僑直到1967年才重獲自由,朱秀英、張士興、侯錦秀等數(shù)十名難僑則在關押的過程中被迫害致死。[58]
為解決難僑歸國后的生計問題,早在首批難僑回國之前,國務院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難歸國華僑委員會”,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難僑的接待和安置工作。[59]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休養(yǎng)或治療后,歸國難僑按照個人志愿,大部分被分散安置在各地的華僑農(nóng)場,少數(shù)人選擇了回鄉(xiāng)落戶,無一人再度流離失所。
五、結(jié)語
邊境戰(zhàn)爭后印度圍捕和拘禁華僑是中印關系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本文在梳理分析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印度外交部編撰的《白皮書》《外事檔案》等文獻資料后發(fā)現(xiàn):作為戰(zhàn)敗方,印度之所以在中國主動宣布停火撤軍后仍繼續(xù)大規(guī)模圍捕和長時間拘禁華僑,其行為看似有悖常理,實則是印度當局在國際援助和國內(nèi)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為獲得戰(zhàn)俘問題上的所謂“對等”、維護國家的“體面、尊嚴和自尊”而不擇手段的結(jié)果。
盡管中國領導層對印度當局的意圖洞若觀火,但為了爭取尼赫魯政府重回和平談判,防止其加速右轉(zhuǎn)、完全投入西方陣營,中國政府在救助難僑的過程中始終堅持通過外交渠道與其交涉,并未采取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不過,事實證明,“印度政府特別是尼赫魯沒有談判需要,只有冷戰(zhàn)需要”。[60]此后,兩國關系持續(xù)冷淡,直到70年代、尼赫魯去世多年后才逐漸有所改善。而在另外一方面,旅印華僑對印度當局的所作所為一直心有余悸,很多有條件者相繼選擇離開印度,另謀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2004年在印漢族華僑的總數(shù)僅余6000人。[61]近年來,中印經(jīng)貿(mào)往來雖有較大增長,印度華僑社會衰落的趨勢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注釋]
[1] 《印度華僑簡況》,《僑務報》1962年第6期;阿荒:《印度華人飽經(jīng)滄桑》,《僑園》2006年第2期。
[2] 《中國駐印度大使潘自力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的書面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和印度關于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匯編(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內(nèi)部刊物,第61頁。
[3] 新華社:《歸僑揭露印度當局伙同蔣幫特務的反華勾當》,《人民日報》1963年8月23日。
[4]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December 31,1962)”; “Memorandum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January 6, 1963)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Notes,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Vol.8,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1963, pp.111-112, p.114.
[5] 黃云松:《從中印藏人身份的法律爭議看印度的涉藏行為》,《南亞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
[6] 編者:《印度華僑簡況》,《僑務報》1962年第6期,第10頁。
[7] The Foreigners Law (Application and Amendment) Act, 1962, 2016年10月,http://www.helplinelaw.com/docs/theforeigners-law-application-and-amendment-act-1962, 2018年2月15日訪問。
[8] 新華社:《就印度當局在全國猖狂迫害華僑 我外交部向印度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人民日報》1962年11月9日。
[9] 新華社:《印度軍警嚴密封鎖 特務到處監(jiān)視 移民局經(jīng)常勒索 加爾各答華僑聚居的塔壩區(qū)已成變相集中營》,《人民日報》1963年8月22日。
[10] “Letter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to Premier Chou En lai”, December 1,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8. p.29.
[11] “Prime Minister’s Broadcast”, November 19,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vol.8,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63, pp. 318-319.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1–1963, Vol.1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397.
[13] John Kenneth Galbraith,ALife inOur Times: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1, pp.438-439;“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November 19, 1962,F(xiàn)RUS,1961-1963,Vol.19, pp.399-400.
[14]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cember 5, 1962,F(xiàn)RUS, 1961-1963, Vol.19, pp.420-421.
[1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20, 1962,F(xiàn)RUS,1961-1963, Vol.19, pp.449-454.
[16] Jerome M. Conley,Indo-Russian Militar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Lessons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in SouthAsia,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 p. 14.
[17] 戴超武:《亞洲冷戰(zhàn)史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73-275頁。
[18] “Shipping Services between India and USSR: New Agreement Signed”, November 20,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8, p.321.
[19] “Defence Minister’s Statement on Supply of MIGs”, December 4,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8, 1963, p. 337.
[20]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21~341頁。
[21] 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印:《亞洲國家(地區(qū))與中國的關系》,上冊(東亞、南亞、西亞及附錄),1965年5月,第252、270頁;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印:《亞洲國家(地區(qū))與中國的關系》,下冊(東南亞),1965年5月,第198~199、237頁;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印:《非洲國家(地區(qū))與中國的關系》,1965年5月,第16、166、222頁。
[22]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on Border Situation”, November 19,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8, p. 319.
[23] Neville Maxwell,India’s China War, p.409.
[24] “Prime Minister’s Broadcast”, November 19, 1962,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vol.8, pp. 318-319.
[25] John Kenneth Galbraith,A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p.437.
[26] Ajay B. Agrawal,India Tibet and China: the Role Nehru Played, Mumbai: N A Books International, 2003, pp.194-195.
[27] T. Karki Hussain,Sino-Indian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62-66, New Dehil: Thomson Press (India) Limited, 1977, p.29.
[28] “Prime Minister’s Reply to Debate in Lok Sabha”, January 25, 1963,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9,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63, pp.37-46.
[29] 《印度外交部發(fā)言人1962年11月27日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99頁。
[30]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in Lok Sabha on India-China Border Situation”, December 10, 1962,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F(xiàn)oreign Affairs Record, vol.8, p.335.
[31] 駐印度使館:《陳代辦就華僑問題見梅農(nóng)事》,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編號113-00458-01,第3頁。
[32] 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1962年12月28日給我駐日內(nèi)瓦總領館的備忘錄》,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編號113-00458-01,第8頁。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63年8月26日給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3年11期,第289頁。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62年11月24日給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抗議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1962年13期,第266頁。
[35]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關于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62年12月1日起主動開始后撤呼吁印度政府及時采取相應措施給印度共和國總理尼赫魯?shù)男拧罚腥A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2年13期,第263~264頁。
[36] 駐印度使館:《陳代辦就華僑問題見梅農(nóng)事》,1962年12月10日,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編號113-00458-01,第2~3頁。
[37] 外交部:《關于日內(nèi)瓦公約問題》,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編號113-00458-01,第6~7頁。
[38] [3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62年12月18日給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抗議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2年14期,第295頁。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發(fā)言人關于印度當局繼續(xù)無理迫害華僑并企圖阻撓我國派船接運華僑回國的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3年第1期,第19~21頁。
[41]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March 7,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Notes,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Vol.9,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63, p.101.
[42] “Note Given by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to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March 14,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06.
[43] “Memorandum given by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to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March 26,1963,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p.112-113.
[44]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March 26,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09.
[45]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March 29,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58.
[46] 新華社:《歸國難僑揭露印度當局卑鄙暴行陰謀扣留華僑打擊僑胞愛國意志》,《人民日報》1963年5月17日;新華社:《歸僑揭露印度當局伙同蔣幫特務的反華勾當》,《人民日報》1963年8月23日。
[47] 新華社:《應在頭兩批回國的二百六十多名難僑為什么沒有回來?歸僑揭露印度當局扣留難僑的卑劣手段》,《人民日報》1963年6月16日。
[48] “Note Given by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to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April 1,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14.
[49] “Letter Given by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to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April 9,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16.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63年4月27日給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3年10期,第182頁。
[51]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May 6,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30.
[52]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May 17,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38.
[53] “Memorandum Given by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to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June 10,1963,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p.147-148.
[54] “Memorandum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June 14,1963,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Vol.9. p.150.
[55]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to the Embassy of China in India”, August 10, 1963,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White Paper: Notes,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and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Vol.10,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64, p.60.
[56] 新華社:《第三批歸國難僑在湛江舉行集會 強烈抗議印度當局阻撓我國繼續(xù)接僑》,《人民日報》1963年8月29日。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63年8月26日給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3年11期,第289頁。
[58] 新華社:《歸國難僑控訴德奧利集中營慘絕人寰的暴行》,《人民日報》1963年4月23日;新華社:《向祖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控訴》,《人民日報》1963年4月28日;新華社:《歸國難僑集會控訴印度殘酷迫害》,《人民日報》1963年4月30日。
[59] 新華社:《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難歸國華僑 國務院決定成立接僑委員會》,《人民日報》1963年4月25日。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61頁。
[61] 錢峰:《從半個世紀前的5萬人減到目前的6000人 印度華人為何越來越少》,《環(huán)球時報》200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