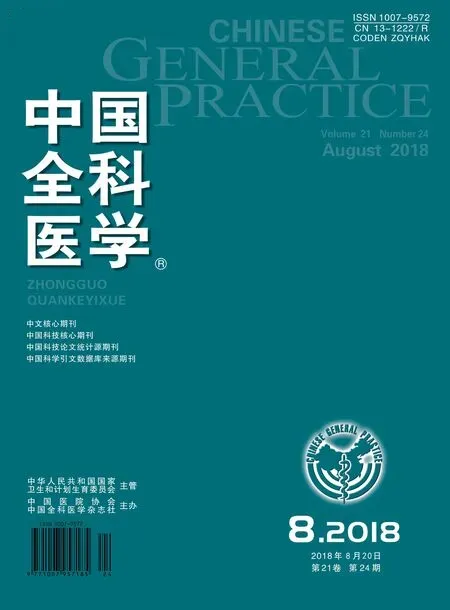慢性腎臟病患者腸道菌群的變化及影響研究
包文晗,王悅
健康人群的消化道內定居著約100萬億的微生物,其基因總數約為人體基因數量的100倍,構成了人體消化道內復雜而龐大的微生態系統[1]。正常情況下,腸道菌群與人體相互適應、互利共生,人體為腸道菌群提供寄居場所,腸道菌群參與人體的消化吸收、能量代謝、免疫調節等生理活動[2]。近年來,多項研究表明腸道菌群結構和功能紊亂與多種疾病相關,如慢性腎臟病(CKD)、癌癥、肥胖、糖尿病、炎癥性腸病等[2-3]。CKD患病率為8%~16%,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疾病[4],其與腸道菌群的關系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就CKD患者腸道菌群的變化及影響做一綜述,希望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延緩CKD進展以降低病死率。
1 腸道菌群的組成和生理作用
健康人群腸道內定居著種類繁多的微生物,其中以5個細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放線菌門、變形菌門、疣微菌門)和1個古菌門(廣古菌門)最常見。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占腸道菌群的90%[2]。腸道菌群中既包含對人體有益的益生菌,又包含一些潛在致病菌,二者處于共生狀態。腸道菌群保持動態平衡并與人體相互作用,發揮著重要生理功能。腸道菌群可通過修復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結構、誘導熱休克蛋白表達、上調黏蛋白基因、競爭性抑制病原菌、分泌抗菌肽、抑制腸道炎性反應等方式維持腸道的結構與功能[2,5]。腸道菌群參與重要免疫反應,可促進免疫系統發育和成熟,降低人體對食物或環境中抗原的過敏反應,誘導免疫調節及細胞分化[2,6]。此外,腸道菌群還可參與能量物質代謝,如降解難消化的植物多糖,促進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合成維生素B、維生素K和氨基酸等[3,7]。正常情況下,腸道菌群與人體處于動態平衡、互利共生狀態。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可引起一系列疾病,而疾病的發生發展亦可導致腸道菌群發生變化。
2 CKD/終末期腎臟病(ESRD)患者腸道菌群變化
CKD/ESRD患者腸道菌群與人體間的平衡被打破,腸道菌群的數量和結構發生明顯變化。VAZIRI等[3]研究發現切除5/6腎臟的尿毒癥大鼠腸道中乳酸桿菌和普雷沃菌的比例顯著降低。ESRD患者腸道中短桿菌、伯吉古菌、腸桿菌、鹽單胞菌、莫拉菌、涅斯捷連科菌、多囊黏菌、假單胞菌及絲硫菌家族的比例顯著增多。王尊松等[8]對60例非透析尿毒癥患者、60例透析尿毒癥患者及30例健康志愿者的糞便進行分析,發現透析尿毒癥和非透析尿毒癥患者糞便中長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水平明顯降低,糞腸球菌、大腸埃希菌水平明顯升高。由此可見,CKD/ESRD患者腸道內益生菌減少,而致病菌增加。CKD/ESRD引起菌群失調的機制目前尚不明確,可能的機制包括:(1)飲食中纖維素攝入減少:CKD/ESRD患者為限制鉀離子攝入而減少蔬菜和水果的攝入,導致飲食中纖維素攝入減少,腸道內纖維素和蛋白質比例失調,分解蛋白的細菌增加,最終導致菌群失調[9]。(2)結腸排空時間延長:多種因素如生活方式、飲食限制、磷酸鹽結合劑、原發性腎臟病及并發癥等均可導致結腸排空時間延長,含氮物質在腸腔內潴留,菌群能量結構發生改變,引起菌群失調[2,10]。(3)腸道內可利用的蛋白質增多:CKD/ESRD患者蛋白消化吸收功能受損,導致腸道內可利用的蛋白質增多,腸道內分解蛋白質的細菌數量增多[10-11]。(4)腸道pH值增加:CKD/ESRD患者血液中尿素水平增加,腸道細菌可將尿素水解產生氨,引起腸腔內糞便pH值增加,從而導致菌群失調[2,8]。(5)藥物:CKD/ESRD患者治療過程中服用的抗生素、磷酸鹽結合劑、代謝拮抗物等藥物均會影響局部腸道導致菌群失調[2-3]。CKD/ESRD患者腸道菌群失調可引起腸道菌群移位、局部或全身炎性反應、尿毒癥毒素增加,進而加快CKD進展[1-2,6]。
3 CKD/ESRD患者腸道屏障功能受損
CKD/ESRD可以損害腸道屏障功能,引起菌群移位,導致內毒素血癥及炎性反應。正常情況下,腸黏膜上皮細胞及其頂端的緊密連接蛋白能阻止細菌及有害物質由腸道入血。研究發現尿毒癥小鼠結腸壁中緊密連接蛋白的重要組成部分:閉合蛋白、封閉蛋白-1、ZO-1的表達明顯下降,導致腸道通透性增加[2,12-13]。VAZIRI等[14]用血液透析前的ESRD患者血清培養腸上皮細胞,發現體外腸道上皮細胞的通透性增加,并伴有閉合蛋白、封閉蛋白-1、ZO-1的減少。尿毒癥毒素水平增加可引起細胞間緊密連接蛋白表達下降,導致腸道屏障功能受損。腸上皮細胞間緊密連接蛋白表達下降也可降低腸道上皮防御功能,引起腸道屏障功能受損、腸道通透性增加[2]。此外,腸道低灌注,尤其是透析時超濾量過多或血壓較低時,也可導致腸道屏障功能受損,腸道通透性增加[2,15]。CKD/ESRD患者腸道屏障功能受損及腸道通透性增加可引起腸道內致病菌及毒素移位進入血液循環,導致內毒素血癥、局部或全身炎性反應,加速腎功能惡化,形成惡性循環[2,5]。
4 腸道菌群失調與尿毒癥毒素
腎功能減退時,經腎臟排泄的尿毒癥毒素在體內蓄積可以影響腎臟正常生理機制。近年來,蛋白結合性尿毒癥毒素(PBUTs)越來越受到重視[2]。PBUTs前體由腸道菌群分解蛋白質產生,CKD/ESRD患者腸道內誘導碳水化合物分解的菌群減少,而誘導蛋白質分解的菌群增多,可導致PBUTs產生過度。此外,CKD/ESRD患者腸道蠕動減慢,食物蛋白在腸道內停留時間過長,也可導致PBUTs產生增加[2,16-17]。PBUTs多與清蛋白結合,難以被血液透析清除,不但使CKD患者腎功能惡化,還可以誘發炎性反應,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之一[17],其中硫酸吲哚酚(IS)和對甲酚硫酸鹽(PCS)最具代表性[18]。食物中的色氨酸以及苯丙氨酸、酪氨酸在腸道菌群作用下轉化為吲哚和對甲酚,經腸道吸收后在肝臟代謝產生IS、PCS。IS和PCS主要經腎臟排泄,而CKD患者血清中IS和PCS水平增加[2,19]。血液透析對IS和PCS的清除率<10%[2],這可能是血清中IS和PCS與CKD進展、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病死率密切相關的原因[20-22]。IS可促進腎小管上皮細胞活性氧(ROS)產生,激活核因子κB(NK-κB)、p53等調節因子,使趨化因子表達上調,引起腎間質單核細胞/巨噬細胞聚集,導致腎臟纖維化[23-24]。IS也可以通過激活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促進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表達、腎臟纖維化,加速腎功能惡化[25]。PCS可通過激活RAAS促進腎間質成纖維細胞增殖和分化,加重腎臟纖維化[26]。PCS具有促炎作用,可促使腎間質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浸潤及白介素6(IL)-6、TGF-β等炎性因子表達上調,從而促進腎臟纖維化[27]。IS及PCS均可導致Klotho基因超甲基化,抑制Klotho基因表達,使其產物對腎臟的保護作用減弱,促進腎臟纖維化,加速腎功能惡化[28-29]。DOU等[30]研究發現IS可通過促氧化應激作用導致血管損傷。IS也可通過削弱抗氧化屏障作用和促氧化應激作用促進心肌細胞肥大和心肌纖維化[31]。PCS是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22,29]。HAN 等[32]研究發現PCS可通過增強還原性輔酶Ⅱ氧化酶活性,增加ROS,促進心肌細胞凋亡。
近年來,隨著對腸道菌群和尿毒癥毒素的研究深入,腸道菌群代謝產物氧化三甲胺(TMAO)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富含膽堿、肉堿、甜菜堿等的食物經腸道菌群代謝產生三甲胺,后經肝臟分泌的黃素單氧酶氧化成TMAO。TMAO主要經腎臟排泄[33],隨著腎功能減退,TMAO在體內蓄積,血清中其水平顯著升高[34]。TANG等[35]研究發現TMAO可使磷酸化的Smad3水平增高,促進腎間質纖維化。MISSAILIDIS等[36]對179例CKD 3~5期患者和80例健康對照者研究發現,透析治療不影響患者血清TMAO水平,TMAO水平與其血清IL-6、纖維蛋白原、超敏C反應蛋白水平呈正相關;TMAO水平與增加的系統性炎癥相關,是CKD 3~5期患者病死率的獨立預測因素。有文獻報道TMAO是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心功能不全發生和發展的危險因素,其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33]。此外,腸道菌群也可促進胍類衍生物、馬尿酸鹽、苯乙酸谷氨酰胺、硫化氫等尿毒癥毒素產生,對人體造成損害[1]。
5 腸道菌群失調與免疫調節功能
正常情況下,人體與腸道菌群處于動態平衡,腸道菌群對抵抗病原體感染、促進免疫系統形成及成熟、誘導免疫耐受、維持免疫穩態起著重要作用。如果人體與腸道菌群間的動態平衡被打破,可對人體產生許多負面影響。CKD/ERSD患者腸道屏障功能受損、腸道菌群移位、致病菌過度繁殖,可激活局部和全身免疫反應以清除病原體。WANG等[37]在尿毒癥大鼠中發現腸道菌群移位,菌群從腸道進入腸系膜淋巴結、血液、肝臟及脾臟,并伴有血清IL-6、C反應蛋白水平增加。腸道菌群失調可使腸黏膜上皮細胞分泌IL-1和IL-6增加,使B細胞產生大量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誘導樹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激活輔助性T1(Th1)細胞和輔助性T17Th17細胞[38]。MCINTYRE等[39]研究發現CKD患者血液循環中細菌內毒素,即脂多糖(LPS)水平隨CKD進展而升高。LPS被巨噬細胞識別,促進干擾素(IFN)-β、IFN-γ、IL-1β、IL-6、IL-12、腫瘤壞死因子(TNF)α等釋放[2]。大量細胞因子、炎性因子等釋放可加重腸道屏障功能的損傷,促使腸道菌群移位,形成惡性循環。持續性全身炎性反應是CKD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40]。細菌的產物可激活血管內皮細胞、樹突狀細胞、巨噬細胞等細胞上的識別受體。LPS的受體Toll樣受體4(TLR4)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過程。因此,CKD/ESRD患者中LPS/TLR4信號上調,可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41]。
CKD/ESRD患者雖處于慢性全身性炎癥狀態,但仍存在免疫缺陷,使感染概率增加,其機制尚不明確[2,6]。有學者推測,在CKD/ESRD患者中,移位的腸道菌群及產物持續刺激Toll樣受體(TLRs)可產生免疫耐受現象,而伴隨炎性反應上調的抗炎因子可以抑制免疫功能,形成免疫缺陷狀態[6,42]。上述機制是否正確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6 CKD/ESRD患者腸道菌群失調的治療
近年來,部分報道顯示患者服用益生菌、益生元或合生元可減少尿毒癥毒素產生、減輕全身炎性反應、延緩CKD進展[1-2,38,43]。而益生菌是對人體健康有益的活菌,包括雙歧桿菌、乳酸桿菌、鏈球菌等。益生元是指能被宿主體內菌群選擇性利用并有益于宿主健康的物質[44],包括菊粉、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大豆低聚糖、低聚木糖、焦糊精等[43]。益生菌和益生元結合在一起,稱為合生元[2]。RANGANATHAN等[45]對46例CKD 3~4期患者進行6個月的隨機雙盲交叉試驗,發現服用益生菌(嗜酸乳桿菌KB27、長雙歧桿菌KB31、嗜熱鏈球菌KB19復合制劑)可使患者血尿素氮水平下降。WANG等[46]研究發現腹膜透析患者服用益生菌(兩歧雙歧桿菌A218、鏈狀雙歧桿菌A302、長雙歧桿菌A101、植物乳桿菌A87復合制劑)可降低血清中細菌內毒素、TNF-α、IL-6、IL-5水平,增加抗炎因子IL-10水平。MEIJERS等[47]對血液透析患者使用菊粉治療4周,血清PCS顯著下降。ROSSI等[48]研究發現,CKD患者服用合生元(菊粉、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乳酸菌、雙歧桿菌、鏈球菌復合制劑)可明顯降低血清PCS,但對IS無明顯影響,并且可使腸道中雙歧桿菌增多,疣微菌減少。此外,益生菌也可延緩腎臟纖維化、減輕動脈粥樣硬化[5]。目前,益生菌、益生元等對腸道菌群、腸道屏障結構和功能的調節機制尚不明確。由于研究樣本量較小、隨訪時間較短,益生菌、益生元等對CKD/ERSD的治療效果并不清楚[2,38]。有文獻報道,CKD患者飲食中纖維素增加,可促進益生菌增殖、減少炎性反應、降低全因死亡率,認為CKD/ESRD患者應適當攝取富含纖維素食物[9]。但目前對飲食中纖維素的最佳攝入量并沒有明確報道[1-2,5]。調節腸道菌群可治療并延緩CKD進展,這為CKD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仍需大量基礎研究和臨床試驗明確其機制和療效。
近年來,有研究發現腸道吸附劑(AST120)和緩瀉劑(魯比前列酮)可通過吸附腸道內毒素、促進腸道蠕動等機制降低CKD患者體內尿毒癥毒素水平,延緩CKD進程[2,5],但其作用機制及療效有待進一步研究。
7 小結及展望
腸道菌群構成人體消化道內復雜而龐大的微生態系統,與人體處于互利共生、動態平衡關系。CKD患者中人體與腸道菌群間的動態平衡被打破,導致菌群數目及結構變化、腸道屏障功能受損。腸道菌群失調可引起菌群移位、尿毒癥毒素產生增多以及局部/全身炎性反應,加速CKD進展,增加全因死亡率[1-2,43]。腸道菌群失調與CKD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由于腸道菌群數量龐大,組成及結構復雜,而且不同人群中腸道菌群的組成和豐度不同,其參與CKD發生發展的確切機制尚不明確。目前,中國學者對腸道菌群與CKD關系的研究較少,腸道菌群對中國CKD患者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隨著人類微生物組計劃的進行和高通量基因組測序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對腸道菌群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有望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延緩CKD進展、改善動脈粥樣硬化、降低病死率,前景十分廣闊。
作者貢獻:包文晗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文獻收集、整理,撰寫并修訂論文;王悅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