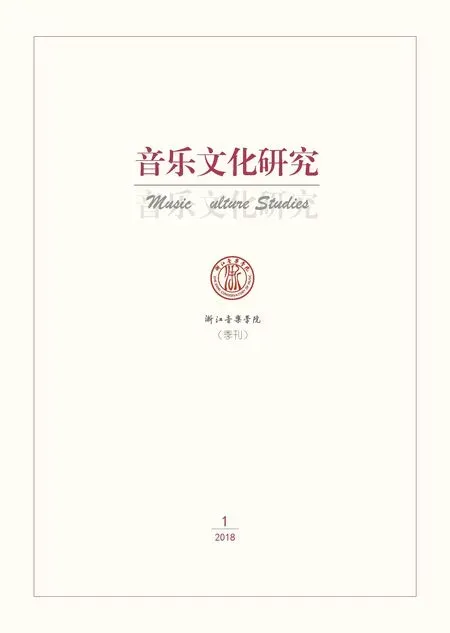《浙江戲曲音樂》序言
洛 地
本書,題名《浙江戲曲音樂》,是一部按“戲曲音樂腔調系統”編寫的戲曲音樂專著。
按“戲曲音樂腔調系統”對戲曲音樂作總體性考察,對戲曲音樂進行梳理、分類、別種,我們不清楚以前是否有人曾經這樣做過及做得如何,至少對我們來說,是無前例可循的“新”的嘗試。今天,在本書完稿,提筆寫這篇《序》的時候,回顧這四年多的歷程,面對這部書稿(未能稱盡我們之意的書稿),想象今后的可能,愿將我們曾遇到和還想著的一些問題,陳述于諸位師長、同道和讀者前,以求討論、共同思索和批評指正。
戲曲音樂,是戲曲音樂,本書既是一部戲曲音樂專著,當然是著述戲曲音樂,這會有什么問題呢?
但是,它恰恰成了問題。在這四年多時間內我們首先遇到的、也是使我們大耗心神的就是這個問題:一部著述戲曲音樂的專著或者說“集成”,是不是、應該不應該或者可不以立足于戲曲音樂本體,從戲曲音樂實際出發,按戲曲音樂自身內部結構進行分類別種,反映其發展脈絡、結構層次及傳流現狀等來編寫?具體地說,是可以或應當按“戲曲音樂腔調系統”編寫;還是只能按所謂“劇種”編寫?經過幾番周折,由于同志們的工作實績,浙江藝術研究所(領導陳西斌同志)的理解,同意我們在編寫一部按“劇種”分類的《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的同時,編寫一部按“調腔系統”分類的《浙江戲曲音樂》——就是本書。過程間的種種,今天已不必贅述。從學術上來說,是對事物的認識,對戲曲音樂的類別及如何進行分類的認識問題。
(一)事物,一大群體事物之有類種之分,是事物自身所具備的。對事物進行分類,并使與事物實際趨相一致,是人們正確地認識事物,即對該事物的認識進入“科學”的第一步及其歸結。
分類,對戲曲音樂與對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其目的是使事物系統化,即對事物的“系統”的認識。
“系統,具有整體性、結構性、層次性、歷史性等特性”,其中最根本的,決定系統之為系統的是“結構”——“結構是系統的本質方面”——事物的整體構成、層次等級、歷史征象等都取決于其結構。戲曲音樂是一大群體性事物,對其自身具有的系統的認識,即對它進行分類,只能按其結構,也就是我們時時所說的“透過現象求本質”。當我們將盡可能齊全的戲曲音樂資料,透過其各種繁復斑駁的現象探求其結構的時候,也只有當我們明了其結構的時候,我們就能也才能對它進行分類。結構——系統——分類,是認識事物及其類別的應有的思維或者說基本的知識。
戲曲音樂,其本質構成是音樂,其結構即為音樂結構,其系統為音樂系統,其分類當然是音樂之類別。
(二)一事物之成為該事物,在于它具有區別于他事物的特征。一事物的特征是他事物所不具有的,否則就不成其為特征了。對事物的類別、種別也同樣,事物的每一類、類下的每一種都有其自身的特征,此特征在該類、該種是必具的;而在與其同層次的其他各類、各種則是不具有的。事物類別的本質特征是其結構特征。如“高腔”“一人滾唱,眾口接腔”的腔句構成為其結構特征,“昆腔”以“‘字腔’與‘過腔’的組合”的腔句構成為其結構特征,二者相區別;而“高、昆”二腔又以同用長短句文體曲牌、同以“腔句構成”為其音樂結構特征而為一類“南北曲腔”,從而與以“唱調及唱調連接”為其結構特征的“亂彈諸調”相區別,與以“起平落”為其結構特征的“(唱說)攤簧”相區別,等等。
共同的音樂結構形成一個音樂系統,不同的音樂結構形成不同的音樂系統,包括大系統和小系統、母系統和子系統,無不以結構為其特征。我國戲曲音樂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劇唱往往用“腔”或“調”作為稱謂,不同的劇唱往往稱為“某腔”“某調”。音樂結構的異同,形成有層次的、有類別種別的“腔系統”“調系統”,統稱“腔調系統”。并不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所有的對戲曲及戲曲音樂的稱謂都具有“系統”的意義,然而,歷史已為戲曲音樂的類別即“腔調系統”提供了可資應用的某一些稱謂。事實上,歷史對戲曲音樂已曾作了某種程度的歸納,使某一些稱謂實際上已漸具有了一定程度上“腔調系統”的含義。如:“高腔”“昆腔”“亂彈”“攤簧”等。然而,它們往往是自然狀態下趨成的一種籠統的概念,未曾在理論上予以確定和規范,更不曾從“結構”這個“本質方面”去把握戲曲音樂“腔調系統”的層次性和整體性;更者,又有近幾十年來尚未科學化的“‘劇種’論”逐步在歸納、形成過程中的系統化的自然趨勢受到了干擾。如“高腔”原本是個“腔系統”概念,其下有各“路”高腔(如“西安高腔”“西吳高腔”“松陽高腔”等),它可以單獨成班,也可以與他者合班,其關系本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劇種’論”,每一路高腔都可以成為一個“劇種”,又都可以不是“劇種”,前者如“松陽高腔”,后者如“西吳高腔”;而在某些“劇種”中,又可以包含著有高腔,如“婺劇”。在“婺劇”中,高腔成為一種“聲腔”(“婺劇”有所謂“六個‘聲腔’”),而且在“婺劇”的“高腔聲腔”種又可以有三至四種“聲腔”:“西安高腔”“西吳高腔”“侯陽高腔”和“松陽高腔”。于是,松陽高腔便成為:既是一個“劇種”,又是一種“聲腔”,又是另一種“劇種”(“婺劇”)的六種“聲腔”中的一種“聲腔”(高腔)中的四種“聲腔”中的一種“聲腔”。又如“昆腔”原本也是個“腔系統”概念,因是否運用“水磨”而區分出“正昆”“草昆”兩支,各支下有多路昆腔,可以單獨成班,也可以與他者合班;本來也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劇種’論”,它是一個“劇種”昆劇的別名;同時,這個“劇種”中又有許多“劇種”,曰:“蘇昆”“北昆”“浙昆”“金昆”“甬昆”“武昆”“永昆”等;同時,它又是許多不同“劇種”中的一種“聲腔”,如“婺劇”“甌劇”“臺州亂彈”“平調”等;又者,“金昆‘劇種’”全同于“武昆‘劇種’”,又全同于“婺劇‘劇種’”中的昆腔“聲腔”等。以上僅舉高腔、昆腔兩例(也還未說全其糾葛),其他都無不如此。
事實是,我們之所以會按“腔調系統”編寫這部《浙江戲曲音樂》,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打算的,也不是從“分類學”角度提出來的,而恰恰是先按“劇種”“劇種音樂”編寫《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因遇著了如上所述的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才對編寫體例問題、概念限定問題、特征問題等引起討論和考慮。考慮的基點是什么呢?是《集成》總部對編寫《集成》提出的總要求:“史料性、全面性、科學性。”按我們的理解:
“史料性”,不僅是指資料的翔實可靠,而須使本書具有“系統的‘歷史性’”。“全面性”,并不是羅列現象,而是須具有“系統的‘整體性’”。“科學性”,就是“分類”——“系統”的“層次性”和“結構性”。從結構——層次——系統——分類,才能反映歷史,通貫整體;從而反映總體面貌,“類”,是“整體”內的“類”;“種”,是“類”下的“種”。這樣做,才是有意義的,而不是去羅列一個地域內(如浙江省)有哪些個由“劇團”組成的所謂“劇種”和把諸劇團使用的音樂稱之為所謂“劇種音樂”;無論該著述是不是題名為“集成”。
(三)戲曲音樂、浙江戲曲音樂的類、種。
這里首先的問題是,浙江戲曲音樂是否具有“整體性”?回答是肯定的。
眾所周知,我國民族戲劇的成熟,其標志是南宋時的戲文,戲文首成于浙江——宋元之際的劉勛(公元1240—1319)其《水云村稿·詞人吳用章傳》有云:“至咸淳(1240—1319),永嘉戲曲出。”這是“戲曲”“永嘉戲曲”在文籍中的首載。元滅南宋(1276)后,元曲及元曲雜劇興起,浙江杭州是其中心——今存《元刊雜劇三十種》,其“大都新編”者僅四種,在“古杭新刊”者有八種,而“大都新編”四種之一的《東窗事犯》系據《西湖舊本》①;這可為說明元曲雜劇以杭州為盛之一斑。集“南戲、北劇”于一身的我國民族戲劇之大成的傳奇,其“鼻祖”是浙江人高則誠的《琵琶記》,其“絕唱”是浙江人洪升的《長生殿》,在自明至清(初)的“傳奇時期”,署名劇作家中浙江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浙江又是我國戲曲理論的中心地,有我國第一部及第一批戲劇評論集——呂天成《曲品》,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有我國戲劇學的奠基人李漁及其著作《閑情偶寄》。清中葉后,“亂彈”漸起。浙江“南北十一府”民間戲劇蜂擁勃興。直到近代,產生勢淹江河南北的“越劇”。
至于戲弄性質的“民間小戲”,自唐五代以下直至如今遍布全省。②
在戲曲音樂,古代無樂譜傳留,按現今有實際演唱可據的,浙江有元曲雜劇的“北曲”唱,有由“昆腔”演唱的《單刀赴會〈訓子〉〈刀會〉》《昊天塔〈會兄〉》《金貂記〈北詐〉》《漁樵記〈北樵〉〈寄信〉〈相罵〉》《馬陵道〈孫詐〉》《東窗事犯〈掃秦〉》《西游記〈認子〉〈胖姑〉〈借扇〉》及其他等等,尤為可貴的是,在“調腔”等“高腔”中,至今猶能演唱《北西廂〈游寺〉〈請生〉〈赴宴〉〈拷紅〉》《漢宮秋〈游宮〉〈餞別〉》,這是在全國僅存的。
明清傳奇,自《琵琶記》至《長生殿》,又有許多民間“無名氏”劇作演唱著。至于民間戲,向來以實際演唱而傳存著。總以上,浙江的戲曲及戲曲音樂,庶幾可反映我國民族戲劇史的全過程及我國戲曲音樂的整體面貌。
其實,這也不是浙江才如此,全國許多省(市)都差不多是這樣的。因此,以著述一個足夠大的地域如一個省份內的戲曲音樂為課題的一部專著,就當著眼于戲曲音樂的“整體性”及“系統性”。
我們將浙江的戲曲音樂“腔、調”,根據其結構分為三大類、九種(套),種下以其音樂形態特點分支、以地區差異分路,并按其興起的歷史時序排列,為:宋元至清初的“南北曲腔”,其下為“高腔”“昆腔”;下為各支、各路。清中葉勃興的“亂彈諸調”,內含:“三五七——二凡”“蘆花——拔子”“二簧”“西皮”四套;下有各路。清末民初后流行的是“攤簧”,有:“南詞攤簧”“唱說攤簧”,其中又歧發出“越劇(唱調)”;亦有支和路。
以上三大類、諸種(套)及其下的眾多支、路(詳見該書),以各自共同的又與他者相區別的結構,構成堪反映戲曲音樂歷史邅遞、層次等級的“腔調系統”的戲曲音樂整體。這樣地述說浙江戲曲音樂,庶幾才能使這部《浙江戲曲音樂》具有浙江戲曲音樂“總集”的意義;同時,是不是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具有了提供師長、學者、后人編纂中國戲曲音樂“總成”時作參考的意義。
(四)然而,本書畢竟是《浙江戲曲音樂》,只能對浙江戲曲音樂中的“腔、調”進行考察,探求的是浙江的諸“腔”眾“調”的結構而作歸納——故為“腔調系統”;而不能更進一步,從更大的宏觀角度、更高的學術層次,完全以音樂構成、音樂結構學角度去考察戲曲音樂,即不能完全從“結構系統”去梳理“腔、調”。這使我們不得不只能對“腔調”進行分類——即用不能反映音樂結構性質的“腔”“調”名稱以至許多非音樂性的名稱作為“腔調系統”類別種別的稱謂;而不能以“音樂結構”體式進行分類,即不能用音樂體式作為戲曲音樂類別種別的稱謂。具體地說,最使我們為難的是,本書不得不使用“越劇(唱調)”的說法,而不能用其音樂結構“兩段(四句)式”作為戲曲音樂的類種。
思維是由概念反映的,概念是用詞語來表達的,合乎邏輯的思維要求有明確的概念和有限定指義的詞語。
然而,由于漢語詞語的多義性,由于民間音樂用語的方言性和任意性,由于我國自古至今對音樂理論包括其術語往往欠缺嚴格的論證和確定;以及在近代西洋音樂及其理論輸入時使用的譯語,近幾十年來偏于“就俗求便”傾向等影響;使我們在使用詞語、確定概念、表述問題時遇到不少的困難。本書的做法是——
(一)對一些一般不致發生歧義的原有的詞語,盡可能地沿用。如:“高腔”“昆腔”等,“接腔”“腔格”“旋律”“樂句”等。
有一些詞語,本具有明確指義或者原系理論家的研究成果,只是在戲曲音樂界很少使用而往往被忽視著,本書按需要而沿用之。如“散聲”“正昆”等,“真戲劇”(王國維)、“戲弄”(任半塘等)等。又有一些詞語,從詞語構成角度說或有欠妥,只要使用較普遍而又不致發生概念混淆的,也沿用之。如“散板”“伴奏”等。
(二)對一些多義的及使用時常常發生或容易發生概念混淆的詞語,本書按其基本指義或其規范趨勢,力求加以限義、規范而使用。
如,“曲”這個詞,通常又指文體文學又用指音樂,混淆一起,其實在我國民族文藝,宋元以下,“曲”的指義主要為文,③故有“南曲”“北曲”之異、“散曲”“劇曲”之分;其音樂即唱,則有“曲唱”“歌唱”之別,“清唱”“劇唱”之分。因此,本書使用“曲”這個詞,一般只用指文體如“曲牌”“律曲”“南北曲”等;本書用“樂體”這個稱謂指稱音樂體裁以取代通常使用的容易引起概念混淆的“曲體”一詞。
又如“腔”與“調”,此二詞很經常地被混用而致混淆。本書采用此二詞的本義而分別用之。“腔”,在音樂,是為唱中的特殊的或特定的旋律片斷或局部,如“接腔”“幫腔”“字腔(腔格)”“過腔”“潤腔”等,“腔”的要領最大止于一音樂個體的旋律部分,如“腔句”,如某唱調的“唱腔”等。“調”,在音樂,是在某種限定條件下按一定關系組成的樂音排列,如以律位為限定條件為“調高”,以主音為限定條件的為“調式”,以散聲為限定條件有“笛調”“小工調”“正宮調”等,以及用作為對包括節拍、旋律、調式、首尾齊全的完全的音樂個體的一種稱謂,如[蘆花調][二簧調][弦索詞][燒香調]等,又有用其“指法調”作為其具體音樂個體的稱謂的如(“越劇”的)[四工調][尺調]等。因此,本書不用概念含混模糊的“聲腔”一詞;也不用與文體概念相混淆的“曲調”一詞④,而用“唱調”作為對完整的音樂個體的稱謂。也因此,本書將以用長短句曲牌為文體、以“腔句構成”為韻結構特征的一類定名為“南北曲腔”——以腔句構成為其音樂結構特征的南北曲的唱腔;將以唱調及唱調連接為音樂結構特征的一類定名為“亂彈諸調”——“亂彈”是沿用的稱謂,“諸唱調”包括唱調組合是這一類的特征。等等。
(三)當我們從戲曲音樂本體結構運河梳理其腔調系統的時候,有時發覺詞語的不足敷用,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使用一些精煉而成的“新”的詞語或詞組。如上已述及的“樂體”“唱調”及“南北曲腔”“亂彈諸調”等。
本書按“腔調系統”著述戲曲音樂,提示戲曲音樂的本體結構,并據此對戲曲音樂進行分類別種。人們對事物及其系統分類認識,是“從個別到一般,從普遍到特殊”不斷反復驗證的過程。人們對事物系統分類的結論及其表述方式,一般是從整體到類、類到種即大系統到小系統、母系統到子系統“從整體到部分,從一般到特殊”為次序;而人們對事物系統分類的認識的獲得過程,則是從個別到一般、特殊到普遍開始的——從事物的外部現象進而考察其內部結構,從小系統到大系統以至對事物整體認識。然后將認識付與驗證,再“從個別到一般”,再“從普遍到特殊”,反復驗證……對本書而言——
(一)首先,要求我們盡可能齊全地掌握戲曲音樂原始資料,以“事實的全部總和”作為基礎,從這里開始進行“從事實的聯系去把握事實”的探索;同時,要求我們的認識——對戲曲音樂腔調系統分類的認識與戲曲音樂實際趨向一致。我們以“寧濫毋缺”為要求,集印了約2000萬字篇幅的浙江各市、地戲曲音樂資料本60卷。參加編寫這60卷資料本的有浙江省四十多位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戲曲音樂工作者,他們是參與本書工作的“大班子”。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對戲曲音樂系統分類的大小各個課題,及直接編寫本書的“小班子”。要求“小班子”的每一個成員都須能對戲曲音樂三大類有所掌握,能運用邏輯思維,不僅熟悉浙江戲曲音樂的外部現象,而且探索其內部聯系。在本書編寫過程中的每一階段,由“小班子”分工,各領課題,互相合作,“攻關”、撰寫;然后提交“大班子”共同討論、通稿;再然后“水磨”,以“寧缺毋濫”為要求,寫出初定稿。在討論、研究、撰寫時,提倡“學術上‘求異存同”’,各抒己見;“工作上‘求同存異”’,集體合成。如此,逐步地使我們從感性向理性認識推進,使本書擺脫現象羅列,向戲曲音樂的結構、腔調系統、分類別種探索。
(二)事物的現象是斑駁繁復、變化無定的,而事物的結構則是一事物成為該事物穩定的因素即本質。本質在現象之中,但本質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現象。正如文體譜中的《詞譜》《曲譜》著述詞牌、曲牌的文體結構,并不包括介紹每一具體作家風采、每一具體作品意境一樣,本書著述戲曲音樂的結構、系統分類,并不能介紹每一具體唱段的“音樂形象”以及每一具體演唱上的具體特色。然而,也如同《詞譜》《曲譜》闡述每一詞牌、曲牌文體結構時必引用某些具體作品作例一樣。本書在闡述每一腔句、每一唱調等時也須引用某些具體樂譜作例。引例只為了說明結構。亦如一首具體詞作的文辭不能與該詞牌的文體結構相混同,一段具體樂譜不能與該腔句或唱調的音樂結構相混同一樣。在這里提出這一點,又為了要說明、強調說明我國文藝包括戲曲音樂在構成上的帶有根本性質的一個特點——“據本而演文”:
本,是本體、是本質;文,是具象、是文飾。戲曲音樂每類、每種以至每一唱調都有其“本”,“本”是事物內在的質,即其結構——結構是事物成為該事物穩定的因素,“結構的穩定性”為其“本”;依據此“本”演化為具體的“文”——發于唱者之口、入于聽者之耳的聲、音,反映在書面為具體的樂譜,具體的唱(樂譜)即為其“文”,“文”是其數無定又變化無窮的,任何一唱調沒有完全相同的兩段具體的唱,而不論有多少以至無數的變化無窮的不同的唱(譜)都是依據該唱調的穩定的結構而演化出來的——這,反映為戲曲音樂構成上的“使用上的通用性”。
以上,便是“據本而演文”。本質在現象之中,現象并不就是本質,羅列現象并不能反映本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明[二簧調]的結構,即使將其所有具體的唱譜收集羅列,并不能說明何為[二簧調],不探求戲曲音樂的結構系統,即使將戲曲音樂所有的樂譜收集羅列,并不能知何為戲曲音樂。
(三)本書對戲曲音樂的結構、系統、分類,只是一種探索,探索的初步。
本書不是一部理論研究性的專著,至少不是真正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研究。本書所做的,只是按戲曲音樂本體結構、腔調系統對戲曲音樂、浙江戲曲音樂的類別種別及諸支路作一些我們可能做到的介紹和闡述而已。
本書的目標是希望能使讀者“知其然”——知戲曲音樂、浙江戲曲音樂腔調之“然”,這目標未必很輕易地能達到,本書只是在求“知其然”上的一個開端,還有許多問題并沒有解決;所以,如果本書有幸正式出版了,還是一本“初稿”;至于“所以然”即真正進入對戲曲音樂規律性的理論研究,只能有待于今后,有待于同道諸賢了。
以上為序。
《浙江戲曲音樂》編著組
1992年9月
注釋:
①另外18本未標明地名。
②(南)宋雜劇及金元院本之段數(院本)名目,唯浙江人周密、陶宗儀所撰《武林舊事》《輟耕錄》中有載乃傳世。
③如《欽定曲譜》,何良緣、徐復祚等人的《曲論》,王驥德《曲律》,臧晉叔《元曲選》,呂天成、祁彪佳等人的《曲品》以及《曲海總目》等無數文著,其所稱“曲”明確地皆專指文——文體文辭以至劇作。
④“曲調”,在民族文藝原系指韻文文體學中與“詞”相對的“曲”文體中的個體的稱謂,即俗稱為“曲牌”者,明王驥德《曲律》“曲之調名,今俗曰‘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