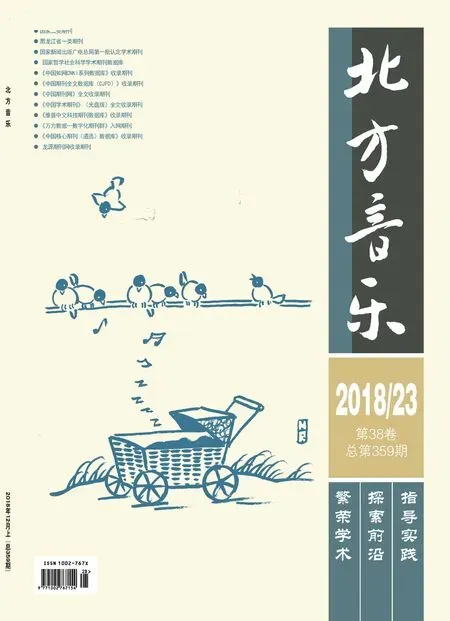浙江民歌的音樂特征與演繹
王 潔
(浙江音樂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4)
前言
浙江省繁榮的經濟以及獨特的區域環境使得其勞動內容與方式非常豐富,因此,在這片土地孕育了大量內容豐富、旋律優美的民歌,這些風格多樣的民歌賦予了多彩的生命力于浙江音樂文化,獨具特色的浙江方言也為民歌的韻味增添了藝術色彩。作為一種伴隨著民族文化發展歷程的藝術文化,民歌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獨特的民族色彩是組成我國絢爛民族音樂文化的要素。筆者作為民族聲樂的教育者、表演者與傳播者,以浙江民歌為例,希望能為民族聲樂的深層發展提供助力。
一、浙江民歌的音樂特征
浙江民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具有悠久的歷史,是生活在東南沿海地區人民勞動生活的真實寫照,情感世界的高度凝練。按照音樂體裁,浙江民歌能夠分為號子、山歌、儀式歌、蓮花、燈調、小調等類別,具有強烈的江南韻味,音樂風格鮮明。
浙江民歌的節奏節拍有著獨特的形式,極具地方特點,這些特點在教科書似的民歌節拍特點總結中,往往被錯誤理解為“臨時變換”,這種共同規律的研究方式,反而不利于民族音樂的個性研究,使得其獨特的民族形式在這種研究概念中被忽略了。散拍子,是我國民間音樂所共有的節拍形式,浙江民歌也不列外,它將散拍子作為基本的節拍形式應用。在散拍子的大線條旋律之后,往往還會有一些具有敘事性、小段、快速的樂段作為調劑,而這種極具口語化的旋律,通常采用一拍子這種旋律線條平穩、一字一音的節奏形式。還有一種類似于明年見鑼鼓節拍中的形式——“強弱強”在浙江民歌中有較多體現。例如普遍流行于杭州地區的《采茶歌》就較好的體現了三拍子的節拍,四字句的格律,每個樂句的第四個字大多為虛字,伴隨著采茶勞動的動作,三拍子運用得更為自然貼合。再如搬運號子這類勞動號子,作為強力勞動時的調劑精神的“作料”,三拍子更具感染力。
浙江民歌的音階調式也富有地方色彩。作為南曲發祥地的浙江,曲調與戲曲、曲藝的聯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就現存的浙江民歌而言,其音階調式大多采用我國傳統的五聲音階,在過門處通常采用五聲音階之外的音。例如《苦老大》這首舟山民歌,主調性采用五聲音階,在第七樂句則出現了變宮音,在最后兩小節還出現了變徵音,而這些音仍屬于五聲音階。對于浙江地區,尤其是舟山群島與浙南地區的民歌之中,七聲音階也較為普遍存在,比如《繡牡丹》這首舟山民歌中就呈現出音階轉換的現象,在五聲音階中加入了七聲音階,從而使得音樂的感情更富有色彩,多了些轉折與變換,豐富了音樂的內容。
再次,民間音樂中旋法的特點在浙江民歌中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旋法,廣義上可定義為旋律,這里重點指旋律同語音、語言的關系,等等。在語言層面,浙江方言統歸于吳語,也存在少數民族方言,語音、語調的區別賦予了浙江民歌特有的風格,尤其體現在人聲。在浙江民歌中,凡是入聲字通常表現得較為短促,由于南北地方的差異,北方的語言中并不存在入聲,而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入聲較多,因此形成了這一旋法特點,這在口語化較強的民間歌曲中較為常見。首先是受地方語言傳統的影響;其次是由當地的生產方式與內容所決定的,浙江地區的生產主要以茶葉、稻田、棉等為主,在氣質上較為平穩,常用音區適中;再次,受江南風俗與小調的影響,演唱用音同口語較為接近。
第四,在曲體方面,我國民歌大多形式短小,對于一些篇幅較長的體裁,長以分節歌的形式呈現,在這一層面,浙江民歌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一種是在浙江民歌中占有較大比重的“單句變化體”。這是一種每個樂句擁有相同結束音,相同旋律骨架,在詞位、節奏等方面能夠看出的微妙變化。雖然看起來單調,但演唱者可通過裝飾音以及與其的變化,使作品更富生氣。比如作品《麻只娘》中就有生動的體現。還有一種“起平落”的一段體形式,這是受浙江戲曲影響而形成的曲體形式。主要體現在節奏或句幅方面,“起平緊疊落”能夠較為形象地說明這一曲體的特點。
最后,表現在唱法方面,它包括語言咬字、發聲共鳴以及演唱情感等方面。語言、語調、情感以及唱腔等方面都需要演唱者細細體會,這些方面很難用文字來說明,需要依靠音響資料來仔細揣摩。
二、浙江民歌的演繹
浙江民歌是我國民族音樂中的絢麗瑰寶,它們是勞動人民在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體現了音樂最本真的形態。在演唱方法上,不需要過多的演唱技巧,甚至有些僅用真聲演唱就能夠直接表達作品的感情與意境。倘若按照演唱方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直聲,演唱時運用直白的發聲,在浙江民歌中,無論是采用真聲還是假聲的作品都含有直聲現象。例如《對面山上》這首金華民歌,就是一首直聲演唱的作品。而運用直聲演唱的歌手數目較多,且大多都是沒有接受過專業歌唱訓練的,因此演唱的水平良莠不齊,但也正是這種淳樸、真實、自然的唱法,使得這類民歌更具民族性。過多的修飾與技巧反而會使得這些根植于山林鄉野間的民間音樂多了些造作的人工氣息。
假聲或半假聲,這是需要一定歌唱訓練才能夠達到的演唱方法。假聲唱法主要體現在畬族的民歌作品中,演唱時通過頭腔共鳴,以假聲帶動聲帶邊緣的振動,使得聲音聽起來更加清透、響亮。而半假聲的演唱更具難度,僅有少部分歌手能夠從容運用,在演唱時主要運用真聲,在高聲區稍稍加入一些假聲,從而讓聲音變得更具彈性。例如《魚鷹號子》就需要運用此種唱法。
連頓音,這是浙江民歌尤為出彩的一種唱法。美聲唱法中也存在頓音,但通常僅運用單獨的頓音,在浙江民歌中,演唱者通過連續的頓音發出類似于咳嗽一般的“跳音”,為作品增添了生氣與活力。
裝飾音,這也是浙江民歌地方特色形成的重要體現。它能夠更加自然、巧妙地凸顯浙江民歌的音樂風格與語言特點。浙江民歌從根本上是由語言發展而來,曲調、旋律較為靈活。普通話包含四個聲調,浙江方言則包含八個聲調,豐富的聲調變化使得其民歌曲調尤為委婉、曲折。裝飾音,是浙江民歌延長中被較為常用的一種演繹方式,藝人在演唱時根據作品的內容、情感的需要,加入這種唱法,能夠極大的豐富音樂的內涵,增添作品的藝術表現力與音響效果。
三、結語
演繹民歌,首先要了解民歌所在地區的地方特點;其次,需要掌握該地區的地方語言,在演唱時做到音腔融合。中國民歌大多是大線條的旋律走向,流動的旋律中咬字就顯得尤為重要;再次,我國民歌主要是勞動人民生活智慧的結晶,節奏比較自由,演唱者須仔細體會作品的節奏韻律;最后,是演唱中的情感表現,我國的藝術文化善于借物抒情,演繹者須認真分析、體會作品的情感,再進行詮釋。民歌的演唱不僅要展現所在區域的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以科學的發聲方式為基礎,將聲音、語言等元素巧妙融合,最終才能呈現出完整的民族聲樂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