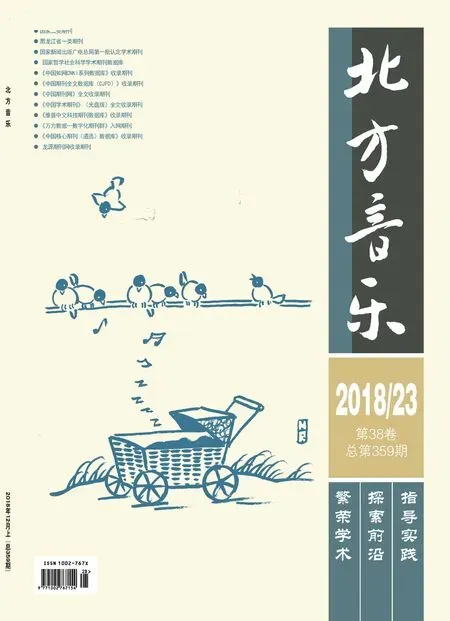古詩詞歌曲《峨眉山月歌》的版本對比與演唱探究
——以羅忠镕版與趙季平版為例
楊 柳
(蘭州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一、李白生平及其古詩《峨眉山月歌》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有“詩仙”之稱的李白是我國盛唐時期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他一生的漫游使其詩詞多以抒情為主,想象力豐富,詩風簡練豪放。李白存世的詩文有千余篇,有《李太白集》30卷,這些詩文或表現出對權貴諂媚之人的蔑視,對勞苦人民的憂心,或抒情寄予山水之間,表達對故鄉對友人的情誼。其詩文展現了唐詩歌獨特的藝術魅力。
這首《峨眉山月歌》是李白約25歲時初離蜀地創作的一首依戀家鄉山水,思念故鄉友人的佳作。短短四句中,從遠至近。秋高氣爽,峨眉山上掛著的半輪秋月倒影映在川流不息的平羌江上。從景到人,在靜謐的夜晚我從清溪乘船向三峽行進,我思念之人不得見,只能懷著不舍乘流東去,直下渝州。詩中巧用的五個地名也體現了詩人心思的細膩與情懷的豪放灑脫。
二、《峨眉山月歌》兩個版本的對比分析
(一)羅忠镕創作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歌》是羅忠镕先生于1984年選李白同名詩創作的藝術歌曲《唐詩絕句五首》中的第一首,1985年李雅美與廖沖在西柏林首演該作品。整首作品結合中國與西方作曲理念,將十二音序列技法、興德米特的作曲技法融入到作品中,以詩人李白乘舟觀景抒情,滿懷壯志與充滿離愁的心理作為全曲的創作基調,簡短精致,共25小節,無反復。在女高音獨唱與鋼琴伴奏的配合下,完美展現了音樂與詩詞的結合。
從樂譜上可以看出,作品是配合詩詞句子的非方整曲式結構,作品可以分成引子(1-5小節)、呈示部(6-12小節)、對比部(13-16小節)、再現部(17-20小節)、尾聲(21-25小節)。整部作品的旋律在中國傳統五聲音階調式風格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方和聲的創作思維,啟承轉合,采用F宮調式,小三度和弦為特征音程書寫樂曲的前三句,雖然在對比部分回到了F宮調式調性上,卻沒有旋律結束感,而是在再現部將調性轉為了降B調,給樂曲增加了一種縹緲而思緒未斷的感覺。樂譜中標記的音樂術語,配合右手的柱式和弦與左手分解和弦的流動,將作者的情感淋漓盡致的宣泄出來,展現了水的流動,山的巍峨,經過的地方和思念的人。旋律線條優美連貫,織體層次分明,在第四句“思君”處,出現全曲最高音,將情感推向高潮。在“下渝州”處婉轉結束,像寂靜夜晚留有的半絲情愁,首尾呼應。
(二)趙季平創作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歌》是趙季平先生于2014年發行的《唐風古韻》中十首唐詩藝術歌曲之一,也是選擇李白的同名詩詞創作譜曲,整首作品采用民族七聲調式,遵循詩詞的韻味特點,多采用一字一音的創作手法,用裝飾音進行修飾,增添了古韻的氣息。
從樂譜上看,整首作品在民族七升調式的基礎上采用A羽調式,小三度和弦做支持,樂曲中加入變音,使樂曲的古風風格更加凸顯。全曲共35小節,沒有復雜的調性與曲式結構,樂曲可以分成引子(1-4小節)、呈式部(5-11小節)、對比部(12-20小節)、簡單變化再現(21-35小節),樂曲結束在主和弦上,調性歸屬感強烈,并且最后兩小節中加入了兩組三連音的琶音,像晚風輕輕略過,增添了詩詞的意境。左手柱式和弦的波音仿佛像江水的水波,右手和弦的行進像是月光在水中的倒影,又像偶爾輕輕滑動的雙槳,配合演唱旋律的行進,用最簡樸的音樂,表達了詩人乘舟遠行的內心情感。
三、《峨眉山月歌》兩個版本的演唱探究
(一)羅忠镕版《峨眉山月歌》
在演唱羅忠镕版本時,首先在譜面上的全曲速度標記是Lento(慢慢的),引子部分鋼琴伴奏左手旋律以很輕的十六分音符慢慢引入,這里左手的十六分音符是十個音作為一組進行的,劃分出來不在完整的一小節里,右手的和弦音與左手相同的音是不對位的,所以在聽前奏時,要將引子作為整個的部分來聽,根據標記的強弱力度變化與重音,調整呼吸,不能單獨數小節數來算什么時候該演唱。第一句演唱和鋼琴伴奏都以弱的力度開始,但在演唱“峨眉”時,聲音要開口掛在位置上,不能虛聲,隨著樂句漸強將氣息推開突出音“山月”,展現峨眉山的巍峨雄偉,在“半輪秋”處力度漸漸弱下來,終歸是夜晚,展現了詩人對所見遠處景色的贊嘆。第二句全句用中弱的力度演唱,音域沒有跳躍,像低頭看這水中的流水和月影,在左手伴奏模仿流水的襯托下,在“水”處,做了三連音的處理,在前面十六分音符處不要趕節奏,平穩演唱,在三連音處可以稍作漸強再收音,演唱時保持力度,掛住頭腔位置。第三、四句,根據力度標記突出情感,保持氣息的流動,雖然演唱的旋律結束了,但要讓情感和鋼琴伴奏一起結束。
(二)趙季平版《峨眉山月歌》
在演唱趙季平版本時,樂譜在最開始便給出了“古典風”的風格要求,鋼琴伴奏和演唱者要想象置身于那個時期的場景中,鋼琴伴奏可以更偏向于古琴彈奏的感覺。整首作品中沒有過多的音樂術語標記,但每一個音樂術語出現的地方,都有該句獨特的魅力。在引子部分標出了弱的力度,鋼琴伴奏左右手的波音和和弦的行進就要收攏一些,每一個音彈清晰。開始演唱時,第一句要有夜晚縹緲的感覺,力度上控制,掛住頭腔高位置,像朗誦詩詞一樣演唱,每個字要準確,不能拖著音走。在第二句“江水流”處,注意旋律的空拍,不要趕節奏,旋律的音雖然低一些,并且加入了空拍停頓,但是在此處聲音位置不能掉下來。第二句結束后有三小節短暫的間奏,此時要聲斷而情不斷,如果情緒完全收回,那第三句很難將情緒宣泄出來。第三句“向三峽”處可以作一個漸弱的處理。樂曲一、二、三句中前半句用了同樣的音型,像在水中山和月的倒影一般,應著詩人的小舟,在月夜下行進。第四句“思君不見”處,隨鋼琴伴奏做漸強處理,要將二度裝飾音再提調說音的位置上,潤腔帶出來,該句中的“下”處可以做這個音單獨的重音處理,展現內心的宣泄。第二遍演唱時,情緒的處理可以稍作修改,與第一段的演唱形成對比。
(三)兩個版本演唱時音樂細節的共性處理
兩首同名作品,都是選自李白的古詩詞創作的藝術歌曲,在演唱時有一些共同的處理方式。比如在演唱作品前,可以先以戲曲中提調說音來調整要掛的頭腔位置,感受氣息流動中,聲音在體內的經過。開始演唱作品時,除了注意音高和節奏的準確以外,還要注意依字行腔,歸分每個字的聲韻母,按十三轍中的每一轍多次練習,每一個字咬準確,不能含糊帶過。演唱中除了要注意以情帶聲外,還要注重表情在演唱過程中的運用,在這首作品中不能夸張的表現愁和哀傷,作品本身并不是悲情歌曲。同時,演唱者情緒的表達要與鋼琴伴奏相結合,兩首作品都運用傳統民族調式,在力度、音樂細節和感情處理上要有別于西方藝術歌曲的處理方式。
四、總結
《峨眉山月歌》是中國優秀詩詞文化的組成部分,無論是羅忠镕先生創作的版本,還是趙季平先生創作的版本,都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民族調式,都是古詩詞歌曲與音樂的完美結合,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讓更多的學者接觸、學習古詩詞歌曲。演唱者在表現古詩詞歌曲時,要注重對古詩詞歌曲意境和韻味的把握,注意區別于其他聲樂體裁的細節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