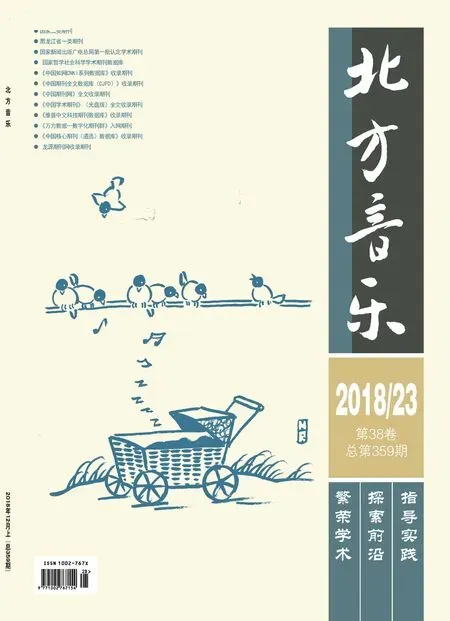瓦格納“整體藝術(shù)”觀對音樂劇的影響
張宇航
(江蘇省南京師范大學(xué),江蘇 南京 210046)
瓦格納所表達的“整體藝術(shù)”觀,是對藝術(shù)觀念的一種強調(diào),將音樂、表演、戲劇以及舞臺的布景等藝術(shù)元素進行了有效融合,這種藝術(shù)觀念對未來的藝術(shù)發(fā)展具有很強的預(yù)見性,對戲劇的內(nèi)涵進行了充分表達,不僅有效地體現(xiàn)了音樂劇的魅力,還促進了音樂劇獲取持久活力的生命力,而瓦格納“整體藝術(shù)”觀對音樂劇有著怎樣的影響,就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內(nèi)容。
一、瓦格納“整體藝術(shù)”觀概述
整體藝術(shù)的觀念是一種19世紀時期具有的時代意識和精神,它代表著浪漫主義中的“合”理念,此觀念表達把各門藝術(shù)進行一體化的融合,其于當時文學(xué)以及繪畫等藝術(shù)領(lǐng)域都有著一定程度的體現(xiàn)。這種整體藝術(shù)的觀念是建立于瓦格納對“整體”藝術(shù)觀念的重視,借助一定的手段將人群聯(lián)系于一起,達到比單個個體更加自由和全能的表現(xiàn),運用不同感官的人比單個官能表現(xiàn)的人更加全能,能夠?qū)崿F(xiàn)各門藝術(shù)間的有效整合轉(zhuǎn)化。比單個形式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也更加自由,通過整體性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和熏陶,才能促進整體、全能的產(chǎn)生,而瓦格納這種整體藝術(shù)的觀念的實現(xiàn)也是需要具有過程的,其成熟時期呈現(xiàn)于《塔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以及《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等音樂劇座屏中,于早期德意志的浪漫主義形式歌劇內(nèi),也已逐步的體現(xiàn)了整體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理念。自《漂泊的荷蘭人》起始,首先于宣敘調(diào)拓展和發(fā)展方面進行體現(xiàn),盡管其歌劇仍然還遵循著意大利的歌劇分曲,借助宣敘調(diào)拓展,實現(xiàn)戲劇良好連續(xù)性,還體現(xiàn)于分曲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連綴體的創(chuàng)作,這在《羅恩格林》的音樂劇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有效體現(xiàn)[1]。
二、瓦格納“整體藝術(shù)”觀的實現(xiàn)
音樂劇整套機構(gòu)主要有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以及舞曲構(gòu)成其骨架,詠嘆調(diào)與舞曲則是歌劇華而不實最主要的表現(xiàn),也是歌唱家以及舞者進行炫技的主要手段,藝術(shù)表現(xiàn)比較矯揉造作和浮夸,在劇情宣敘調(diào)的陳述中也不完全對戲劇進行服務(wù)。在歌劇藝術(shù)發(fā)展歷史中,有很多歌劇著名的作曲家,比如,格魯克以及韋伯等,而從瓦格納藝術(shù)觀念來看,他們都沒有實現(xiàn)藝術(shù)的整體性,即便是最有天賦音樂天才莫扎特,其創(chuàng)作若不服從戲劇安排,則也不可能實現(xiàn)出整體藝術(shù)效果。眾多作曲家都在拼命進行對歌劇藝術(shù)的追逐,來體現(xiàn)自身藝術(shù)的表現(xiàn),但他們大多都停留于藝術(shù)的形式化表現(xiàn),眼內(nèi)被音樂充滿,而詩人的角色則被忽視和棄置,歌劇戲劇的內(nèi)容僅僅作為他們音樂展現(xiàn)工具而已,這也就導(dǎo)致歌劇如同藝術(shù)表演秀形式。因此,作曲家一定要重視詩人角色的作用,在作曲家和詩人進行有效的合作中,方可實現(xiàn)對音樂戲劇的寫作形式和內(nèi)容深度的不相符問題的解決,如果各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一致是對戲劇目的進行服務(wù),以這種形式進行聚攏,就真正的體現(xiàn)了整體藝術(shù)的觀念[2]。
三、瓦格納“整體藝術(shù)”觀對音樂劇的影響
(一)貫徹戲劇詩樂舞共鳴的中心理念
瓦格納創(chuàng)作了很多的優(yōu)秀劇本,劇本充分地體現(xiàn)了詩的內(nèi)涵,并且其對歌劇內(nèi)的詠嘆調(diào)以及宣敘調(diào)分曲的模式進行了變革。其詠敘調(diào)的創(chuàng)作類似于說和唱,對詠嘆調(diào)和宣敘調(diào)交替使用進行了代替,從而對音樂中斷問題進行了解決,對分曲的結(jié)構(gòu)造成音樂限制進行了打破,使觀眾能夠置身在完整戲劇感受中。舞蹈于瓦格納的樂劇內(nèi)并不是一種宏大芭蕾的形式,如果是以舞蹈當做核心布局的話,會對“整體藝術(shù)”表現(xiàn)進行影響,其對舞蹈藝術(shù)展現(xiàn)更多是通過舞臺演員肢體上的動作完成的,音樂和劇情有效的配合下,演員肢體的動作一定要符合戲劇表達內(nèi)容和形式,和音樂律動具有良好的呼應(yīng)關(guān)系。
(二)主導(dǎo)動機的戲劇提示效果
主導(dǎo)動機將人物、場景以及事件等進行標簽式設(shè)置,這樣就會將戲劇進程向觀眾時刻提醒,從而實現(xiàn)樂劇的整體性表現(xiàn),只有對戲劇被主導(dǎo)動機進行有效的掌握,方可實現(xiàn)對戲劇的深入把握,融入到戲劇的情境中。這種音樂的表現(xiàn)手法于《指環(huán)》戲劇中表現(xiàn)十分明顯,主導(dǎo)動機如同針線將散亂內(nèi)容進行有效的連接。比如《萊茵的黃金》的前奏曲,在萬物復(fù)蘇、混沌初開表現(xiàn)上,就使用了神秘感bE大調(diào),并伴隨調(diào)式主音的bE音的長音形式進行體現(xiàn),奠定了整部樂劇表現(xiàn)的基調(diào),其調(diào)式的主音維持有四小節(jié)時間,后第二聲部則用主音五度音的bB音來緩緩進行體現(xiàn),一直和主音持續(xù)有12小節(jié)長音,從而體現(xiàn)出一種寂靜荒蕪之景。在《萊茵的黃金》的第一幕中,也出現(xiàn)了“黃金”的動機,使用G大調(diào)的主和弦中三音采取跳進表現(xiàn),使用小號金屬的音色來進行黃金質(zhì)感的表現(xiàn),其音色明亮正好和明亮萊茵河進行配合[3]。
(三)歌劇結(jié)構(gòu)的連續(xù)性
對于歌劇結(jié)構(gòu)的連續(xù)性,在《羅恩格林》歌劇中就得到了有效的體現(xiàn),是一種連綴體的歌劇形式,在此歌劇三幕的十一場內(nèi),其歌曲主要是以詠敘性旋律作為主旋律,并沒有構(gòu)成相應(yīng)獨立分曲的形式,只有在埃爾莎和羅恩格林以及奧特魯?shù)轮饕巧膬?nèi)心獨白中有用到,和同連綴體的歌劇相呼應(yīng),歌劇對序曲進行摒棄,在三幕每一幕前都配有相應(yīng)的“前奏曲”,主要有管弦樂進行演奏,它們并不對情節(jié)進行預(yù)示,僅僅是一種進行音畫式描述。比如在第一幕中主要講述了弗里德里克進行控告,以及羅恩格林拯救埃爾莎,前奏曲則是以圣杯動機進行陳述和構(gòu)成發(fā)展的,圣杯的動機主要由八小提琴于高音區(qū)進行奏出,從而呈現(xiàn)出圣杯具有的靈性,圣杯的動機有三次重復(fù),伴隨的樂器在不斷的增加,具有一種層層遞進的感受,對圣杯榮耀進行了展現(xiàn)[4]。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整體藝術(shù)觀是瓦格納歌劇美學(xué)藝術(shù)中的重要體現(xiàn),這也是瓦格納歌劇創(chuàng)作中的主要體現(xiàn),這種美學(xué)觀念是一種實現(xiàn)歌劇內(nèi)容和舞臺內(nèi)涵的綜合體現(xiàn),對后期的歌劇藝術(shù)發(fā)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