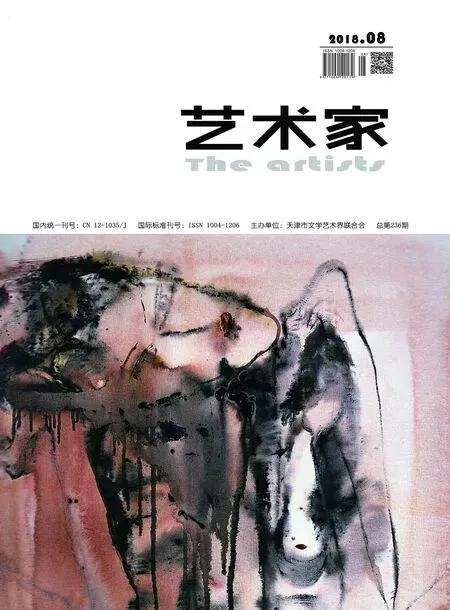立象盡意——蔡智寫意花鳥畫藝術(shù)語言探源
□冀雪瑩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
蔡智寫意花鳥畫藝術(shù)語言的形成,與其鮮明的漓江畫派寫意特征和自己對于花鳥畫與生活間的自在領(lǐng)悟息息相關(guān)。特別是,其藝術(shù)語言形成的根源還與其本身所堅持的“立象盡意”的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不能分割。憑借多樣深厚的對于寫意花鳥畫及其藝術(shù)理論的深刻理解與準(zhǔn)確研究,形成了蔡智寫意花鳥畫中意象美的藝術(shù)語言。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中國畫學(xué)院副院長蔡智(號一泉,1963-),于2017年3月13日在中國國家畫院成功舉辦了“立象盡意——蔡智中國畫展”。使得這位從事美術(shù)教育三十多年的“老教師”,重新進入到理論批評的“現(xiàn)場”。他的作品風(fēng)格在三十多年間總體是一個不斷上升的過程。這個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根植于他對于以廣西為代表的西南地區(qū)山水植物的情感所得;另一方面,則是他對于中國畫理論以及中國哲學(xué)中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的美學(xué)思想與當(dāng)下創(chuàng)作進行融會貫通的嘗試。這個嘗試通過其個展及“立象盡意——蔡智中國畫展”研討會的舉辦,獲得了業(yè)內(nèi)的肯定。
蔡智在《中國畫修養(yǎng)隨感》中曾援引石濤:“筆墨當(dāng)隨時代,文章自有風(fēng)神”來概括自己對于中國畫的學(xué)習(xí)和創(chuàng)作的理論感悟。在蔡智這里學(xué)習(xí)中國畫及其背后的哲學(xué)理論與研習(xí)大師的杰作一樣重要,而且筆墨還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進步,這種進步不是取消筆墨,而是獨辟蹊徑,通過汲取美學(xué)和文藝?yán)碚摰臓I養(yǎng)來對當(dāng)下的筆墨進行一種新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是建立在蔡智對于創(chuàng)作、對于生活自下而上的感悟之中的。不僅國畫,每一個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及其藝術(shù)語言都根植于藝術(shù)本身所生長的土地,不斷自我汲取其中營養(yǎng),并且能在此基礎(chǔ)上繼承創(chuàng)新。因此,只有從蔡智對于中國畫及其理論的脈絡(luò)中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其作品背后意象美的藝術(shù)語言真正的內(nèi)涵。
蔡智將中國國家畫院美術(shù)館中舉辦的寫意花鳥畫展覽定名為“立象盡意”,在畫家自己看來,是有深刻的理論淵源的:展出命名,是以取法萬物形象之手段,追求“意”的極致表達,更映現(xiàn)出以形達意上的不懈追求。蔡智將最早出自《易傳》的“立象以盡意”,經(jīng)過自己的理解將“意”和“象”自然聯(lián)系起來。可以產(chǎn)生一種“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審美,因此在這里對于象,就不僅僅是一種呈現(xiàn)與視網(wǎng)膜上的“眼中之竹”,而是成為與“意”息息相關(guān)的一種特殊“物象”,形成一種《系辭》中所言的:“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易·楚辭下》)”的文藝狀態(tài)。這與蔡智常說的“文章自有風(fēng)神”是一致的。一般而言,“象”是感性具體的,是對現(xiàn)實事物的一種模擬、反映;它不是直言藝術(shù)形象,但卻可以通向藝術(shù)形象。可見“立象以盡意”,就是說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不是單純?nèi)バ蜗竺鑼懀€要追求那些“言外之意”。這樣就把藝術(shù)的形象特點與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統(tǒng)一起來。子曰在《周易·系辭上》中又將:“圣人立象以盡意“的問題,發(fā)揮成為“觀物以取象”。從這里實際上就獲得了一種文藝創(chuàng)作(包括繪畫)的一種理想的觀審方法。雖然孔子名沒有直接展開論述具體如何進行“觀物取象”式的創(chuàng)作,但是他這種“助產(chǎn)術(shù)”式的方式,確實啟發(fā)了后人對于藝術(shù)觀察與創(chuàng)造之間聯(lián)系的了解。
黃格勝先生在談蔡智的作品時是這樣認(rèn)為的:“蔡智的造境能力自不恃言,他筆墨縱橫,撒豆成兵,指哪兒打哪兒,且造型生動,色彩艷麗,而不火不俗;畫面可松可緊,可滿可疏,活潑燦爛,傳達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健康人生態(tài)度和樂觀瀟灑的情致。”這樣的藝術(shù)感受,是與其對于生活的體察和憑借對自然景物感受的認(rèn)識而獲得的,就像朱光潛先生在《談美》中所言:“個人的情趣不同,所以各人所得于景物也不一致。”蔡智就是在這樣的對于自然景物的體察感受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寫意花鳥畫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語言,并且以此為基礎(chǔ)不斷發(fā)展、深化、豐富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