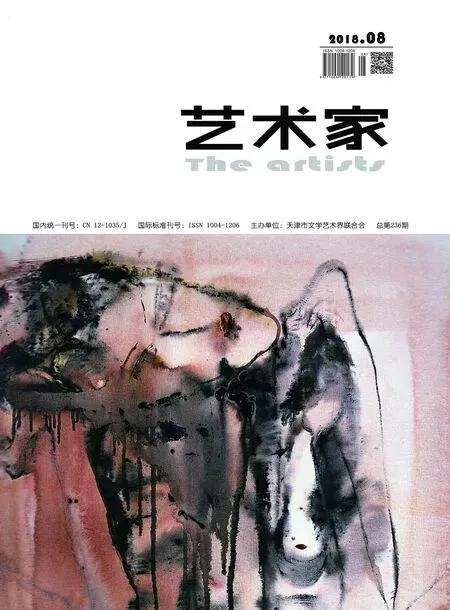淺談寫實油畫中形的透視關系
□張 聲 四川省服裝藝術學校
透視關系是品評畫作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自文藝復興至今,已有諸多的油畫大師對形的透視做了深入的研究,列奧納多·迪·皮耶羅·達·芬奇在《畫論》中提到,透視學就其與繪畫的關系而言可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線透視、空氣透視、隱沒透視。達·芬奇提出線透視的功能在于研究視線,并借測量發現等距物體間隨空間向遠處推移會縮小多少。物體要符合畫面場景的透視法則,它的形應隨著空間的縱深而產生變化,我們說畫面里的形是否準確,即透視變形是否準確。
一、大場景繪畫中的透視關系
在達·芬奇的油畫《最后的晚餐》中,作者主觀地將畫面中的人物分成四組,把主要人物放在畫面的中心位置,錯落有序地排列分布,一組組人物的穿插、重疊使每組人物之間的空間都得到充分表現,而人物在形體比例上比前景人物有了透視縮形。作者在這幅畫中運用到了隱沒透視:遠處窗戶中的風景隨空間的推遠而變得模糊;空氣透視:遠處山的固有色削弱而傾向于空氣的顏色;線透視:墻面的方形、天花板的方格、餐桌上的餐具都經過精密推算,被準確安排在畫面中,構成上下左右向中心集中的透視關系,使每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在達·芬奇之前,還極少有畫家把透視法則用于如此宏大的構圖之中。
拉斐爾的油畫《雅典學院》則將背景鋪成為向遠處縱深展開的高大建筑拱門,營造出極其宏偉、莊重的室內場景,畫面中匯集了不同時代、地域、學派的精英學者,作者巧妙運用線透視來增強畫面的空間縱深感,使拱門和兩側石柱在透視線上向中心透視點層層推遠,一直通向天際,顯示出博大與神圣的格局。學者被對稱地、富有節奏地安排在臺階兩側,錯落為前后兩組,通過前組人物和后組人物的形的疊壓和透視大小、虛實的變化,將空間向消失點逐漸推移,營造出深遠的視覺空間。
風景畫通常由近景、中景、遠景組織構成完整的大場景,往往涉及更為復雜的透視關系。如荷蘭畫家梅因德爾特·霍貝瑪的油畫《林蔭小道》中,作者嚴格地采用了焦點透視來構建畫面,給觀者以強烈的空間縱深感。最能帶動透視推移的是分布在道路兩側的細而高的樹,它們相互參差錯落地排列在透視線上,既有十分對稱的透視變形,又有各自在形態上的豐富變化,每棵樹都充滿了個性。作者在構圖時有意地組織了很多三角構圖,并將樹和路地形緊密的安排在這些三角構圖的框架里,這種三角透視無疑是對空間最好的概括。
二、創作中的透視問題分析
在創作過程中,透視始終是造型、構圖上的難題,由于透視的理論體系龐大且枯燥,所以也成為大多數人較難把握的難點。如刻畫人物時,往往把握了大的形體關系,卻無法準確掌握骨骼和五官的內部透視變化;在風景寫生中,常常關注于色彩而忽略了形的透視的基本規律,造成空間的混亂。其實把握人物、建筑和樹木等事物近大遠小的透視變化才是表達空間深度的關鍵。還有人體寫生中的諸多難題,如一個平躺的人體,當我們看到人體透視特別大的時候,人的身體長度會被壓縮到很短的距離,而這段距離在畫面中顯得特別重要,我們常用形的相互疊壓來表現各結構間的距離,可往往會忽略在這個過程中還有透視縮形,隨著物體離我們視線越來越遠,逐漸向消失點縱深,形體也會發生變化。
經不起推敲的形體在畫面中是極不和諧的,而要準確地把握精密的透視關系,做到絕對的準確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繪畫畢竟不像方程式那樣需要科學的精密計算。如何在透視并非絕對準確的條件下,使畫面看起來和諧而豐滿,這對畫家主觀的畫面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對形的透視的思考
在深入研究中,筆者對形體透視變形有了些新的體會。如大師們在保證透視基本準確的情況下,對表現對象的動態和透視做出適當的夸張,從而削弱對形的細究。
當描繪一幅激烈的運動場面時,我們可以主觀地對人物動態做出適當的夸張、變形,從而更能體現運動的張力和力量感。如在畫家彼得·保爾·魯本斯的油畫《強劫留西帕斯的女兒》中,肢體處于激烈的扭轉運動中,并產生了明顯的透視,形體的疊壓和穿插讓人感到場面的混亂和激烈,瞬間捕捉的畫面充滿了動感,使觀者立即便產生緊張的情緒。再如在周大正的油畫《劈山引水》中,雖然奔流的河水、遠處的公路、從山上垂下的繩子都是次要表達的事物,作者卻通過透視變形細微表達其縱深感,從而營造出富有力量感的勞動氛圍。從主體人物和環境的刻畫可以看出作者在構圖時對透視的周密推敲和巧妙運用,將復雜的場景梳理得井然有序,使畫面空間更加真實,為筆下刻畫的人物賦予了力量感和宏偉感。
透視不僅影響著畫面氛圍的烘托,也帶動著觀者的感官神經。如要表現一幅寧靜的場面,我們可以將形的透視變化處理得柔和些,這樣就能達到平靜、緩和的效果。如畫家吳憲生作品里的女人總能給人以柔美、平靜的感受,雖然也帶有透視,但與之前的幾位畫家所表達的意境截然不同。形與形的穿插都流露出婉轉的抒情氣質,他對線條的組織將人物的形體透視和畫面柔美感詮釋得淋漓盡致。筆者在對透視變形的實踐和研究中會發現許多令人驚喜的畫面表達,值得細細品味和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