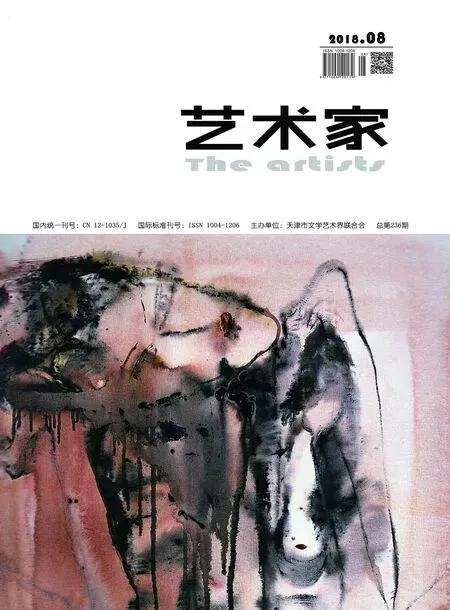淺談雕塑藝術批評——理性與感性之間
□馬蕭涵 沈陽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系
今天的雕塑藝術家們都已經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以作品說話,以事實說話,比什么東西都具有說服力。簡而言之,雕塑家是以雕塑作品的形式與社會性,與欣賞者進行交流的。然而,雕塑藝術家想進一步提高個人的雕塑藝術水平,就必須對深藏在思維深處、模糊的所謂理性的東西進行自我辨析,而這,需要外界的議論和批評。
可以說,只有形形色色的“批評家”熱衷參與,雕塑藝術才可以進入意識形態領域,它的藝術思想和精神屬性才可以發揮真正的作用。批評家在使雕塑作品貶值或增值的同時,也能引導雕塑家在創作時進行理性和感性的分析,從側面提高了雕塑作品的質量。
一、感性認知
中國古代雕塑藝術批評沒有像現在這樣系統和成熟,古代雕塑藝術品主要由手工藝術高超人士擔當制作,參與批評的人則是由帝王將相,王侯貴族等統治階級所擔任,他們的欣賞標準就是批評標準,當然也有遵循著中國傳統的以意象為主的藝術形式。宗教雕塑自有其整套的創作與批評的體系,如信教的人士和教主等群體是雕塑批評的主體。雕塑家、雕塑家兼理論家、專門的理論家及詩人、學者這些知識分子的批評帶有極濃的文學(文化)氣息。唐代雕塑家楊惠之一開始是和名畫家吳道子師法張僧繇派的繪畫,后來吳道子成了眾所周知的畫家,他便放棄了繪畫專攻雕塑,其作品合于相法,十分傳神,塑造技術和千手千眼觀世音的造型對后代有著深遠影響,乃至在各地往往都有一些雕塑被附會或傳說為他的作品。當時的評論家評論楊惠之“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由此可見,楊惠之原本繼承著張僧繇的“筆才一二,象己應焉”中國傳統繪畫的意象藝術表現手法,加之長久以來自成體系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然將吳道子的繪畫和楊惠之的雕塑共同比評,就如張彥遠所說“六法具全,萬象必盡,神人假手,窮及造化也”[1]。
二、理性基礎
在古代西方,雕塑家主要是以雕塑創作感想筆錄的形式進行藝術批評的,但藝術批評的中堅力量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批評家、理論家,甚至是哲學家。從一開始,西方的雕塑批評就具有很強的哲理性。古代西方很早就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系統學科,這為研究學問和社會批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古代西方哲學家往往是把美術作為哲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他們的哲學理論常常對古代西方雕塑批評產生很大的影響[2]。
三、融合
雕塑就如繪畫一樣,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雕塑批評已經建立起了系統的理論體系,且產生了獨立的批評體制,但這種批評機制仍沿襲著西方古代藝術批評的傳統,西方社會層出不窮新的哲學觀點仍然是對藝術批評理論產生極大影響的理論力量。譬如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觀點、“利比多情結是藝術創造的原動力”的觀點、尼采的“意志”說、薩特的“存在主義”等對西方藝術批評乃至對西方現代派藝術的產生和發展都具有極大的影響作用。但在此時,獨立的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學說也產生并建立了起來,這是時代的進步[3]。E·H·岡布奇的《藝術與幻覺》、H·沃爾夫林的《藝術風格學》、魯道夫?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蘇珊·郎格的《情感與形式》,以及羅蘭·巴特、德里達等人有關結構、解構等理論體系對現代西方雕塑乃至整個西方現代藝術的拓展、擴張、異化、分裂有著直接的作用,或促進或指導。在西方傳統雕塑異變成西方的現當代藝術的過程中,西方藝術批評中的理性意識,理論探討對西方雕塑藝術創作中的感性形象的立體構成產生了十分特殊的作用[4]。正是在理性和感性相互探討、相互融合中,雕塑藝術才得以向前繼續發展。正如批評家波西加(1906——1969)評論雕塑家賈克梅地的創作“自由聯想,內心獨白,時空錯亂”,這種舍棄了古典主義情節雕塑創作的完整性、豐富性、連貫性,試圖完成一場不讓目光停留的不穩定運動,被波西加稱為借助于自身的“內心的真實”“心理現實”的內化為一種“純粹的真實”或“最高的真實”的思想轉植。從哲學與社會思潮的角度看,此類雕塑藝術創作作品更具有從非理性中轉讓、回收和重復的特征,直至完全有理由呈現內心理性,并進入客觀真實,這不就是理性和感性相互探討、相互融合的最好范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