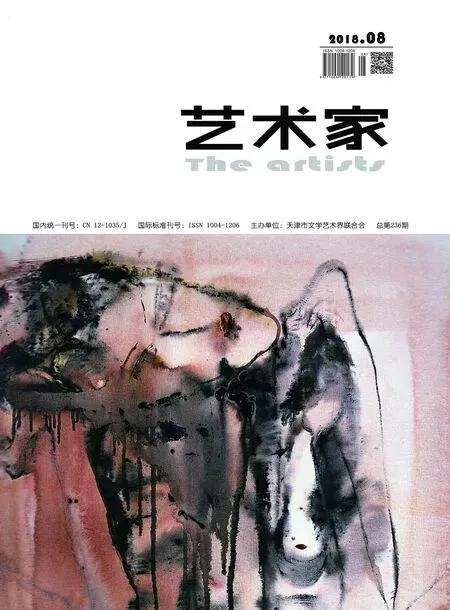當代中國畫教學之流弊
□郭元波 廣西藝術學院
中國畫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精髓和藝術魅力,它不同于西方繪畫,以特有的藝術語言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成為東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和象征。無論是“成教化,助人倫”的政治作用,還是文人雅士的獨立審美取向,中國畫的教育教學問題從古至今都備受重視。1917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再次推動了中國畫教學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藝術院校(還有一些綜合性大學)為中國畫的發展也都做出了貢獻。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在現行的中國畫教學當中,似乎還存在一些問題和弊端。下面筆者結合自己學習中國畫的經驗,談一點看法和認識。
素描在中國畫教學當中是不是具有絕對的必要性,一直飽受爭議,討論甚多,筆者也不敢妄下定論。但是在中國畫當下的教學體系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學習過素描,在西方素描(透視學)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學生在中國畫的創作中過度追尋體積感和光影效果,從而使傳統的中國畫變了味,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點。
線是中國畫的精髓和靈魂所在,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中國畫的線都有不可替代性,它承載著作者的情感和人生體悟,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線條的粗細緩急都有著不同的情感表達,但是,在當代的工筆畫教學中,有太多的學生一味追求線條的細,可謂是細如牛毛,無細不歡。他們認為“細”才能體現自己的技術高超,體現出自己對毛筆極強的掌控能力,其實不然,中國畫里最不缺的就是技術,而最缺的是情感。情感的表達往往就是通過線條的變化來體現的,否則古人為什么會總結出“十八描”呢?因此,一味追求“細”線,似乎就非常欠缺表現力了。
臨摹是學習中國畫的一個重要手段和過程,學習大師的作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許多學生在剛接觸國畫時就直接著手名家大寫意(如齊白石、潘天壽等),這一點筆者著實不敢茍同,即使他們臨摹的再像,那也僅僅是外表的像,并沒有精神層面的內涵。名家的大寫意看似笨拙,實則蘊含著他們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生活情感。沒有長時間的生活閱歷和積累是絕對畫不好大寫意的。因此,基礎較弱者可以結合自身特點,選擇相對合適的名家臨本練起。名家的大寫意我們早期可以通過讀畫、品畫來間接地學習和體會。讀畫能提高學生的審美,開闊學生的眼界,讓其知道什么是好畫,為什么是好畫。如果在臨摹前就有了這樣的思考,那接下來的學習就會事半功倍了。
在當代的中國畫壇名家輩出,風格迥異,自然而然也影響著學生的創作思路和方向。一些學生因某一名家在國內的影響力而去學習他的優秀東西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慢慢產生了崇拜與排異思想,甚至放棄了傳統名作的學習,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現象。當代名家的作品無論多么優秀都肯定是以傳統為支撐點,否則他們的作品根本立不住。中國畫中最精華的東西必定是在傳統佳作里,潘天壽先生所講的“學畫,要學高不學低”值得學生們去思考。
由于生活年代的原因,一些教師對于前沿性的中國畫學術問題接觸的不多,阻礙了他們藝術思想的更新,導致其因循守舊,固守傳統,缺乏創新,影響了學生的藝術創作軌跡。徐悲鴻先生曾提出中國畫改良論不就是他在那個時代立足于傳統對中國畫的改革創新嗎?石濤也曾提出“筆墨當隨時代”的先前口號。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能以偏概全,藝術是沒有對錯之分的,至于如何拿捏傳統和創新還需我們自己去斟酌。
有些學生認識到了中國畫所應有的當代性和創新性,就把西方的平面構成與色彩構成等藝術形式融入自己的畫面進行了現代意識的處理,這無疑是進步的。但是,他們并沒有真正認識和理解這些構成形式,這種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空洞表現只能糊弄外行人,并不能引起觀者的共鳴。
寫意是中國畫中最具表現力,最易抒發情感,也最具代表性的,幾乎所有的古今國畫名家都是以寫意畫揚名的,但是中國的寫意畫發展到現在似乎出現了青黃不接的尷尬局面,原因可能是由于多年來各大美術專業院校的學生研習寫意畫的人越來越少了,更多的學生選擇了工筆,目的是為了更容易參展獲獎,而本來喜歡寫意畫的學生也在為了所為的目的隨波逐流,違背初心。試想帶有強烈功利性的作品怎么可能是好作品,怎么可能讓人為之動容?學校評獎評優看獲獎,畢業找工作看獲獎等一系列問題阻礙了學生的專業發展。寫意畫沒有幾十年的積淀確實難出好作品,然而如何提高青年學生的寫意積極性,是一個關注焦點。
中國畫教學的發展經過了幾輩人的努力,一大批老藝術家為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也出現過激烈的學術辯論,正因如此才推動了中國畫的更進一步發展。以上內容僅僅是個人的淺拙之見,若有不對之處,還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