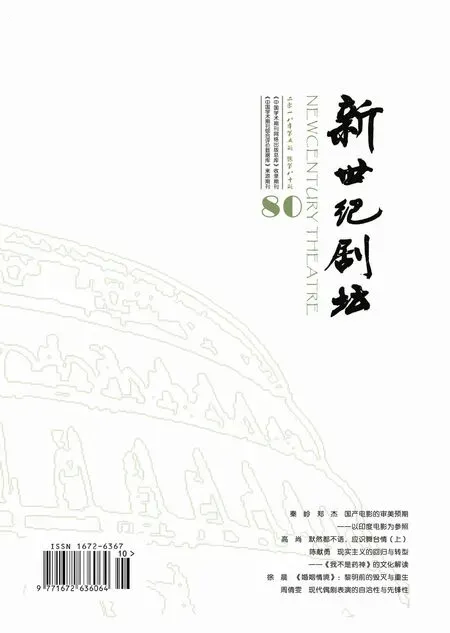聚焦“真實”
——淺談國產犯罪片的“現實主義”
基于討論會“第幾代導演能救中國電影”的話題,我選擇從國產犯罪片入手淺談中國電影的發展。近年來,犯罪題材因情節的震撼性和視覺的沖擊性而成為國產電影的“新寵”,電影的多元化進程與觀眾的觀影需求推動了犯罪片的發展。但許多國產犯罪片在社會問題的真實性、對犯罪事件的批判性以及對人性的挖掘上仍不夠深入,導致影片脫離了社會現實,不能達到針砭時弊、寓教于“影”的效果。影片的敘事是內核,彰顯電影的藝術性,國產犯罪片應以中國社會為本,用中國化的影片風格作為區別于好萊塢犯罪片的工具;而電影作為娛樂活動最終要面向觀眾,故國產犯罪片要開辟出一條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的道路。本文從犯罪片的現實主義敘事和犯罪片商業化兩方面淺談國產犯罪片要立足中國社會本身的重要性。
一、類型化的現實主義敘事
類型電影,是指由不同題材或技巧形成的不同的影片形態,流行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好萊塢。犯罪片是最具代表性的類型電影之一。在美國,犯罪片又稱黑幫片。黑幫片與社會問題具有某種關聯。[1]要明確的是,類型片是一種影片的創作模式。犯罪片的類型模式必須與犯罪事件緊密相連,而犯罪活動則源于現實社會。電影的“現實主義”是指影片內容盡量客觀,強調真實性。在以消費為主導的華語影壇,國產犯罪片的敘事應與觀眾的審美相符。因此,國產犯罪片要立足本國現實社會才能充分體現犯罪片“現實主義”的特點。
以平民化的人物形象奠定現實基調。戲劇理論家貝克認為“類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鮮明,以至于不善于觀察的人也能從他周圍的人們中看出這些特征。這種人物每一個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關的特征來概括”。[2]“定型化的人物形象”是類型片的基本特征之一,作為類型片之一的犯罪片當然不能缺少這一重要元素。這一定律是由美國早期類型片所歸納的,但應用于中國土壤時勢必會發生改變。好萊塢推崇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我們看到好萊塢犯罪片的主角常為聰明的探長、高智商的博士或身手不凡的特工等。中西文化的迥異之處便在于后者是精英文化,強調個體強者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而前者則是平民文化,強調“以民為本”。所以當如《心理罪》《嫌疑人x的獻身》等“優于常人”的主角設置出現在國產犯罪片時,就會給觀眾以一種不切實際之感。但像《暴裂無聲》中的啞巴礦工,《白日焰火》中落魄的警察,《暴雪將至》中好高騖遠的保衛科干事等,這樣有“缺陷”或“弱點”的普通人成為主角時,就有如影片在窺探現實社會的某一個角落,好人與壞人的界限不再清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復雜的個體,人物的復雜性使其形象更為真實,影片的“現實主義”風格也更為強烈。
在現實化的敘事題材下挖掘影片主題。好萊塢犯罪片通常以一樁犯罪事件始末為敘事背景,講述罪犯的落網過程。國產犯罪片應在好萊塢模式的基礎上從本國社會中進行題材選擇,對中國社會的各種現象進行描寫,打造本土化的犯罪片。首先,在非典型的社會中選取典型的事件為題材。非典型的社會就是中國社會,它是客觀存在的,應從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中選取具有代表意義的犯罪題材,如拐賣人口、復仇殺人等,從一樁樁犯罪事件中窺探人性的善惡,在“現實主義”中批判犯罪事件。其次,本土化的人文關懷與對人性的解讀是將犯罪片“中國化”的表現。好萊塢的犯罪片更崇尚于表彰正義者的價值,相對而言鮮少重視對人倫道德的評判。而國產犯罪片因角色的設置是充滿“人情味”的,故在中國社會背景下挖掘犯罪片的情感線索是體現“現實主義”的重要方式。如影片《黑處有什么》雖然以小鎮的連環殺人案為背景,但其內核是講述一個少女在那個年代的成長過程、青春懵懂;《湄公河行動》改編自真實的邊境中國船員遇難事件,實質則表達了中國為緝毒事業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體現了緝毒警察無私犧牲的高尚品質;《烈日灼心》的心靈救贖;《追兇者也》中對人性的真實刻畫等,都是在現實主義的故事中挖掘深層次的主題思想。
用非線性的敘事方式營造懸疑氛圍。非線性的敘事方式作為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敘事手段,開始逐漸應用于電影敘事中。非線性敘事即打破經典的單線敘事,多條線索交錯出現。對于犯罪片而言,非線性敘事方式的使用更有利于揭露社會現實。因為對一個犯罪事件,通過對它發生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的多方位展示,可以更加真實地還原事實。使用全知視角可以使代表正義和邪惡的兩條人物線索共同分擔劇情,將整個犯罪事件充分統一起來。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觀眾比主角所知還多,全知視角使影片更富于現實性。如《樹大招風》中的三線并置;《追兇者也》中類似日本經典電影《羅生門》的“多人視角鋪陳故事”;再如《暴裂無聲》也是從正反兩方面敘述劇情,但片中的“懸念”即男孩的失蹤卻一直“懸而未決”,而導演另辟蹊徑地以屠夫的兒子來代表“全知”的視角,這樣的安排讓觀眾有恍然大悟之感:原來真相就在身邊。這大大體現了犯罪片“現實主義”的魅力。
二、商業主導的現實主義模式
“電影首先是一門工業,其次才是一門藝術。”[3]電影作為21世紀人們娛樂消費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商業性。電影的商業性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觀眾的審美心理,故導致了影片所關注的“焦點”的變遷。對犯罪片的模式而言,電影商業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為博取觀眾眼球而加入夸張的血腥、暴力等刺激性場面;為迎合審查與過分彰顯“邪不壓正”而削弱了影片結局的現實性;為探索新式的思維模式而扭曲了本該彰顯的社會責任意識。這也正是一部犯罪片在商業化的同時,與“現實性”產生矛盾的原因。如何將“商業性”滲入到“現實性”中,并仍然保留影片“關注現實”的內核,是當下國產犯罪片應該重視的問題。
商業噱頭服務于現實主義。動作場面的融入是近年來各國犯罪片的流行趨勢。各電影類型的相互融合是舊好萊塢邁向新好萊塢的影片特征之一,這使得各類型之間的界限不再清晰,這也是類型片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轉變。對于犯罪片而言,與動作片的相融就是其在轉變過程中最大的特征之一。犯罪片以犯罪事件為題材,在表現正邪兩立、善惡沖突的場面中,往往會出現暴力、血腥的打斗鏡頭。動作戲不僅應運而生于影片的商業性,更是增強犯罪片場面張力的“工具”。以《暴裂無聲》為例,張保民獨闖昌萬年辦公室的長鏡頭中,他一人與一眾保安進行搏斗,動作絲絲入扣,場面刺激性十足,動作場面充滿了商業噱頭。再如《湄公河行動》中的邊境槍戰,地雷爆炸、子彈橫飛等商業性因素的融入,使影片充滿了好萊塢大片之感。但如《冰河追兇》中的冰面打斗戲就給觀眾以脫離現實之感。商業性融入現實主義的過程,就是在考驗導演對于影片整體藝術性的把握程度,因為對商業噱頭的拿捏要以現實主義為基準,不能為追求感官刺激而與真實性脫節,應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表現“正邪沖突”的外在動作,以免出現嚴重脫離現實主義的浮夸內容。
“迎合有度”激發真情實感。影片結局如何在保留“現實性”的基礎上又被大眾及審查機構所接受,是當下國產犯罪片的一個重要問題。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強調“懲惡揚善”,并以此作為藝術創作中美好結局的一個原則。但過分伸張正義很可能導致影片結局遠離現實,因為“現實”就是“社會中確實存在無奈的事情”,應當直面現實社會中的“不合理”,而不應該予以回避。許多國產犯罪片為了結局力求善惡有報的“大快人心”而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合理性,造成了一種“虛偽感”。例如影片《烈日灼心》結局處,三個并非真兇的主角卻認罪與自殺,雖然導演旨在升華“自我救贖”的偉大主題,但這樣的邏輯安排卻顯得十分牽強。而《暴裂無聲》就以一種“好壞參半”的結局收尾。雖然昌萬年與律師分別因非法采礦和受賄被逮捕,但他們卻永遠地隱瞞了男孩被害的真相。隨著結局山谷無聲的暴裂,下層人民在權貴面前“失語”顯得更加真實,也正是由于這種現實的,甚至悲哀的結局才會激發起觀眾的情感。
思維探索彰顯社會意識。電影思維的僵化是當下國產電影的詬病之一。犯罪片的思維模式一旦固定,觀眾就會對之產生審美疲勞。思維的僵化會使觀眾對影片劇情“一目了然”,這便使犯罪片失去了懸疑的特點。故犯罪片導演力圖在犯罪題材的范圍內進行探索,以求在犯罪片中給觀眾帶來全新的觀影體驗與人文立意。以入圍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國產影片《大世界》為例,影片以動畫的形式展示了小城市里一樁犯罪事件引發的連鎖反應。影片不僅用方言、破舊的街景、日常的臺詞展現出了一個逼真的世界,向觀眾傳達了“仿真”的信息,其最精妙之處更在于動畫的形式與連環的結構,此創新之舉為影片贏得了國際上的贊譽。但過分探索犯罪片的思維模式會造成影片“失真”,從而沒有突出影片的類型特征,而成為不倫不類的混合體。以《澳門風云3》為例,影片試圖將犯罪片以喜劇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卻導致影片類型特征不明顯,從而使影片嚴重“失真”。
無疑地,國產犯罪片是華語電影可以蜚聲國際的一個突破口。《烈日灼心》的自我救贖、《暴裂無聲》的階級博弈、《白日焰火》理性與欲望的掙扎,無論是業界還是觀眾對這些國產犯罪片的肯定,都不僅是因為其縝密的懸疑邏輯或激動人心的動作場面,更在于它們聚焦了尖銳的社會現實,以“現實性”為準則,以中國社會為背景,在犯罪片的外衣下展現了一個個真實的中國故事。犯罪片應當來源于現實社會,又高于現實社會,它應該成為一幅充滿藝術韻味的社會圖畫,讓觀眾從光影中窺探社會的面目、洞悉人性的復雜,從而審視、反省當今我國社會仍存在的問題。未來,國產犯罪片能否植根于中國的本土社會,打造屬于本國的獨特風格,成為成熟的創作類型,并得到國際影壇的認可,還需中國電影人的努力。
注釋:
[1] 大衛·波德維爾,克莉絲汀·湯普森.世界電影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 喬治·貝克.戲劇技巧[M].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3] 邵牧君.西方電影史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