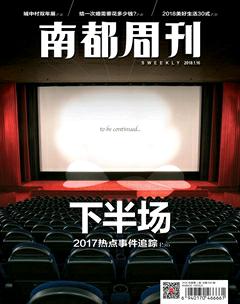為什么結婚彩禮會越來越高?
萬喆
20世紀70年代及以前,是大家普遍認為“沒有彩禮”的年代。實際上,當時男方要給女方買衣服等,也要到女方家送禮物。這已經是彩禮了,只是價值較低,尤其是與“陪嫁”相比。
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貨幣開始成為彩禮的支付形式。彩禮從數百到千元。嫁妝與彩禮開始趨于平衡。總體看來,彩禮所造成的負擔仍不算太重。
90年代后期,彩禮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數額迅速攀升,彩禮數目開始明顯超過嫁妝。而農村娶媳婦難也已經成為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局部區域范圍內,越貧困、越邊遠地區的農村婚姻要價越高。
從彩禮的歷史、演變、現狀來看,今天的彩禮問題,更多出現在農村,其成因有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迅速,跟隨心理不可避免。傳統小農生產方式下,生產節余很少,經濟分層的變動性較小,經濟水平較均衡,彩禮數量也相對穩定。改革開放后,農業剩余勞動力價值得以實現,貧富差距拉開。富裕家庭率先提高了彩禮水平,帶動地方婚姻規矩整體發生變化。
二是隨著家計模式發生變化,社區道德規范失去效用。在以農業為主要收入的家計模式中,社交范圍較局限,有限范圍內的道德規范約束作用大。通常,一地彩禮文化模式與當地經濟水平相均衡。女方若提出過分要求,就可能被詬病“這家人太難纏”,反而陷入被動。但當地域流動性加大,約束就自然被瓦解了。
三是供需缺口大,女方有“要價”基礎。當前適婚男女比例1.15:1,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萬,“供需”失調相當嚴重,男性求偶成功難度系數自然大大增加。而我國傳統思想中,男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女方當然有條件、有基礎向男方提出更高的財務要求。
四是社會階層固化帶來壓力,婚姻成為調節手段。當前,區域經濟、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仍然非常明顯,而社會階層固化的趨勢仍舊不減。一些家庭也將彩禮作為一種調整兒女婚姻的預設手段。對于農村貧困家庭而言,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因此“弱勢積累”現象較為嚴重,越窮的地方,要的彩禮越高;反之,一些條件尚可的家庭又希望通過高彩禮切斷與貧窮家庭的聯姻。
五是子女地位發生變化,代際關系失衡。當前,子女依賴父母的現象十分嚴重。這其中,有著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少子女所帶來的嬌溺,也有急劇城鎮化后父母外出打工對孩子的教育欠缺和親情愧疚,亦有兩代人兩種文化思潮兩種權利意識的錯位。農村一些兒子的婚姻負擔幾乎完全落在父母身上。
綜上所述,五個因素與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社會變遷迅速息息相關。
原因之中,有些是相對比較正常的。比如說有一定的競爭、攀比心態。彩禮存在,既有歷史文化基礎,也有社會經濟基礎,粗暴批判和武斷禁絕都意義不大。主要對策還是予以輿論上的引導,并加強相關法規細則的建設。
有些并非正常,但是已經在歷史演變中形成。比如說男女比例失調,目前國家生育政策已在不斷調整,相信將來會逐漸正常化,但短時間內恐怕還難以改變。
有些不正常。比如當今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呈現出的子女過于依靠父母,不愿意承擔相當的社會責任,甚至也不愿意承擔正常的家庭責任,以及不愿意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等。這種狀況的成因較為復雜,但未來農村可能出現“因老致貧”與“因婚致貧”相結合的情況,國家或需要出臺更健全的法規,有力保護其中的合法權益。
有些很正常,但卻伴隨著很多失常。比如城鎮化很正常,但高速城鎮化帶來的居民既有關系網的喪失、自我身份認知的迷惑等,正影響著新一代人的心理,其導致的道德淪喪和倫理扭曲不可小視。怎么能夠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轉換得更為順暢?更快形成新的社會關系網路和社區?形成社會人的責任感和自信感?都是當前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有些不正常,導致的結果會更不正常。比如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階層固化共同引發著社會中許多人群的不安全感,繼而可能在各個方面都形成不穩定狀況。這恐怕是對新時期治理能力的考驗,需要加大力度進行系統設計,解決社會上升通道的順暢問題。
(本文為節選,作者系中國黃金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