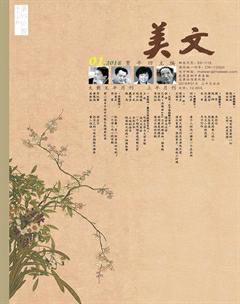書生李浩
周燕芬
在2017年9月舉辦的“文化寫作與學人隨筆專題研討會暨李浩作品系列新書出版座談會”上,幾乎每個發言者都會先來一段“我與李浩”的開場白,然后引渡到李浩的為學為人和對他系列新書的評論。輪到我說話的時候,突然間有點語塞,我和李浩之間的“多重關系”,還真不是一句話就可以交代清楚的:大學時代,李浩高我兩屆,應該是我的學兄,我們都來自偏遠的陜北,見面以老鄉相稱。當我二度進入西北大學中文系讀研時,李浩已經先期畢業并留校任教,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了,后來我也調入母校教書,變為李浩的同事,不多久我們搬進桃園校區新的教工住宅樓,我成了他樓上的鄰居。再后來,我們先后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站做博士后,出站后的李浩很快被選拔為新一屆文學院院長,為文學院當家十年后又升為校級領導,所以在很長時間里,我們又是工作中的上級和下屬的關系。如此“復雜”的關系介紹,引來眾同仁一陣善意的笑聲,讓稍顯嚴肅的會場氣氛變得輕松起來。
記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在西大讀研的時候,李浩已經是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老師了,同時還兼任研究生秘書,管理我們在校研究生的學習考核一攤子事務,每每遇見,不是忙于案頭,就是行色匆匆。事業和生活都在爬坡階段,緊張、忙碌乃至狼狽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我所見到的李浩,從來都是耐心周到、謙虛勤懇的樣子。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西大校門口,我的導師和李浩商量我們這一屆碩士畢業生答辯安排,不知為什么導師發了脾氣,我剛好站在邊上,我是導師的弟子,聽訓話已經習以為常,但此刻他是對著李浩的,而且又在人流如織的校門口,我有點擔心地看著李浩,生怕有沖突發生。不想李浩比我鎮定多了,他不斷點頭說“是”,畢恭畢敬地領受了老師一通教導,趕緊就去忙工作了。那時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李浩豐富的人生經歷及其學術成就的增長和閱歷身份的變化,應該足夠一本傳記來承載了,但是在我眼里,他一如當年的學兄,那種溫良簡行、質樸端正的書生品質,一直與他的為學為人緊相伴隨,成為他文化性格的真本底色。
大凡學人,因其經年求學而后著書立說,個性氣質必然會在自然成長的基礎上形成新的變化,這種融合了生命個性在內的文化心理建構,會逐漸塑造出一個更為立體和豐富的學人形象,李浩當然也不例外,他在由學生而成長為學者的過程中,不待說是大大加強了生命的厚度和寬度,但以我的感受和理解,李浩一直沒有離開自己最初的出發點,一個放大了的“學生”身份一直潛藏在他文化性格的深部,于是才有了李浩尊重師長和敬畏學問的不變姿態,也才有了他在學術道路上不知滿足、求精求深的鉆研精神。如果說以往,這些朦朧的感覺多來自于日常相處,以及對他學術著作的粗疏閱讀,那么現今,隨著李浩隨筆作品集的陸續出版,我對他的認識就有了更切近的窗口,也印證了我對李浩學人性格的解讀大致沒有跑偏。
李浩以唐代文學和文化為治學方向,辛勤耕耘數年,出版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幾本沉甸甸的學術專著。散文隨筆的寫作大約開始于新世紀以來,《課比天大》《悵望古今》《行水看云》三本是其集中展示,并與上世紀90年代的兩部舊作《流聲》和《馬駒》共同推出,形成頗具規模的系列成果,好生令人羨慕。因為作者寫作背靠廣袤的知識領域,所討論的問題又涉及了社會歷史、學術文化以及現實人生的方方面面,以我有限的筆力,很難達到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討的程度,于是避重就輕,就自己所認識的作者和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發表一點個人心得。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學者散文”漸成風氣,創作現象糾纏著種種概念的爭議綿延至今。實際的情形是,中國當代散文創作在這一潮流中再度崛起,形成新的發展勢頭。任何概念的提出,總有其特定指向而做不到全面衡量,以“學者散文”的視角討論,側重的是由創作主體角色和身份的變化,帶給散文新的思想藝術面貌,這也與散文偏于自我表達的藝術特質相一致。李浩的隨筆創作應該算作比較標準的“學者散文”,因為集子里所有的文字都是以他的深厚學養為底墊,以一個學者的生命體驗為表現對象,以知識考古和理性思考為思想支撐,最后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融知識修養和豐富內心世界為一體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
作為學者,選擇隨筆散文,其實也是嘗試另一種方式的學術研究,在此路徑上,中國既有悠久的治學傳統,也有越來越多的后學自覺承傳。李浩早年著述的《流聲》,是一卷研究中國姓名文化的專書,為了方便普通讀者接受,寫得既有知識性,也有趣味性,此次歸于隨筆系列再版,讓我對他早年的文字風采有所領略。看到作者在后記中說:“我后來專攻的中古隋唐士族與文學,空間地域與文學,都與姓名文化有關。”可見也是李浩學術思想系統中的有機一環。另一卷《馬駒》是為馬祖道一大師作傳,作者“試圖用通俗的文字描繪大師的行誼風采,揭示大師的精神境界”,“讓大師真正走到我們大家中間,用他的智慧和機鋒來浸潤現代人干枯焦裂的心田”。同樣是兼顧了專業學問和文化情懷的一本好書。
閱讀李浩的散文隨筆,最有思想沖擊力的當屬那些討論當代文化教育的篇章。比較而言,李浩研究中古隋唐文化與文學的專業優勢,使他具備了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以此為參照,他對當代文化現象的批評,更有深度和力度,能夠提出頗具歷史眼光的獨立見解。而作為從教三十余年的高校教師和曾經的教育管理者,李浩深知教育對于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課比天大》一卷集中了李浩對中國現代教育問題的思考。從進入大學開始,李浩從來沒有離開過高校,從學生到教師再到教學管理,每一階段都是用生命來體察,用實踐經驗來說話,他對教育的愛之深痛之切,他揮灑文字時流露出的書生意氣,與我們常見的那些高頭講章和官樣文章相比,無論識見還是境界有著明顯的區別。
《悵望古今》和《行水看云》中的大部分篇章很能代表“學者散文”的精神特征。作者對傳統文化和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探照,對中國學術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對當下文化重建的種種思考,都充滿問題意識,富于學理的力量。同時,因為隨筆的形式少有規范,給了作者更為感性和自由的表達空間,使得看起來有些堅硬的理論話題,帶上了作家的體溫和文學的情致,從而易于得到讀者的認同和共鳴。我覺得這兩卷文章大約可以囊括迄今為止李浩學術生涯的全方面內容,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個人奮斗的歷程和精神演變的軌跡,也最能體現他的書生性格和學者情懷。一個優秀的學者,他做的應該是活的學問,看似外化于個人生活的學術研究,其實也內化著研究者個人的真性情,散文隨筆作品就更是了。由于從事專業領域的不同,李浩的這些集子中,有不少更閑雅自由的性靈之作是我尤為喜歡的,比如他寫的游學雜記和學林軼事,筆墨輕松有趣又不失內在意味;再比如他寫給師長和親友的寄情之作,細膩婉轉之中透出絲絲溫情。通過散文隨筆,讀者在獲得思想啟迪的同時,也真實地觸摸到作者的情感和心靈,文學的感染力由此而來。學者執筆寫散文,意味著你要將真實的自我交給讀者,甚至你的個人筆調可能會泄露性格和情感的秘密。所以,想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一個學者,特別是他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讀他的散文隨筆,應該是最直接最準確的途徑。
李浩在《行水看云》序言中說:“我也曾有個夢想,就是在專業的教學科研工作之余,無目的,無功利,無追求,僅為興趣和感觸寫點小東西,但絕不會開辟第二戰場,也絕不會把業余愛好發展成為第二專業或第二職業。”這番話令我心動并感同身受,因為我們同是中文系出身,都曾有過夢幻般的文學初心,心靈化的文字正因其無目的、無功利和無追求才更顯得純粹和珍貴。但另一方面,我倒覺得李浩不必刻意在學術研究與散文隨筆之間畫上楚河漢界,在今天這個大散文的時代,李浩的這些隨筆文章,既屬于自己的心靈世界,同時也洞開了另一扇思想之窗。一個學者豐富的文化性格,本就是由多重精神面影立體塑造而成,正如從我的眼中看去,依然是一個不變的書生李浩,但在更多人看來,李浩已經華麗轉身,在為師為學的大道上走得很遠很遠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