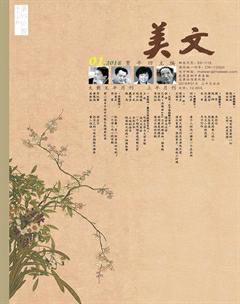交叉小徑的花園
沈文慧
“交叉小徑的花園”——請允許我借用博爾赫斯的題目,來指稱位于北京市朝陽區魯迅文學院的花園,在我看來,沒有比它更合適的稱謂了。
梭羅說:“每個早晨,都是個愉快的邀請。”這是十月的清晨,夜里,淅淅瀝瀝的秋雨灑落下來。雨,落在望春玉蘭茂盛的枝葉上,沙沙有聲。初春時節,這些高大的玉蘭樹總是迫不及待地掛滿碩大的象牙黃花朵,晶瑩剔透,莊重地迎接春天的到來。那時,它們的葉芽兒還在枝干的母體中沉睡,要等到花瓣兒落盡,嫩綠的葉兒才伸著懶腰,不慌不忙地探出枝頭——她們已經奉上了早春最妖嬈的風景。
雨,灑落在茂密的銀杏樹葉上,鑲了金邊的銀杏葉看起來潤澤多了。九月初,我們剛到魯院時,濃密的枝葉間是一串串、一團團淡黃色的銀杏果,如今,銀杏果已經金黃了,落地了,不知哪里去了,是隨落葉一起掃走了?還是被人撿拾、收藏了?都不得而知。魯院大門兩旁,左邊是棵高大的海棠樹,右邊還是棵高大的海棠樹,都掛滿了青綠光潔的海棠果,向空中竭力伸展的枝干上依然綠葉蔥蘢。
雨,落在花園中心的池水里,紅鯉游得更歡了,每天都有游客、學員拿著面包屑、饅頭渣來喂它們,魚們養得越發紅艷鮮亮,這是它們的天堂。池中的殘荷被撈起,散放在岸邊,有幾只枯黃的荷葉依然挺立風中,那些熟透的蓮蓬,變成了學員們書桌上的點綴。
待到它下一次綻放,這個院子已是我們記憶中的風景了……
為此,任何一次呼吸魯院甜潤空氣的機會,于我們,都是生命中意料之外的驚喜。清晨、中午、黃昏,沿著林蔭道一圈又一圈散步,目光貪婪地在花草樹木、天空樓宇間流連,心中充滿莫名的喜悅和感動。
這個被夜雨洗過的深秋的清晨,空氣清涼濕潤,干凈的路面有塊塊水漬,片片落葉舒適地躺在地上,仿佛長久跋涉后終于回到了溫暖的家。鳥們藏在茂密的枝葉間,淺吟低唱,唯恐驚擾了誰。太陽還沒有從鱗次櫛比的高樓間露頭,文學館A、B、C三座展廳大門緊閉,以巴金手掌印為模子的門把手靜默在清冽爽凈的空氣中,耐心等待著今天第一個觸摸它的人。兩年前的8月19號,我們在文學館C座召開《中原作家研究資料叢刊》出版座談會,第一次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一次觸摸到巴金手模的門把手,滿懷虔敬之心,把自己的雙手覆蓋上去,一次又一次,仿佛有神秘的電流傳遍全身。
與往常一樣,整個院落寧靜安詳,但走進花園深處,你會發現,這里隱藏著一個時代的文學風云,關乎一代甚至幾代人的精神塑造,折射出社會歷史的復雜變遷。是的,魯院的花園與別處花園最大的不同,就是坐落在綠地林間的文學大師們的雕像,這些雕像賦予了這座文學殿堂如本雅明所說的“靈韻”,讓人既心懷敬畏又神往不已。
從文學館大門進入,然后左拐,映入眼簾的是鑄鐵材質的魯迅雕像,大寫意風格,也是我所見到的最有個性的魯迅雕像。臉部線條刀削斧砍般粗獷、簡潔,只有一只左眼,這只眼睛凝望著世界,懷疑、審視、思辨的眼神彰顯著思想家的鋒芒,令人肅然、敬然。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他永遠“在路上”,跟《過客》中那個決不妥協、決不放棄的“過客”一樣,即使“受了許多傷,流了許多血”,即使前面是“墳”,依然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他是“朔方的雪”,是“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魂”。意大利畫家阿馬代奧·英迪里阿尼曾說:“我用一只眼睛觀察周圍的事物,而用另一只眼睛審視自己那些屬于靈魂的東西。”這于魯迅是再恰當不過的寫照,先生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以清醒深刻的理性審視一切陳見、習俗、傳統、定勢——“從來如此,便對么?”狂人的質問如劈開濃黑烏云的閃電,炫目轟鳴。與此同時,他更無情地解剖自己,在《墓碣文》中,他這樣描述:“有一游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他以創痛酷烈的自我解剖,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期待并幫助我們成長為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新人”,這是先生留給世人最可寶貴的財富。先生去世已經八十年了,但他始終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巨大精神存在,如林中響箭,穿越時空,呼嘯著飛向遙遠的未來。
沿著魯迅雕像往后走,經過一個不大的籃球場,就是魯院的小花園了。時值深秋,雖春紅凋盡,但樹木蔥蘢,枝繁葉茂,碎石鋪成的小路在綠地林間時隱時現。穿行其中,偶一抬頭,但見茅盾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大衣的下襟被風微微吹起,雙手輕扶身后齊腰高的褐色石基,身軀微斜,正極目遠眺,從頭到腳洋溢著一個偉大作家、理論家以及左翼文學領導者的深邃、理性和睿智。這位從浙江烏鎮走出的文學大家,十二歲時就在作文中就寫下了一生的抱負:“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并化用莊子《逍遙游》寓意,抒寫自己的“鴻鵠之志”。他以畢生努力踐行諾言,他在身上,實現了“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是并不多見的“把兩種素質集于一身的人”,他所開創的社會剖析派小說,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和形式的創造力,充分顯示了文學記錄歷史、介入現實的強大功能和鐵肩擔道義的價值追求,就連頗為偏激挑剔的夏志清也說:“茅盾無疑仍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共產作家,與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遜色。”
在器宇軒昂的茅盾雕像不遠處,是瘦小的巴金雕像,巴金老人身著有點皺巴的中山裝,低眉順眼,若有所思。顯然,這不是寫“激流三部曲”的巴金,而是寫《隨想錄》的巴金。那時的巴金意氣風發、激情澎湃,此時的巴金歷盡滄桑、身心俱疲。但他卻歷時八年,嘔心瀝血,完成了長達四十二萬字的《隨想錄》,對于年屆八旬的老人來說,不僅意味著工作的艱辛,更是一次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歷經磨難后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這部“遺囑”般沉重深刻的“懺悔錄”,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會良知。
花園東南角是艾青身披大衣、手執香煙的坐式雕像。詩人面帶愜意的微笑,令人想起他的《黎明的通知》《向太陽》《復活的土地》等充溢著新生的希望與喜悅的詩歌。“土地”“太陽”是艾青詩歌的經典意象:endprint
早晨,我從睡眠中醒來,看見你的光輝就高興;……我已踏著露水而來/已借著最后一顆星的照引而來/我從東方來/從洶涌著波濤的海上來/我將帶光明給世界……
多么熱切的歌唱!這位“吹著蘆笛的詩人”,從“彩色的歐羅巴”采擷藝術之菁華,詩歌創作卻始終與多舛的時代、厚重的大地、苦難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假如我是一只鳥,我也要用嘶啞的喉嚨歌唱,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多么濃烈的深情!“最偉大的詩人,永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最高的藝術品,永遠是產生他的時代的情感、趣味、風尚等等之最真實的記錄”,這是他的詩歌宣言,也是他衡量詩歌優劣的標準。詩是最精致、最美麗、最凝練、最抒情的文體,遺憾的是今天的詩歌越來越成為個人化、圈子化的自言自語、喃喃囈語甚至胡言亂語,詩歌的讀者日漸寥落,詩歌的影響力日漸式微,難道詩人們不應該反躬自省嗎、捫心自問嗎?
距離艾青幾步之遙,老舍、曹禺、葉圣陶“三老”正在興致勃勃地聚談,葉公身著長袍馬褂、老舍手拿拐杖,二人分坐在褐色長椅的兩端,閑散舒適,曹禺手扶椅背站在他們身后,曹、葉兩位先生都目視老舍,炯炯有神,他們是在討論《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還是《雷雨》《日出》《北京人》?我想起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博物館里展出的藝術家們的手稿,人物分析、舞臺說明、場次安排、服裝造型、研討記錄、修改意見、觀眾反饋等等,一沓沓、一本本,或工整細密、或圈圈點點、或簡筆勾勒,發黃變脆的紙張訴說著精益求精的藝術精神。是的,每一部經典的誕生都是智慧和心血的結晶,都凝聚著藝術之靈與思想之魂。
“三老”斜對面,籃球場東北角,年輕的冰心留著齊耳短發,身披大衣,一手托腮,端坐在濃密的樹蔭下,耽溺于“愛”與“美”的沉思。這是整個花園中唯一的漢白玉材質雕像,冰清玉潔,端莊秀雅。不遠處的池塘邊,儒雅的朱自清戴著眼鏡,身著長袍馬褂安詳端坐。清風明月送荷香,惠風和暢柳絲長,這是屬于朱先生的一方天地,他終于可以永久享受他的“荷塘月色”了。然而,就是如此儒雅的朱先生,卻有著“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錚錚鐵骨。他在“抗議美國扶日政策并拒絕領美援面粉”的宣言書上毅然簽名并說:“寧可貧病而死,也不接受這種侮辱性的施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貧困交加的朱先生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還囑咐夫人:“我是在拒絕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簽過名的,我們家以后也不買國民黨配給的美國面粉。”
繞過荷塘,茂密的竹林邊,年輕的郭沫若正踮起腳尖,高舉雙手,向著太陽大聲吟唱,《鳳凰涅槃》《站在地球邊上放號》《天狗》……這些激情昂揚的詩歌彰顯了“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和濃烈真摯的浪漫情懷,曾使多少“五四”青年激情澎湃,投身到時代洪流之中。緊挨著郭沫若的是丁玲,這是延安時期的丁玲,標準的女戰士裝束,身著厚重的棉大衣,豐滿健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現代女性“莎菲”的苦悶抑郁、憂傷彷徨在革命洪流的激蕩下,早已無影無蹤,今日丁玲,毛澤東譽之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丁玲從國統區歷經艱辛到達延安,毛澤東設宴款待并題詞相贈。丁玲果然不負眾望,很快組建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主任,帶領全團歷時六個月,輾轉三千里慰問、演出、調查、采訪,在戎馬倥傯中寫下了《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速寫彭德懷》《南下軍中一頁日記》《到前線去》等大量速寫、通訊,這些作品生動講述了紅軍將士的革命斗爭生活,洋溢著高昂的革命激情、英勇無畏的戰斗精神,是知識分子以筆為槍、獻身革命的生動樣本。
不能忽略的還有趙樹理的雕像,這個雕像毋寧是一個生動的敘事文本。趙樹理身著樸素的中山裝,背著手慢慢踱著,身旁是一頭小毛爐,馱著一個大姑娘,這姑娘低著頭,黑黑的大辮子松松地從肩頭直垂到胸前,期期艾艾,滿腹心事,仿佛在訴說著自己的憤懣和憂傷。作為描寫農民的“鐵筆”“圣手”,不論是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作品,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心愿、心聲、心情,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樣關注農民、理解農民。他將生活和創作的根牢牢扎在農村、農民之中,以清醒的問題意識和深厚的人文情懷全心全意地“寫農民”,兢兢業業地“為農民而寫”。《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等作品以細膩生動的筆觸譜寫了中國農民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全面翻身解放的時代史詩,散發著原生態的醇厚質樸之美。
在魯院花園閑庭信步,總能與大師們不期而遇,那些風格迥異、形神兼備的雕像是坦誠的告白、誠摯的傾訴,更是無聲的召喚、殷切的期盼和熱情的鼓勵。一切都那么那么鮮活,仿佛觸手可及。他們的靈魂在云端、在樹梢、在花瓣、在草尖;在鳥兒婉轉的歌唱、在空氣無聲地流淌、在歲月流轉的滄桑;他們的氣息與露珠一起晶瑩,與雪花一起飄灑,與春雨一起淅瀝,與秋風一起纏綿。大師們的才情、氣節、追求,凝聚成不朽的精神、永恒的風骨,同他們的作品一起滋養著每一位走近他們的人。
這是文學的力量,是永遠生發著的向上的力量。
碎石鋪成的小路在花園深處蜿蜒、延展,不斷分叉又疊合,無論從哪個路口都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這座“交叉小徑的花園”是隱喻亦是象征,是天啟亦是神諭:文學之路,雖然蜿蜒曲折、荊棘叢生,但只要走進去,以自己的方式和路徑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就一定會曲徑通幽、別有洞天。況且,在每個拐角、路口處,都有前輩大師們在引領、召喚著后來者。“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魯迅先生對青年的忠告歷經百年風雨,依然振聾發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