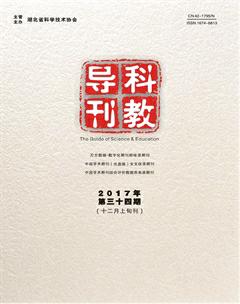關于“國家”建構歷程的再探討
石麗榮
摘 要 本文通過梳理近現代中國關于“國家”構架的發展歷程,探討了現代中國在“國家”構建上“超克”“民族”與“文明”的復合機制。特別分析了近代知識分子的縮影梁啟超對“國家”認識及其與日本明治維新的關聯。本文旨在通過對中國“國家”建構的分析為當今國家間文明沖突的解決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 民族 文明 國家
中圖分類號:D0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2.069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Course of the State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Civilization-state"
SHI Li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framework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mpound mechanism of "transcend",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figure out the course, the author analyzed Liang Qichao's thought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and the relation of his thought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on s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nation; civilization; state
0 導言
自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潮東來,近代文明第一次真切地讓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辱國亡家之痛的同時,還引發一系列對于“國家”建構的討論。從滿清朝廷到有識之士在國家危機面前,無一不欲力挽狂瀾、改弦更張,在“國家”建構的問題上更是相互齟齬。從魏源、林則徐“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從孫中山舊三民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新三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從中國共產黨以民族主義的號召,建立抗日根據地,到毛澤東天安門城樓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按照“民族—國家”的線索輻射開來,形成了關于“國家”建構的歷程。從表面來看,在中國近現代史中關于“國家”建構的紛爭不休終于在1949年新中國的一錘定音之下落下帷幕,但實際上,在當今紛繁復雜、文明沖突不斷的內外形勢下,中國從未停止對適合中華民族、文化的“國家”建構模式的探索和發展。
基于此,本文擬通過回顧近代以來中國對“國家”建構的歷程,分析中國這一系統復雜、結構龐大、糅合民族與文明問題的有機體,研究其失衡與調整的過程,管窺當今中國“國家”建構的本質和意義。
1 艱難的“民族—國家”轉型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國演義》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概括,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在時間的橫軸上,天下國家、儒家文明成為不變的恒量。盡管在朝代的縱軸上,朝代幾經更替,但在所參與的變量微乎其微的情況下,中國歷史的拋物線足以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就在明清交替之后,原本歷史正常衰變的拋物線,在“全球化”的前夜被卷入到了另外一場暴風驟雨之中。滿清康(康熙)、雍(雍正)、乾(乾隆)三代君王或通過戰爭,如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平定準噶爾部;或通過宗教手段,如對蒙藏的佛教政策、金瓶掣簽等,完成對“民族—國家”的構建。同時,在文教政策上,滿清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一方面延續科舉制度、儒學訓詁;另一方面興文字獄,打壓對儒學義理的解釋,隱性地掩蓋了文明內部的沖突。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率使團來華,中華文明與外部的文明的沖突凸現出來,沖突首先表現在禮儀上——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單膝下跪。這場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的沖突最后在妥協中和解,但之后的鴉片戰爭將滿清這個國家卷入到了更大的“暴風”之中。
鴉片戰爭,梁漱溟先生把當時的中國稱為“無兵之國”,它“疏于國防”,“缺乏國際對抗性”。①與其說是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之間的對抗,不如說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斗爭,毋庸贅言,這場爭斗的結局以工業文明取勝。這場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斗爭不僅僅只有中國需要面對,其余震之勢也波及到了一衣帶水的日本。但日本卻在“大政奉還”、“明治維新”中走向近代工業文明,這一問題姑且擱置。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在面對文明沖突時的第一反應是卻是尋求民族之路。
許倬云將近代拯救中國國家沉疴的處方歸結為八種:(1)今文學派托古改制,借中國經典,尋找改革的方向,其思想來源是中國文化的求變;(2)堅持中國文化本位,但是模仿西方,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折衷派;(3)學習西方武器及生產工具,仿照西方練兵籌響,以致搬來西方典章制度的維新派,他們的思想泉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4)從民間宗教中,另辟蹊徑,借用基督教的一些表面形式,動員中國民間力量,全面打開新方向的太平天國革命;(5)以革命行動,建構國族國家體制及民主政權的現代國家,這是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革命;(6)從社會主義立場,不僅建立現代國家,而且糾正資本主義弊病的革命運動,這是共產黨的社會革命;(7)從教育、學術方面,推動西化,以至貶斥中國文化的文化革命,這是“五四運動”;(8)救社會革命之弊,改變方向,從經濟發展,救中國之積貧積弱,這是國民黨在臺灣發展經濟,及鄧小平在大陸改革開放,兩者頗有共同之處。②endprint
從許倬云的歸納來看,除去(8)的社會改革之外,前七項都是直指同一問題——御他族之入侵,尋國家之獨立。從反面來看,(2)、(3)、(5)、(6)、(7)基本都采取了向工業文明妥協的方式,但卻激烈地表達了抗爭西方民族入侵的意愿。就這樣,在民族的執念下,中國形成了“國家”構建的歷程。在這一歷程當中,梁啟超尤為值得關注,他在伯倫知理政治學說的影響下,首先論述了《國家有機體說》。梁啟超強調國家需“自有其精神”。③對于“民族”和“國家”的關系,梁啟超指出:“民族之立非必舉其同族之部民,悉納入于國中而無所遺也,雖然,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于國家”,④在這里盡管梁啟超強調了民族之于“國家”構建的重要性,但也沒有忽視精神文明的重要性。
但是,近代中國的民眾中,不僅缺少民族凝聚力,更缺乏民族意識。因此,才有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對中國積弱之源于風俗者的批判,甚至于為了塑造民族精神,他在《中國武士道》中借助對中國歷史人物的挖掘證明中國武德之民族精神。如梁啟超所思考的一樣,近代中國用舶來品——民族主義為精神的武器去抵抗西方入侵,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民族主義在實現“民族—國家”的構建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2 中國“文明—國家”構建與日本
當中國還在承受如分娩般痛苦的“民族—國家”的轉型時,毗鄰大陸板塊的島國日本——卻在悄無聲息中完成了“明治維新”。在這里必須認識到兩點,一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目的或出發點;二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明治維新的關聯。
日本在進入江戶(1603—1867)德川幕府的統治之后推行儒家思想,在實質上仍然處于農業文明階段。但是,伴隨1853年黑船來航,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并帶著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的國書向江戶幕府致意,最后雙方于次年(1854年)簽定不平等條約《日美和親條約》,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就這樣在日本的海灣邂逅。之后1867年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次年1868年,明治天皇實行“明治維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在1868年所面臨的時代課題與中國如出一轍,即抵御西方,這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出發點。但是,在西方文明的表象——船堅炮利的攻擊下,明治維新一下讓日本站在了西方工業文明的陣營,這樣一來,近代的中國的“民族—國家”的構建就顯得特別突兀。
關于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明治維新的關聯,本文擷取梁啟超作為整個近代的縮影,進而把握其中關系。梁啟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就接觸過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陰的《幽室文稿》;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君恩友仇兩未報”的梁啟超加深了對幕末志士的仰慕之情。1899年梁啟超在神戶中華會館講演,據當地知事所言:“梁啟超涉獵日本近世史,特別敬慕佐久間象山、渡邊華山、高杉晉作、吉田松陰、并專以松陰、晉作自任”。⑤由此可見,明治維新對梁啟超思想的影響。之后,梁啟超在日本更是接觸到了盧梭的思想,還又接受了波倫哈克與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甚至一度接受革命,主張共和,嘗試跟孫中山的革命黨聯合。縱然梁啟超在思想上幾經轉變,但是明治維新對他的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前文所述,關于“國家”建構的思考,梁啟超也是在日本完成的。通過梁啟超,可以管窺近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縮影,中國知識分子或直接或間接,都接受了來自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
無論間接還是直接,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國家”轉型的歷程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西歐產生的“民族-國家”觀念,在劇烈地沖擊著中國的國家認同,“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長期在西方以堅船利炮為后盾的優勢文化沖擊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棄傳統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轉而以西方‘國族國家(nation-state) 為典范,著手從事中國‘國族的塑造。”⑥因此,有學者認為,由那時起,中國人的國家認同發生了“極重大的變化”,“變化中的國家認同自然需要從本土的歷史和文化資源中去尋求表達自己的適當形式,但它實際上并不能依賴于中國的歷史文化資源本身就蛻變出來。來自外部世界的因素,對中國近代史上的國家認同的變遷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⑦無論是盧梭、還是波倫哈克、伯倫知理,這都代表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先進思想。從梁啟超的論述上,似乎看到更多的是對“民族—國家”構建的論述。其實不然,梁啟超在對“民族”與“國家”的關聯進行論述時,還強調“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于國家”,可以看出,精神層面的“文明”也滲透其中。
再反觀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福澤諭吉《勸學篇》強調“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精神;新渡戶稻造所宣揚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井上哲次郎所鼓吹的日本精神,等等。這一切都構建了一個借助中國儒家、西方哲學以及日本神道思想的“文明—國家”。那么,近代以后的中國是否仍選擇了“民族—國家”之路呢?
3 “民族·文明—國家”構建的“超克”
1945年在中華民族興亡之際,國共兩黨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毋庸贅言,這是民族主義在“國家”構建過程中的重要表現。同樣,解放戰爭更是為了爭取國家的獨立和完整。如果說抗日戰爭是民族的救亡圖存,那么,解放戰爭則是中國選擇“文明”來構建“國家”的抉擇。最終,如黃仁宇所言,共產黨成功地建構了控制中國社會下層的機制,相對而言,國民黨建構控制上層的機制,本來就根基不固,更何況經過八年的消耗,缺乏草根支持的上層,當然兵敗如山倒了。⑧從“國家”構架方式上來說,中國從近代就一直選取了“民族”的道路,當然這中間如梁啟超也曾強調過“文明”的重要性,但在1949年新中國選擇走同樣作為西方工業文明結晶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后又經歷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始終在克服“民族—國家”并超越“文明—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探索。
“超克”一詞源于日語“ちょうこく”,意為超越·克服。對于中國當前“國家”建構也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不是一個通常西方意義上的所謂“民族—國家”,而只能是一個“文明-國家”,因為中國這個“國家”同時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厚重歷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學界流行的說法是,現代中國是“一個文明而佯裝成一個國家”。但是,2017年5月14日到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進一步否定了西方學者對中國“國家”建構的評價。誠如西方學者所言中國確實不是一個通常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建構,但是對于“一帶一路”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合作與對話,若單純用“文明—國家”來定義中國就顯得過于片面了。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從中國的國家內部來看,20世紀以來中國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擊中國傳統的運動,以及今日中國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強烈反傳統情結,實際恰恰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其原動機乃在于建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近代西方的入侵讓中國拋棄了天下主義,轉而采用民族主義,從文明國家艱難轉型為民族國家。歷史發展到今天,各種國內外挑戰加劇,繼續揮舞民族主義旗幟凝聚人心是否適合中國值得商榷。有學者指出,“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似乎有著與其它國家不同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即她并不象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在行事,她的民族主義似乎總是一種成色不足的民族主義。”⑨既如此,歷史昭示中華民族民族思維深處有著不同尋常的自我期許,在救亡圖存后,中國當有此份自信走一條特色之路。endprint
如前文所述,許倬云所歸納對中國改革的第(8)如鄧小平改革開放,正是這條特色之路的基礎。當然,對“民族—國家”、“文明—國家”的“超克”需要中國對“中華文明”的反思和重視,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因噎廢食。中國“國家”建構并非是普通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也不是單純的“文明—國家”,而是在超越·克服二者的基礎上的復合機制。
4 小結
關于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國,塞謬爾·亨廷頓認為中國在超級大國競爭結束后的目標是:成為中化文化的倡導者,即吸引其他所有華人社會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恢復它在19世紀喪失的作為東亞霸權國家的歷史地位。⑩當然,亨廷頓的分析側重于中國在文明文化認同中的作用和角色,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有機體,民族與文明本身就是相互交織、相互糾葛在一起的,強調中華文明的同時也是在確立中華民族的概念。中國在歷經近代“國家”構建轉型的苦難之后,從民族主義的道路到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再到“超克”“民族”與“文明”,不可否認走了不少彎路,恰恰如此,根植于中華文明下的復合機制才是當代中國“國家”構架的選擇,這也是由中國自身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復合結構所決定的。中國的“國家”建構必將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產生深遠意義,也將為當今國家間文明沖突的解決提供借鑒意義。
注釋
① 梁漱溟.中國文化之要義.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328-329.
② 許倬云.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M].三聯書店,2010:122-123.
③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華書局,1989:71.
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三[M].中華書局,1989:72-73.
⑤ 吉田熏.梁啟超對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與消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2):79-89.
⑥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J].臺灣社會研究刊,1997(28):1-77.
⑦ 姚大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與國家認同[J].中國學術,2002(4):187-206.
⑧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M].聯經,1993:339-359.
⑨ 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J].戰略與管理,1996(1):14-19.
⑩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華出版社,2010:147.endprint